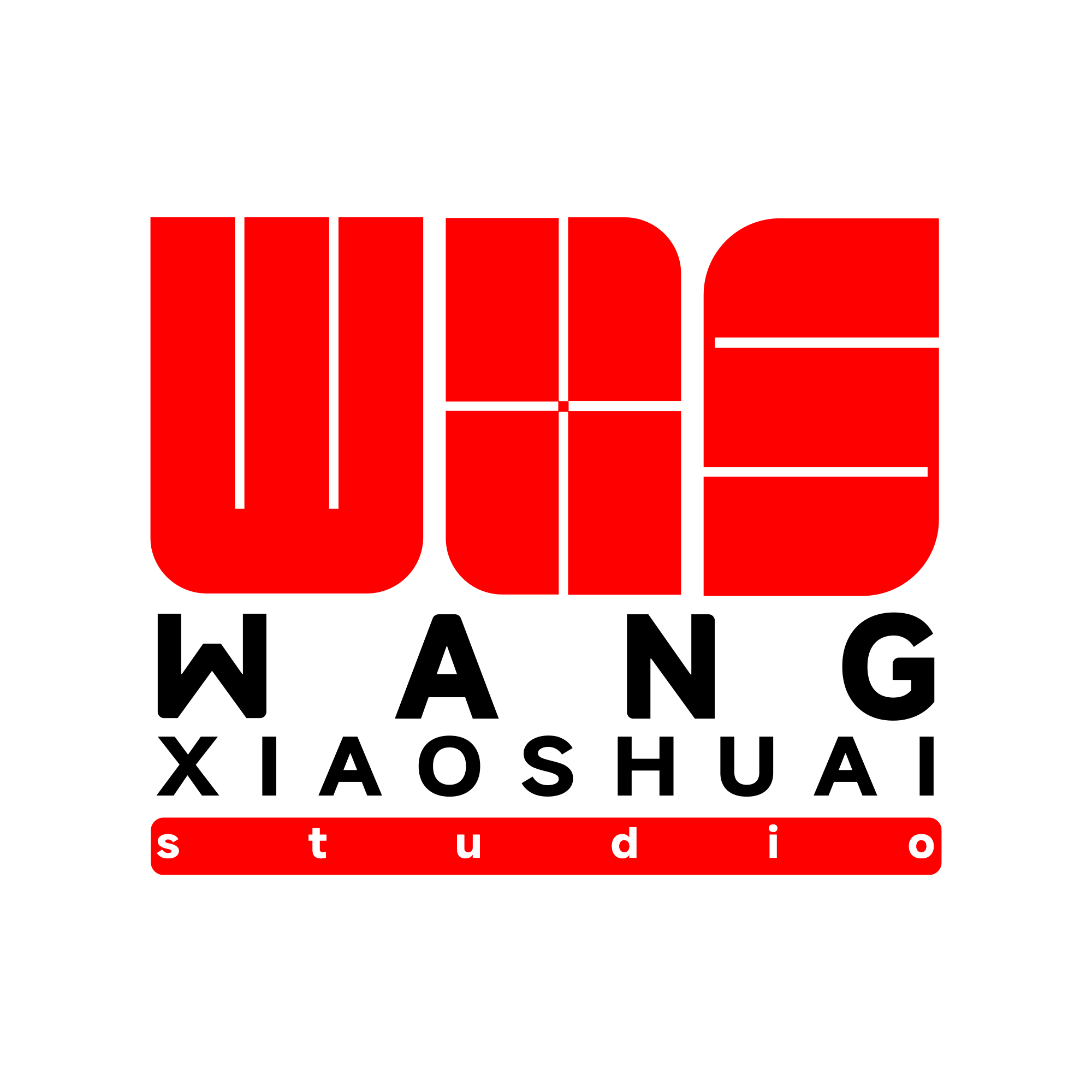王小帅以其讲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村移民人群的刚强但深入感人故事的影片而被熟知。他广受好评的三部曲《扁担·姑娘》(1998)、《十七岁的单车》(2001),及《二弟》(2003),均聚焦当代中国面临的农村到城市或城市到海外的移民的残酷现实。正如白睿文(Michael Berry)所总结的“通过他最近的作品,王小帅准确地描述了人口移动的复杂现象……将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非常重要而有代表性的特征”(2005:164)。不像主流媒体企图忽视游移人群或将其痛苦正常化,王小帅的作品拒绝将他们的流离失所和从属性视为理所当然,参考Xu Jian(2005:434)所说的“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符号秩序的批判性干预”。王小帅对农村工人的梦想和困境的分层描述,不仅说明了其主体形成的复杂过程,也揭示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体联合在这一弱势社会群体身上施加的经济和制度暴力。
研究王小帅电影的学者倾向于关注他是如何展现人物从乡村移民到城市1。但很少有学者研究反向移民的角色,尽管这在他后期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王小帅反复将故事设定在“三线建设”的阴影中,那是在1960年代越战升级、中苏交恶时,由中央指挥的大规模的城市往农村迁徙的革命运动。出于国家边防考虑,中国政府号召成千上万的工厂及工人从沿海地带(在战时可能的边防地带)迁移到中国西南部、西部偏远的山区,也就是被称为大三线的地区2。这个运动旨在构建中国内陆地区工业体系,从而保证国家在战时仍能正常运转(Naughton 1988:354)。王小帅的家庭也曾加入这个大迁徙,跟随其母亲的工厂从上海迁到贵阳。
因被视为国家机密,这一运动多年都被排除在公开的中国历史之外,也很少被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在文化作品中3。王小帅是少数几个会讲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段常被忽视的历史,以及更少为人知的受其影响的苦难家庭的故事的导演之一。保留有关注流离失所人群的内核,但王小帅关于三线建设的影片显然区别于之前只有现代都市背景的作品。相反,这些影片深入挖掘被遗忘的过去,探寻与经济历史动荡有关的记忆和创伤的问题。考究历史与历史的遗产,王小帅说他的最终目的是丰富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深远影响的理解4。
王小帅第一次寻回三线建设家庭经历的尝试是2005的长片《青红》。故事设立在1980年代早期,中国改革开放几年后,贵州省的一个偏远村镇。影片聚焦于父女冲突:父亲想要实现他带着全家重回上海的愿望,但女儿却不愿离开,因为她在贵州找到了故乡归属。Richard Letteri(2010:5)认为,女儿最终的心理崩溃显露出“无家可归之感吞没了她,也吞没了那些被卷入中国经济和社会巨大变革的人们”。的确,父亲和女儿,归根到底都是政治目的推动下经济移民运动的牺牲者,两代人的青春都被流离和破坏。
关注同一主题的后一部作品,《我11》(2011),将年代更往前推至“文革”接近尾声的1975年;它可以被看成是《青红》的前传。一个源自王小帅童年记忆的半自传式故事,这部影片捕捉了他以前一种天真和好奇心意外地与历史事件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的片段。一个成熟的十几岁男孩的眼睛巧妙地揭示了一个混乱的、令人不安的、被险恶政治变化胁迫推动的成人世界。
王小帅最新的影片《闯入者》(2014)是他“三线建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延续拓展了前两部的主题和事件。《闯入者》持续挖掘和冥思在“文革”的巨大阴影下,三线建设运动时期被流放的家庭的经历。然而,与前两部将故事设置在几十年前不同,这部影片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将过去带到这里和现在。跟随名叫邓美娟的退休独居老人(在整部影片中称为老邓),一位参与过三线建设的工人,影片敏感地捕捉到这位老太太与过去不可逃离的束缚。在文化大革命末期,老邓是少数几个能成功逃离农村劳苦漂离的生活,而把家人带回北京的工人之一。城市的生活一切都很好,直到一连串沉默的电话打乱了她回归城市生活后的平静。一个神秘的十几岁的男孩追踪者的出现进一步扰乱了她的生活。持续不断的骚扰电话和男孩幽灵般的出现,使过去的痕迹和记忆开始蔓延,最终将她推回曾经工作过的贵州省的偏远工厂村镇。这部电影因此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将这里(北京)与那里(贵州的一个不知名的前三线建设小镇)交织在一起。为了实现这种混合,这部影片超越了王小帅先前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借用了悬疑片和恐怖片的戏剧性表现手法。从老邓接到的神秘骚扰电话开始,影片小心翼翼地隐藏着信息,让观众的兴奋、期待和焦虑不安不断增强。它通过包括幽灵的形象——或者至少是老邓认为的幽灵想象——为影片增添了新的想象纬度,从而渲染了这种令人战栗的氛围。
为什么王小帅用这些新的叙事方法呢?它们帮助说明了怎样的对历史、记忆和现实的理解呢?着眼于幽灵萦绕的比喻,我阐述了王小帅如何用这种修辞来强调过去的记忆和今天的现实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系——而不是两者的分裂。《闯入者》既挑战了埋葬“文革”动荡记忆的官方举动,也挑战了普通人想用遗忘历史来寻求舒适寄托的行为。这两种做法是服务于前瞻性的、未经反思的后毛时代话语,及对经济发展的执迷。《闯入者》将我们的注意力牵引至历史暴力对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持久伤害。在探索幽灵萦绕的起因时,电影的目的不止在讲述常见的历史原因: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冷酷无情或某些高官政治恶棍的邪恶所导致,也不是全民歇斯底里症的不可言说的发作的结果。相反,它是由普通人导致的。
遗产的政治
文化大革命后的官方论调试图给这个历史阶段画上句号,并迫切要求推动亟需的经济发展。邓小平1978年12月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更显而易见地说明了这一思想转变。尽管邓小平肯定了纠正“文革”造成的一切错误的必要性,然而他推动迅速平反冤假错案,却并不鼓励对过去的问题进行彻底深入的调查。他建议:“要把各个问题的主要方面放在首位,并从大体上解决,深入细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邓小平 1999:449)。在历史进步论的推动下,邓小平领导党和国家将自己从历史包袱中“解放”出来,把目标转向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必须向前看。只有考虑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顺利前进。”(451)邓小平强调。一种向前看的心态以后便成为中国人的发展主义思想和后毛时期中国人身份的标识。“文革”时代的历史与现在从而被割断,两者变得无关紧要。
历史进步论的批评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提出了“幽灵学”的概念,倡导我们关注在当下过去的残存和两者的固有关联。对德里达议题的迅速回击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他在其中预言了“历史的终结”,并宣称全球资本主义将最终完胜共产主义。虽然福山对资本主义的赞词是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明确界限为前提的,但德里达的幽灵学却否定了此种界限的存在可能。幽灵学反而试图打破对历史阶段的局限性论述,揭露当下本体论存在的错觉。德里达(1994:54)警告我们,我们不可避免地承受着过去的印记。用他的话说,“我们的存在首先是继承物,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或知不知道”。因此,他提出要超越时间顺序的壁垒,追求“一种记忆、遗产和年代的政治” (xix)。
文化大革命被官方论述划定为整整十年(1966-1976年),王小帅的《闯入者》探讨文革残余的方式呼应了德里达的幽灵学。向主流观点提出质疑,王小帅试图表明,过去不仅仅是过去,而是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像《青红》和《我11》中,导演不仅仅是回顾过去的经历,而是在探寻过去是如何形成的。如同艾弗里·戈登 (Avery Gordon)(2008:8)在其它文本中所说的,“一个现有的存在、行动和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
上文提及的沉默电话使过去奔涌进老邓的生活,不仅打扰了她内心的安宁,也激起了周围人们的各种猜测。老伴去世不久,老邓在北京一间不起眼的公寓里独居,打发退休后的生活。她为两个成年儿子提供帮助,尽管通常是不被需要的,她也照顾住在养老院的年迈的母亲。然而,老邓的日常生活节奏被反复的电话打断了;每次老邓接电话后,听到的只有沉默(图1)。神秘无常的来电让老邓彻底心烦意乱。当她试图向警方报案时,焦虑使她头脑不清醒,反而不能连贯地表达发生了什么事情。老邓求助的每个人都用他/她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些来电。她的警官邻居把它们视为寡妇因孤独产生的幻觉;对他们来说,老邓的抱怨只不过是空巢症候群(压力,孤独,因子女离家造成的人精神不稳)的表现。这是很容易给出的解释,这也的确是近年来中国空巢老人群体愈发明显的困境。老邓的大儿子,军,却指责他的工人们,他怀疑是他们因工资拖欠而报复他。大军的猜测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另一个当代社会问题——移民工人的困境,王小帅电影中另一个常见的主题。军的妻子没觉得有什么需要警惕的,认为沉默的来电者只是有人在搞恶作剧或误拨了号码。在她看来,老邓的极端反应只是表明了空巢老人的心灵被磨损的严重程度。
在叙事层面上,这些对电话之谜的分歧意见构成了悬念,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心。然而,当深入观察,他们也揭露了当今中国失忆的文化。尽管这些人物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他们都偏好一种将这里和现在视为默认坐标的感知模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和历史遗产的质疑。无论是责备母亲的孤独感、流动人口的绝望状态,抑或精神的衰退,这些人对家庭的过去及其对现在的影响视而不见。这种失忆和否认的做法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随着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欣喜若狂的情绪笼罩着许多受到新生活诱惑的中国人。的确,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培养了忘却的习惯,悄悄地将人们从记忆和他们创造的历史深度中剥离。正如黃易居所言,直接的历史性过去“在一种‘变形’中被释放了——经济发展的知名奇迹,发展中的新信仰和面向未来的狂热凝视”5。
为了抗衡这种历史性潮流,王小帅着眼于家族历史,尤其是与儿子的互动,继续塑造老邓这个角色。老邓是一个固执而又胆怯的母亲,一直在干涉儿子们的私生活。这激怒了军的妻子,她不喜欢婆婆干涉家务和照看孩子。老邓公开表示不赞同同性恋儿子兵的生活方式,因此她与兵的关系也紧张。表面上看,她与两个孩子的关系似乎反映了社会快速变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代际鸿沟。老邓似乎违背了核心家庭,隐私和同性恋这些新概念。但这种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老邓有这样的权力来指导她儿子们的生活。这种权力意识在与兵的一场争执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被母亲频频闯进租处惹恼,兵要求母亲尊重他的隐私,老邓立即激动地喊道:“你的家是我的家,你的就是我的。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你别想把我拒之门外。” 在这里,老邓清楚地表明了兵对她有很大亏欠,这超出了一般母亲所应得的。老邓为什么觉得如此有权力可以指导儿子们的生活呢?
这可从她在三线建设中为家庭的拼搏得到更全面的解释。正如兵最终知晓的情况,当年怀着他的老邓竭尽全力要得到转移名额,是为了保证能让他在城市出生。通过她的努力,他和哥哥才能幸免于继续在山上过着孤独绝望的生活。享受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和优待的军和兵,都忘记了老邓为获得这样的生活做了多少挣扎努力。使她失望的不是她儿子们态度的现代性,更多是他们对她的牺牲没有感激。从这个角度看,老邓想要和儿子们有个更亲密的关联变得更加容易理解。老邓跋涉至兵住处的长镜头直接象征了这种困难:她拖着一个沉重的购物车进发廊,蹒跚地走过前台,爬上狭窄的楼梯,挤过按摩室,最后到达兵的住处。老邓似乎已经穿过了时间的隧道,只发现自己在一个超越记忆的地方;就好像她过去的亲身经历不再相关。
老邓的顽固拒绝放弃自己作为家庭看护者的角色,面对她过去经验的社会和家庭的无用性,她起着应对机制的作用。1965年2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大力使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来推进运动。老邓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于中国三线建设的事业中。像其他数百万人一样,她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归于国家利益(Yang 2006:102)。然而,当主导三线建设的左派政策随着“文革”被否定后,她的努力基本是无价值而徒劳的。老邓被她过去对社会牺牲的荒谬感所困扰,于是她全身心投入到家庭,无论家人是否欢迎她的帮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独立的、意志坚强的,但同时也是脆弱的、可悲孤立的老邓,在现代繁华的北京城市中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
如果说老邓代表了“文革”后的城市回流者,那么悄悄接近老邓的十几岁男孩就把代表了仍在三线建设困境中的人们。与上山下乡运动后再回流城市的知识分子不同,大多数参与三线建设的家庭并不被允许再移回城市。与工厂捆绑、受制于严格的户籍制度,男孩的家人,包括他的祖父老赵,必须留在不发达的贵州三线建设厂镇。随着中国1980年代进入改革时代,发展重新聚焦东部沿海,一度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被搁置了。随着政府补贴的减少,再加上地理和交通的制约,许多三线建设的工厂破产了。他们的生计难以维持,三线建设的工人逐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在电影中,这个男孩和他的祖父母仍住了原先分配的工厂宿舍,现在这个宿舍已经破旧不堪,甚至已经荒废了。家庭住宅的隔离和腐烂是被遗忘和遗弃的实际体现。如果他的祖父赢得了回城的机会,那么这个男孩本应可以享受老邓的孙子的一切优待。但是,他滞留在了一个阴沉的三线建设村镇,在荒凉的贫困中长大。
这个男孩在北京游荡,他的奇怪行为源于永远流离失所和被边缘化的创伤。这部电影的开场展现了这个男孩在北京随意闯进一间公寓,他洗澡,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然后坐在椅子上喝酒。他充满好奇而游离的眼睛、脚上显眼的不合适的女士拖鞋,都表明他与这个陌生人的家的格格不入。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个男孩会习惯性地闯入了别人的房子,他从而体验都市的日常生活,满足他自己的恶趣味。他故意用沸水浇灌室内植物,并把房间衣物弄得混乱。面对休闲和破坏的双重渴望,他实施的行为显然不仅仅是盗窃,而是受到复杂心理冲动的驱使。成长于三线建设区域,这个男孩怀着嫉妒与怨恨:他既想过都市生活,也愤恨这个抛弃了他的制度。这些混杂的情绪与他成长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男孩的精神分裂行为后来使他陷入严重的事件中。他不断闯入别人家时,他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归属感。在一个场景中,他舒服地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吃苹果。王小帅使用横摇慢镜头赋予这个情节一股梦幻般的质感,这种质感在当摄影机从男孩移动到鱼缸,棕色的水铺满整个屏幕时,尤为强烈。通过这个镜头,这个男孩看起来像他真的是住在这间房子里,他只不是在打发普通的一天时光(图2)。然而,跳切打乱了超现实的情景,男孩不再在鱼缸后的沙发上。当摄影机横摇至原来的位置时,房间里一片混乱。在地板上,一把流血的刀子旁,躺着一个被自己的血液包围着的老人的尸体。这意味着这个男孩被房主发现时惊慌失措之下误杀了房主。房主的意外回家也许提醒了他在城市里多么渺小,而残酷的杀人行为是他从梦中惊醒后的绝望反应。正如程青松(程/王,2014)所悲叹的,他的罪行是“历史的一枚苦果”,这种伤害对年轻一代的影响不亚于有过亲身经历过的人。
老邓和男孩的存在都肯定了历史在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的持续影响。不过,他们都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闯入者” ,这也是直译的中文片名。老邓的儿子们厌恶她对他们生活的闯入;且不说男孩入室的行为,他来北京这个事实,就违背了社会的期望。从象征的角度来看,真正的闯入来自老邓和男孩背负的过去的痕迹闯入现在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他们是被拒绝的,意味着当代中国拒绝它过去的记忆以一个未受阻碍的游行为名义迈向未来。老邓和男孩似乎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失去同步。这部电影对他们经历的以及他们背负的沉重的历史和心理包袱的关注,从而成为对于主流失忆文化的一种反抗,对我们历史遗产存在的警醒。通过每个人物的经历,我们看到了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密切联系。
王小帅把老旧建筑物与现代建筑物的镜头放在一起,并不断强调两者的联系。影片的第一幕是一座由灰砖和红砖组成的破旧的两层建筑(图3)。镜头拉近,突出了两个特征:它的破窗户和它前面一棵枝叶稀疏的枯萎的树,两者都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荒凉感6。很快,一个 正沐浴在明亮阳光中的更为现代化、城市化的住宅建筑出现在镜头中。这种交叉剪辑在电影中再次出现,两种形象的对比足以使三线建设地区居民楼的镜头看起来像是出现在倒叙中。但是,正如这部电影所揭示的那样,那个发霉的、被遗弃的建筑在现今生活中也是一样。虽然这个空间对老邓来说有着丰富的回忆,但不仅仅是一种回忆;相反,它是一种存活到现在的物质遗迹。过去和现在并存。
正如王小帅(2015:168)所指出的那样:“《闯入者》是一部充满过去的电影,但也完全发生在现在。 这种表现使我们更加了解过去对现在的持久影响。”
幽灵萦绕
与王小帅以前的通过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主题的电影不同,《闯入者》使用大量的奇幻和恐怖的元素,描绘了幽灵般的形象。沮丧于与儿子们之间的不和,老邓只有在她已逝世的丈夫的遗像前倾诉苦涩,这成为她唯一的慰借。老邓念叨时,她丈夫会突然出现,就坐在她对面,听诉她的委屈。老邓丈夫的幽灵被诡异地带入了另一种现实化的场景,类似的场景在电影中数次出现(如图4,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幽灵般的形象通常是以客观的视角,而不是以老邓的视角呈现。这样做,影片似乎在坚定地表示老邓丈夫的幽灵不是幻觉,而是真实的存在,需要我们予以应有的重视。为此,老邓丈夫的幽灵不是一个半透明的阴影或浮动的幻影,而是一个身体完整的人。
尽管这个男孩并没有如老邓丈夫般死去,但他也像一个鬼魂:沉默,孤独,流亡在这个城市的状态让他成为一个幽灵般的人物,在一个他不属于的地方游荡7。有趣的是,除了老邓之外,他是唯一一个和老邓丈夫的幽灵出现在同一个画框内的人。老邓本以为他是个刚到北京要找工作的外地年轻人,便对他很好,甚至邀请他去家里吃饭。饭桌上,老邓很自然地对死去的丈夫说话,并把男孩介绍给他认识。她的丈夫出现在饭桌边,好奇地转过头看着男孩。虽然没有明确交代男孩是否真的看到老邓的丈夫,但是他们互相注视着彼此的方向,眼神间创造了一个彼此交流的空间,以此暗示男孩对鬼魂的特殊亲和力,并象征性地融入了鬼魂的境界。相比之下,在整部影片中,老邓从来没与丈夫有过目光接触,丈夫也没有出现在军的家里,与家人同进晚餐。
我们如何理解王小帅对幽灵意象的使用?德里达在详细阐述幽灵学的观点时指出,过去的残余物往往体现在幽灵和鬼怪中,以应对霸权秩序的压制。他写道:“萦绕属于每一个霸权的机构”(1994:37)。尽管权力机构希望避免不必要的记忆,但德里达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历史的光谱—— 过去的幽灵总是会回归的事实。他断言:“历史结束之后,灵魂跟随归来而归来,它既是一个死去又归来的人,也是一个预期归来并一次次重复出现的鬼魂。”8 压抑的东西以幽灵萦绕的方式归来,不仅打开了记忆的大门,还产生了质疑意识形态霸权的不同语境。正如艾弗里·戈登 (Avery Gordon)(2008:xvi)所暗示的那样,鬼怪或幽灵的出现是一种“准确干扰那些始终不完全的遏制和不停直接针对我们的压制”的方式。
《闯入者》以类似的方式援引幽灵般的功能,揭示和挑战企图抑制不需要被提起的过去的霸权政治制度。如前所述,国家一直在限制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深度调查,迫使中国人民充分投入到国家发展的新阶段9。然而,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并不仅是被长远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信念所驱动的,也是被试图推翻党臭名昭着的历史残留的努力所驱动。过去封锁“文革”的努力,先发制人地压制了任何可能破坏党性权威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压制那些不符合官方叙述的记忆是为了维持霸权的政治控制10。幽灵的存在是这种压制性结构的一个症状,但它也是一个强大的可用来回忆被压制记忆的媒介。老邓的丈夫和男孩都背负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与政府话语想要驱逐过去幽灵的萦绕的努力相反的是,这部影片为他们打造了一个物理存在和需求认知的空间。
老邓丈夫的幽灵主要是作为一个有共同回忆的精神伴侣,但这个代表不同秩序的幽灵的男孩,似乎对老邓和整部影片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他没有安慰孤寡老人老邓,而是萦绕、困扰着她,迫使她直面一个黑暗而痛苦的秘密。尽管这部电影从没给出明确答案,但多次暗示这个男孩就是那个拨打电话的神秘人,打通电话却不说话,用令人不安的鬼魂方式敲她家的门。他还像一个幽灵般的影子出现在老邓的生活轨迹中,在公共汽车站、在人行道上,在她的公寓楼里向她靠近(图6, 7)。在这些神秘电话和男孩的缠扰之下,老邓变得心烦意乱、心神不宁。
老邓和男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交叉剪辑的段落,得到了极大的戏剧性说明。这段剪辑中,梦想与现实、意识与无意识交织在一起,变得几乎无法区分。那个场景发生在男孩陪着老邓去北京郊区的厂家修理电动足浴盆之后,他们回到老邓家,男孩四处走动。在这个场景中,王小帅反复切入切出老邓的梦境,但没有使用淡入淡出的手法,使观众无法按照传统的电影方法寻找线索。在她的梦境中,老邓发现自己在一个荒凉的郊区蹒跚而行,虚弱无神,男孩抱着电动足浴盆跟随其后。至此,梦境在很大程度上与白天发生的事情重合。镜头然后切回老邓现实生活中的卧室。在这儿,男孩爬上老邓的床,躺在她身边,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老邓仍睡着,她温暖地握着他的手,淡淡的微笑闪烁在她的嘴角(图8)。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作为被遗弃者的共同处境将这两个孤独的灵魂聚集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同情化亲密的感觉。这个男孩觉得在这个城市终有一个人关心他,老邓很高兴能有人陪她11。然后又回到梦境中,男孩站在老邓的身后,准备用足浴盆袭击她:以前的温暖感突然被冷酷的恐惧感取代。接下来的场景,可能是发生在梦境抑或现实中。老邓遇到两个男孩的化身:一个躺在她身边,轻轻地抱着她;另一个站在她的床边,准备用把刀杀死她。这个漫长的梦境场景以老邓从恐惧和困惑的状态中醒来而结束。她挣扎着站起来,去到另一个房间,发现男孩已经离开,家里的旧照片被撕成碎片(图9)。男孩撕碎旧照片的行为暗示了他和老邓矛盾的关系之下隐藏着与过去记忆有关联的某些东西。老邓从男孩的出现中感到安慰和不安,让人想起弗洛伊德的怪怖者的概念,德文原词 unheimilich,寓意与其相反的含义,即heimlich温馨的(亲切的,熟悉的)。对于弗洛伊德(Freud,2001:930)而言,“怪怖会引导回已知的和熟悉的事物的恐惧。”如果这种怪怖的感觉实际上是由熟悉的事物触发的,那么问题是为什么熟悉的可以变得怪怖和令人恐惧。弗洛伊德把压抑当作引起恐惧感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怪怖是“已存于内心的熟悉的、只有通过压抑才能与之疏远的东西”。换句话说,压抑会使熟悉和习惯的东西陌生化。因此,怪怖的致命影响来自于本应该被持续隐藏和缄默的事情被曝于日光。被压制的“陌生人”的出现,威胁着良好维持的心理和象征性秩序,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构成了令人不安的对抗。
男孩的出现对老邓来说是如此的怪怖,正是因为他让她想起了一个熟悉的过去——她和整个国家发自内心想要忘记的过去。过去的细节终于露出:她和那个男孩的祖父老赵,曾在贵州同一个三线建设工厂工作,两家曾共同争夺“文革”后唯一一个返回北京的机会。由于她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老邓了解老赵的过去,并以此抨击和检举老赵,从而确保自己获得了城市回移的特权。失去了这唯一机会,老赵太受打击而中了风,并从此卧床不起,他的家庭也受到摧残。老赵死后不久,男孩就踏上了北京的旅程,开始了他的追踪,可能是通过电话悄悄地骚扰老邓。那时,老邓从以前同事老黄那儿得知了老赵的死讯。男孩在这个时候的出现迫使老邓面对令人羞耻的秘密和她自己内心的黑暗。 因心有疑虑,她向已故的丈夫吐露心声,说:“自从老黄打来那个电话,说老赵去世以后,就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似的。总好像有一团阴影缠着你。”这个男孩的真正影子后来变成了一个内在的影子,导致老邓不断看到他在面前晃悠,但监视录像显示除了她没有其他人。 对老邓来说,她对老赵和他家人造成的伤害,就是一种既熟悉又可怕的记忆阴影——弗洛伊德所指意义上被压抑着的——这个男孩使她不能再压抑它。
当唤醒过去,男孩的幽灵般的存在与早期鬼魂类电影中一些知名人物的存在模式不同。例如,《胭脂扣》(1987)中的如花试图重燃她过去的浪漫,从而唤起了香港对其过去的怀旧幻想和迷恋(Chow,2001)。另,《不散》(2004)中的幽灵般的人物从在一个朦胧的戏院里观看公开放映老电影的体验中寻求安慰(Stuckey 2014)。这两部影片中都投射出过去的理想形象,有能力弥补他们。相比之下,《闯入者》表现出一种复杂的记忆,这种记忆一度令人觉得开心或不安,它挑战了对过去浪漫化的怀旧倾向。的确,老邓对三线建设的记忆是矛盾的:当时她正值青年,满是浪漫的理想主义,但也浸受无情和背叛的污染。她在老年学校门前犹豫地俳佪的场景经常出现,表明了她对过去感情的矛盾情绪:她被社区唱诗班唱到的熟悉的革命歌曲所吸引,但是每当她走近门口时,她立马产生一种逃离歌声响亮的合唱团的冲动,他们的声音回荡着太多的革命性的骚动。当她试图压制黑暗的记忆时,男孩的存在促使她打破心理障碍,面对一直以来逃避着的东西。幽灵的萦绕阻止了她对过去的精神回避;她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压制伤害他人家人的记忆了。
男孩的唤醒力量也促使她最终承认自己的罪过。试图从最近的离奇经历中弄清楚原因,特别是在得知老赵死讯后,老邓认为这个男孩一定是老赵的灵魂转世,而且一定是来找她复仇的12。背负着祖父没有解决的苦衷,男孩最开始表现出伤害老邓的意图,比如那天晚上,很可能是他朝老邓的窗户扔的砖头。如果银幕上老邓梦境段落的结尾处出现的情节部分地反映了“现实”,那么他也很可能设想杀死老邓13。然而,比起复仇,他似乎更看重罪恶感。在电影中,老邓终于在又一个骚扰电话中说出了自己的疑虑:“老赵,是你吗?你要不出声,那就是你了。你是来跟我讨债的吧?……我知道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全家……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值得注意的是,她说完道歉的话语,不断打来的电话铃声一直萦绕在她的公寓和她的心里。正如 Judith Zeitlin(2007:87)在不同文本中解释的那样,“只有当引起幻影表现的不满情绪得到妥善的纠正时,情绪的停滞才能结束,死亡的灵魂终于进入重生的循环,或者解散为沉默和虚无”。老邓承认自己的罪恶,让这个怀着怨恨的男孩停止了他的幽灵般的萦绕,最终让他放心地离开了北京。
就更广意义而言,男孩所体现的幽灵般的萦绕,见证了三线建设未解决的历史造成了无数家庭的地理和社会性质上的流离失所。这些家庭从城市迁徙出来,发现自己漂泊不定,无法再回城市,也无法认同自己的新环境。 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中,将“鬼”定义为“鬼”或“归来”。就鬼的确切含义或“回家”,哈佛大学中文学教授王德威指出“与通常概念相反的是,‘家’不是指人的居所,而是指永恒的安息之地”(2004:266)。参考《左传》,王德威进一步解释说:“如果鬼魂有可回的居所,就不会引起恐慌”(267)。换言之,如果鬼魂有家,它就不会成为一个萦绕的魂灵。根据这种理解,这部影片中幽灵的萦绕,不仅指向没有解决的的个人恩怨,也指向三线建设一代人无家可归的困境。因而,老黄抱怨国家政策导致的漂泊无根状态:“我死了以后不要把我埋在上海,也不要埋在这里(贵州)。哪里都不要埋。你把我的骨灰往天上一扔。”老黄解释了许多留守三线工人,包括那个男孩已故的祖父的不知所措的困境。 如果我们接受老邓的理解,那老赵死后灵魂的回归,就意味着需要解决遗留的怨愤。正如他的不安的魂灵困扰老邓一样,无数工人的回忆也萦绕着一个逃避解决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责任的政府。
道德拷问
问题在于老邓的道歉何以到来如此之晚,更况她明确知道自己如何了伤害老赵和他的家人。是什么让她可以否认自己的内疚感?我认为,在官方和文化文本中,集体受害者的普遍说法让许多人逃避了责任。1981年发表的一项国家决议标志着对“文革”的官方评价,它否定了“文革”给这个国家带来严重的动荡和灾难14。在追溯十年灾难的主要原因时,它指责毛泽东为发起革命的主要责任人15,然后把最激烈的谴责引向反革命林彪、江青等人的派系,说他们恶化了“文革”运动。虽然《决议》指出要深入调查造成灾难性革命的社会历史原因,但这只是抓住了问题的表面,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党的合法性。首先,它强调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短暂历史,并用此作为为党的错误辩护的借口,即尚未完全准备好迎接“全国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到来”。 其次,它归咎于中国封建专制的有害遗产,说这造成了毛泽东的错误指挥和党内民主的崩溃。虽已成定局,但这些反思过于夸张和过早地下结论,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包括“文革”期间和之后的混乱的道德问题,基本上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官方的判断中,广大的中国人通常被判定为受害者。为了让人民反对激进左派力量,《决议》将脆弱的群众和其被误导的领导人做了简单二元划分,且后者对前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通过把它们归入概念范畴,党宣判普通中国人在这场全国大规模运动中的任何责任都无罪,尽管它的很多行为并不总是规矩上级指导的。事实上,官方话语不重视个人责任,与其参与者的倾向一致,都否认他们经常不可分开的受害感和内疚感。在讨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2016)提醒我们:
文化大革命的本质不仅仅在于毛泽东误导且造成了混乱。其实质是,中国人在没有直接的命令的情况下,对彼此是如此残酷。他们互相杀害,互相打架,互相折磨。毛泽东没有走上街头,说:“你有权折磨别人。去折磨吧。“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
的确,许多中国人不仅是受害者,而且是加害者。然而,人民受害的官方叙述使他们在暴力行为中的责任问题很少得到解决。按照这个逻辑,老邓和她的同事一样,也是三线建设的受害者,尽管她已经无情地伤害了其中的一些人。她共通的受害感减轻了她的内疚感,所以她可以避免数十年的道德追问。
中国电影中“文革”记忆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种集体受害的逻辑。普通人被描绘成无能为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不可思议的恐怖事件的各种罪魁祸首的摆布。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8)等,是早期试图了解“文革”原因的电影。这些影片把不公正归咎于某些腐败恶毒的政治恶棍,他们扭曲了党的善意政策,从而伤害了老百姓。这些电影呈现出一种两极的道德模式,使他们的大部分主体得到好回报。 Paul Pickowicz(2009:321)在讨论谢晋的《芙蓉镇》的过程中,对这种还原和救赎的故事提出质疑:
情节模式为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提供了简单和易解的答案。它在一切都琢磨不透时,提供了道德清晰度。但是,通过将邪恶个人化,电影留下的感觉是,只要“邪恶”的人被剥夺了权力,被“高尚”的人所取代,那么一切都会变成好。
不像谢晋,他们的电影倾向于消除复杂的历史,第五代导演田壮壮在《蓝风筝》(1994)中努力揭露“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中的未愈伤口,未解之谜和未解决的紧张局势”( Ban Wang 2004:157)。《蓝风筝》谴责不断令人震惊并制造痛苦的致命的混乱思想和不透明的专制秩序。然而,普通人和普通家庭再一次被描绘成政治导致的灾难的受害者。张艺谋最近的电影《归来》(2014)提供了另一种受害的说辞。尽管《归来》与《闯入者》类似,提醒人们注意毛泽东时代的健忘问题和挥之不去的过去的创伤,但却淡化了个人利用宽恕与和解等理念伤害他人的道德责任。在《归来》影片中,一位前官员趁女主角丈夫在劳教所服务时性骚扰了女主角。丈夫出狱得知那位官员也遭到迫害后,向其表现出惊人的怜悯。就好似仍要追究他的罪行不再是必要的,甚至是残酷的。因此,历史和政治的邪恶掩盖了个人的罪恶,并将他们从罪责中解脱出来16。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强烈谴责了这种集体受害者的心态,以及由此造成的免除个人责任的结果。在她的《平庸之恶》一书中,阿伦特认为,即使在极权主义、恐怖或混乱的情况下,道德选择仍然是可能的,而且一个人必须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然而,大屠杀之后,人们倾向于泛泛而谈,而不是深入细节、针对个人。阿伦特(Arendt,2006:296)指出:“舆论允许我们判断甚至谴责的是趋势,或者说整个群体 – 越大越好 – 简而言之,那么一般的东西不能再做出区分,不再被命名“。那时,德国人民的集体愧疚和欧洲犹太人的集体无罪等流行的结构,被证明是对反对个人责难的厌恶。她反驳了这一趋势,尖锐地指出:“不存在集体犯罪或集体无罪的事情,如果有的话,任何人都不会有罪或无辜”(298) 。阿伦特的观念中有两个基本原则:个人在思考,道德上的人;他们应该为他们所做的事负责。
王小帅在《闯入者》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道德的审视,在历史暴力中要求自己如何行事17。电影中不间断的电话铃声和唤起幽灵的手段被用来唤醒和扭正人物的历史无意识和遗忘,“红色遗忘症”。只有恢复了对道德责任的意识,才能真正反思。在电影中,老邓重新记起了曾被压制的罪恶。被一股内疚的罪恶所推动,她踏上回贵州的旅程。尽管她的老朋友劝阻“算啦,都过去了”,她仍坚持拜访老赵的家人。老邓正在鼓起勇气敲门,老赵的遗孀徐芳开门,讽刺的是她第一眼都没认出这个“家族敌人”。老邓迟到多年的道歉,面对的是坚定的拒绝和打在她脸上的耳光——许多悔悟了的人都知道的命运。可能看起来吃力不讨好,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寻求宽恕是实现道德正义的重要步骤。老邓的反思和赎罪,就是希望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反思“文革”中普通人的责任。
不过,这部影片进一步戏剧化了这一与过去的和解的迟到的努力。在老赵的住所,老邓意外看到了她在北京遇到的男孩,他来问奶奶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一刻,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在北京尾随她的男孩是老赵的孙子,他曾试图为祖父报仇;这个男孩也是社区警方提到的闯入者和行凶的嫌疑犯。出于愧疚与同情,老邓决定不报案。但是,当她第二天再来准备道歉时,她看到一些警察向人打听这个男孩。紧接着一个老邓的跟拍镜头,她气喘吁吁,但仍继续跑着冲向老赵的住所,通知他们这个消息。这种长镜头表明了急切想要将年轻人从历史的残害遗迹中拯救出来的心理,和要达到如此的漫长路途之间的不平衡,更况是这个过程已被延缓了这么多年。到老赵家后,老邓要这个男孩赶紧跑,但是警察很快把他围堵到一个公寓楼顶的空间。爬上窗台,男孩威胁说,如果警察靠近,他就跳下去。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是,他手扒住的窗框脱落,他也随之坠落。影片随而切换到之前男孩空洞鬼魅般眼神的特写镜头,然后是老邓倒在地上的中景镜头,她被刚刚发生在男孩身上的事情所震惊。连锁反应发生了。老邓对老赵的举报导致了他的中风,摧残了他的家庭,促使了这个男孩的各种报复行为;他的坠楼是因果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虽然老邓为自己犯下的错来赎罪了,但是她做得太晚,造成的伤害已很难补救。更糟糕的是,她试图帮助男孩逃跑,反而加重了他已有的伤害。历史陷入了一个荒谬而恶毒的螺旋。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静止在空窗的框架上,透过窗框,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废弃的工厂建筑,这是被遗忘的过去的遗迹(图10)。最后一个镜头呼应了《青红》的开场镜头,也是一个半开着的窗户的镜头。但在《青红》中通过镜头拉近后所展现的,是一段与三线建设时期有关的青春的、思乡的、生活的记忆18。《闯入者》将视角固定在一个更加暗淡和毁灭性的点上。 这个男孩的坠楼在过去的废墟上增加了一个新的伤口。 结尾给观众一个沉重的打击,让我们想知道如何或者是是否可以将螺旋打破。
结论
通过幽灵萦绕的隐喻,《闯入者》提醒我们反思“文革”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下中国继续疯狂成为经济超级大国的时期。这部电影反抗当代中国健忘、前瞻性、不反思的社会潮流,显示出主角身上背负着的三线建设遗留物的程度,这绝不是过去无关紧要的事件,而是萦绕在现在的过去。《闯入者》因此在当今中国有了显着的历史性作用,它不仅重温了往往被忽略的历史时刻,而且标志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以及两者紧密联系的方式。
用遗忘来模糊这种联系,并不仅仅来源于对进步的狂热信念。这也是由于党的霸权控制,为了巩固其权力,党只允许某个过去被记住,同时压制其他不合适的记忆。用幽灵体现过去,出现在现在,《闯入者》隐喻地表现了这种企图强加遗忘的注定失败。对于那些在革命中幸存下来的家庭来说,它带回了不愿被提起的回忆,以及一种十分不舒服的关联。
此外,与以往大多数关于强调中国人受害群体的“文革”电影不同,《闯入者》拒绝普遍化,坚持特殊性。它不是重复熟悉的故事,而是讲述该为历史暴力负责的个人责任。幽灵的存在,从过去萦绕至现在,表明了历史的创伤不仅仅是人民在一个包罗万象的国家机构手中受害的结果,相反,个人,即使他们也是受害者,在这个历史浩劫中对他人施加暴力是有罪的。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这个幽灵萦绕的故事应该推动政府和个人都反思如何记住过去的错误,以及为何造成了新的伤害。
参考文献
汉娜·阿伦特. 平庸之恶[M]. 纽约: 企鹅图书出版社, 2006.
白睿文. 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5:162-181, “Wang Xiaoshuai: Banned in China”.
程青松, 王小帅. 对话: 潜行在现实 与历史之间的洪流之中. HYPERLINK “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vxea” http://yd.sina.cn/article/detail-iavxea fs6472773.d.html?vt=4&mid=awzuney0777426
查奕恩. 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2002: 209-229, “A Souvenir of Love”.
邓小平,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直向前看”. 郑培凯, 李文玺, 史景迁.寻找近代中国之史料选辑. 纽约: 诺顿出版社, 1999: 447-451.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德幽灵. 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1994.
弗兰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 国家利益杂志(夏), 1989:3-1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怪怖者”. Tr. James Strachey. In Vincent B. Leitch et al. 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 2001:929-951.
Gladwin, Derek. 2012. “No Country for Young Men: Chinese Modernity, Displacement, and Initiatory Ritual in Chinese Sixth Generation Cinema.” Asian Cinema 23, no. 1: 31–44.
Gordon, Avery. Ghostly Matters: Haunting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人民网: HYPERLINK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 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黃易居. Tapestry of Light: Aesthetic Afterliv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莱顿, 波士顿: 博睿出版社. 2014
李静君, 杨国斌. 斯坦福,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加利福尼亚: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7.
Letteri, Richard. 2010. “History, Silence and Homeles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Wang Xiaoshuai’s Shanghai Dreams.” Asian Studies Review 34 (March): 3–18.
Lu, Jie. 2008. “Metropolarities: The Troubled Lot and Beijing Bicycle.” Jour- 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57 (Nov.): 717–732.
Mathy, Jean-Philippe. 2011. Melancholy Politics: Loss, Mourning, and Memory in Late Modern France. University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2016. “Q. and A.: Roderick MacFarquhar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hina Today.” New York Times (May 3). URL (accessed 9/15/17): HYPERLINK “http://www.nytimes.com/2016/05/04/world/asia/china-” http://www.nytimes.com/2016/05/04/world/asia/china- cultural-revolution-macfarquhar.html.
McGrath, Jason. 2007. “The Independent Cinema of Jia Zhangke: From Postsocialist Realism to a Transnational Aesthetic.” In Zhen Zhang, ed., The Urban Generation: Chinese Cinema and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81–114.
Naughton, Barry. 1988.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rterly 115 (Sept.): 351–386.
Pickowicz, Paul. 2009. “Melodramatic Repres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Tradition of Chinese Cinema.”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95–326.
Stuckey, Andrew. 2014. “Ghosts in the Theater: Generic Play and Temporality in Tsai Ming-liang’s Goodbye, Dragon Inn.” Asian Cinema 25, no. 1: 31–46.
Teo, Stephen. 1997. “Ghosts, Cadavers, Demons and Other Hybrids.” In Stephen Teo, Hong Kong Cinema: The Extra Dimensions. London: BFI, 219–229.
Veg, Sebastian. 2016. “Debating the Mem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Today.” MCLC Resource Center Publication. URL (accessed 9/15/17): HYPERLINK “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eg2/” http://u.osu.edu/mclc/online-series/veg2/
王斑.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 Trauma, Memory, and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王德威. 历史与怪兽. 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2004.
王小帅. 2014a. 别再让我拿编剧奖了: HYPERLINK “http://xw.qq.com/ent/20140904008767/” http://xw.qq.com/ent/20140904008767/ ENT201409040087670B
王小帅. 2014b. 威尼斯专访《闯入者》导演王小帅 : HYPERLINK “http://news.mtime.com/2014/09/05/1531228.html” http://news.mtime.com/2014/09/05/1531228.html
王小帅. 薄薄的故乡.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
Weissberg, Joy. 2014. “Venice Film Review: ‘Red Amnesia’ Variety (Sept. 4). URL (accessed 9/15/17): HYPERLINK “http://variety.com/2014/film/festivals/venice-film-” http://variety.com/2014/film/festivals/venice-film- review-red-amnesia-1201297599/
Xu, Gary G. 2007. “‘My Camera Doesn’t Lie’: Cinematic Realism and Chinese Cityscape in Beijing Bicycle and Suzhou River.” In Gary G. Xu, Sinascape: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67–88.
Xu, Jian. 2005. “Representing Rural Migrants in the City: Experimentalism in Wang Xiaoshuai’s So Close to Paradise and Beijing Bicycle.” Screen 46, no. 4: 433–449.
杨俊蕾. 2006. 《影像记忆中的历史和个体:论<青红>的现实品格》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1: 101–105.
Zeitlin, Judith T. 2007. The Phantom Heroine: Ghosts and Gender in Seven- teen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Zeng, Li. 2013. “Ghostly Vengeance, Historical Trauma: The Lonely Ghost in the Dark Mansion (1989).”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7, no. 2: 109–121.
我非常感谢制片人刘璇允许我提前观看影片,并为这篇论文提供相关剧照。我也要感谢MCLC的编辑Krik Denton,以及另两位匿名评论家给予我的论文以有用的建议和见解。
1. 研究王小帅作品中对当代中国移民劳工的表现,可参见G.Xu (2007), Lu (2008), Gladwin (2012)的研究。 Xu观察了王小帅电影中象征性的和制度化的暴力移民所遭受的苦难。Lu展示了王小帅的乡村移民如何探索而照亮一个新的城市空间。Gladwin将关注点放在另一个方面:移民劳工在流动环境下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成长。
2. 东部沿海地区是战略上的一线地区,中部地区是二线地区,地理位置偏远的西部是三线地区。
3. 尽管网络上有关于这段历史的某些介绍,1980年代后也有更多相关报道文章,但在官方和文化语境中,三线建设运动没有被广泛讨论和呈现。
4. 王小帅(2014a)说:“在构思这部影片时,我没有任何思想束缚。也不觉得三线建设是影片最重要的方面。我只是想表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长久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对中国老百姓有深久长远的影响……所以我着手进一步调查文革带来的创伤后果。”
图1: 老邓收到沉默的电话
5. 黄易居(2014:76)指出,培育向前看的文化并不妨碍回顾过去。实际上,当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激增的怀旧思潮。李静君和杨国斌(2007:1)指出有种新兴的以怀旧情绪为特征的“记忆产业”。虽然怀旧揭开了随着不平等与社会不公平而上涨的、对尤其是经济改革受害者的不满情绪,但它倾向于美化过去而不是批判地审视过去。
图2. 男孩在闯入的又一户人家家中打发时间
图3. 电影开场镜头,荒废的建筑
6.这个场景中的场地也是十年前拍《青红》的场地。(王小帅 2015:166-168)
图4,5. 谈话间,老邓丈夫的幽灵突然出现
7. 根据王小帅所言(2014b),这个男孩的沉默代表他边缘的社会地位。沉默的男性角色是往昔哦啊摔电影中的一个形象特征,比如《扁担·姑娘》中的冬子,《二弟》中的二弟,《十七岁的单车》中的阿贵,他们的沉默与他们在城市环境中的异类身份相伴相随。
8. 德里达(1984:10)。德里达所说的灵魂的很好的体现,是马克思的幽灵,他的理论和实践被认为不再相关。但德里达提醒我们,马克思的灵魂一直都会回来。持续回来的终止,如同Jean Philippe Mathy (2011:38)指出,“防止经济自由主义的没落成为历史的终结,这将使任何惊喜、反叛和运动都变得不可能。”
9. 即便在2016年,文革运动发起50年的纪念日也被大面积忽视,国有与流行媒体都对之视而不见。
10. 历史类杂志《炎黄春秋》近期的调整与最终休刊,说明了对与共产党政治观点不同的见解的新的镇压。Sebastian Veg认为政府是觉得受到了威胁,因杂志可能提供“更实质性参与文化大革命引发的最为困难和有争议的问题“的机会。
图6, 7. 男孩像鬼影般跟随老邓
图8. 男孩躺在老邓身旁,老邓握住他的手。
11. 某种程度上,因受到儿子儿媳的拒绝,老邓将对自己孙子的爱投射到男孩身上。当她邀请男孩去家里吃晚饭,她做了狮子头,说这是她孙子最爱吃的,但可惜,她儿子儿媳并不喜欢给她孙子做狮子头。
图9. 老邓家的照片被撕碎,散落在桌上。
12. 复仇是中国鬼怪类型片中的核心主题。如Stephen Teo(1997)指出:大部分中国鬼片描述了归来者要的复仇和受害者的毁灭。
13. 男孩最开始的复仇动机让人想起另一部著名恐怖片《黑楼孤魂》(1989),也是跟文革创伤的鬼魂萦绕有关。影片中,十几岁女孩的鬼魂回来为被迫害的父母和被谋杀的自己复仇。与《闯入者》中男孩的萦绕相似,女孩对于历史正义的不懈追求违背了官方对历史创伤的叙述。然而,虽然《黑楼孤魂》的故事随着女孩的复仇达到高潮,但《闯入者》在推动忏悔赎罪上走得更远。对《黑楼孤魂》得研究,可见Li Zeng(2013)的研究。Li Zeng指出,这部影片讲弱势群体的女性接近文革的历史创伤,拒绝认同男性英雄是历史叙述者和女性被害人的拯救者的概念,反而主张女性在揭露未愈合的伤口和执行历史正义的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
14. 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URL: < HYPERLINK “http://cpc”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48.html>
15.《决议》谴责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却没有质疑他所创理论的公正性。毛泽东思想仍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这部影片还用感人的浪漫故事来减轻创伤过去所造成的痛苦和苦难。但值得注意的是,因无法治愈女主角心理的伤害,失忆恰好证明了此种感伤主义是对创伤的的无效处理方式。
影评人往往忽视了王小帅在《闯入者》迈出的更远一步。比如 Joy Weissberg(2014) 仍只将影片定义为对文革的一般批判,他说“电影含蓄的批判不在于对老邓个人,而在于对文革的肇事者。后者的扭曲混乱的实验导致如此多的死亡和长久的痛苦。” 实际上,老赵在影片中不仅仅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尽管他的确受到了老邓的伤害。如同军和兵的对话中所言,老赵跟他们母亲一样,也是各种文革中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也伤害了其他人。
男孩坠楼后,空窗框的静止镜头
《扁担·姑娘》中的怀旧情绪类似于Jason McGrath所说的“反思性怀旧”。McGrath写道,”[反思性怀旧]来自于矛盾的个人和文化记忆,并包含了模糊、距离、讽刺和作为思考对象不可分割的碎片。”(2007,100) 没有打造一个自满和安心的过去,王小帅在《扁担·姑娘》中关于三线建设的回忆充满了矛盾、紧张和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