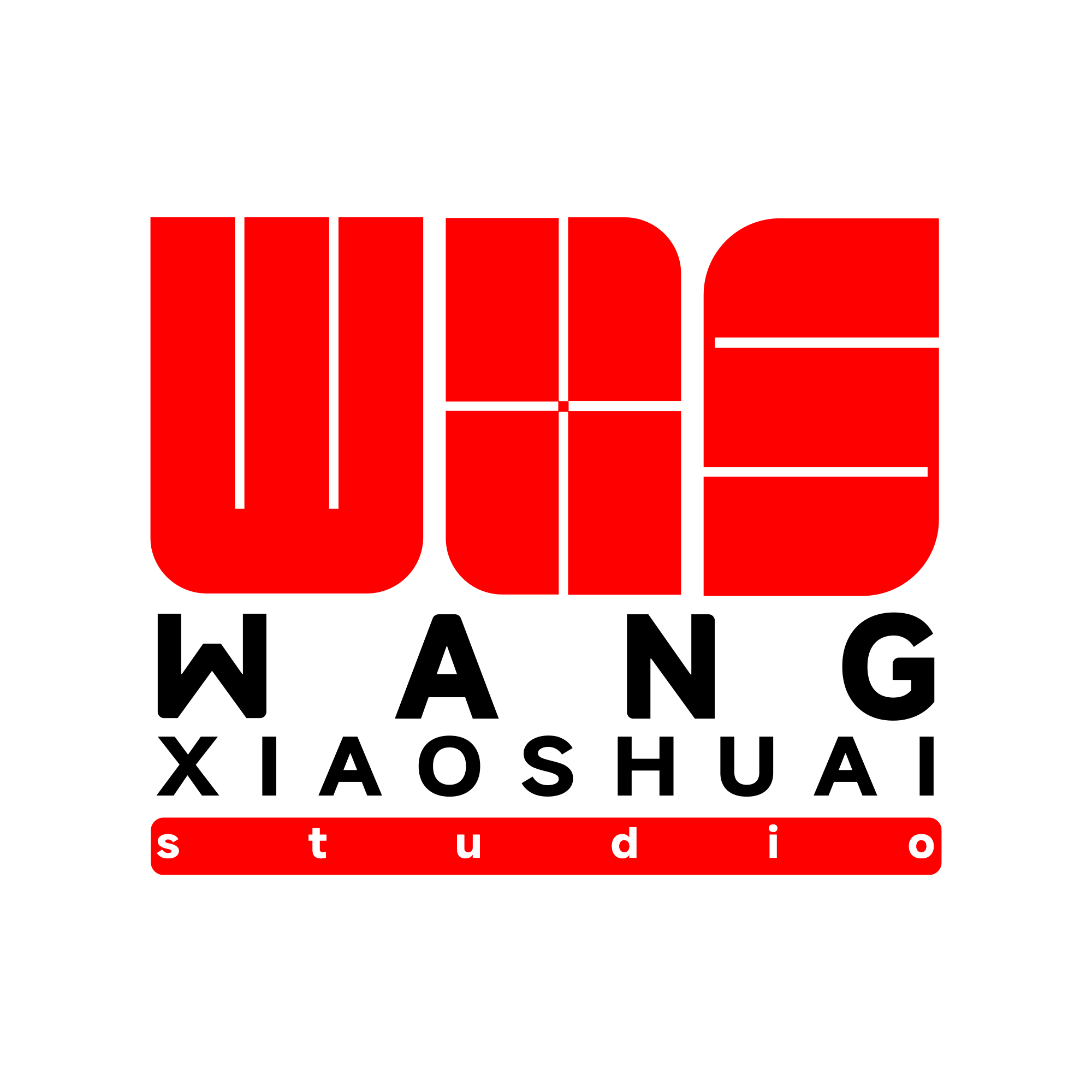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影坛,可谓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创作的分水岭。随着第五代导演从边缘到中心,从底层到上流地位的改变,他们不仅失去了观念的前卫性、艺术的创造性,更失去了对生命与生活的新鲜体验。第六代崛起之初便将目光落在当下与民间,以平民之态叙写平民之事的创作理念使其作品成为一份独特的中国底层社会民众生活的影像文献。
2005年,长期存活于“地下”,奔走于各大国际电影节以求得“他者”认同的第六代导演终于迎来属于他们的第一缕灿烂阳光——贾樟柯的《世界》、王小帅的《青红》顺利通过审查,第一次步入国内院线,正式与观众见面。《青红》还荣膺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奖。这一天,距王小帅自筹经费拍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正好是十二年——一个轮回,也是这一天,王小帅迎来了他的三十九岁生日。这一切,都让人不能小视王小帅和他的《青红》。
青春与梦想见证人生之荒谬、无常
第六代影人初执导筒之时,大都是到自己的家乡去拍摄其电影处女作,像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章明的《巫山云雨》等,而王小帅却是在结束了《冬春的日子》(1993年)、《极度寒冷》(1997年)、《扁担·姑娘》(1998年)、《梦幻田园》(1999年)、《十七岁的单车》(2001年)、《二弟》(2002年)等六部作品之后,才将目光投向他生活了十三年、记忆中的第一故乡——贵阳。《青红》描写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贵州支边家庭中十九岁女孩青红的第一次情感经历。她的初恋对象是一个刚进工厂的临时工,当地男孩小根。对于青红的父亲而言,离开贵阳重回上海的梦想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他粗暴地摧毁着刚刚萌芽的爱情。影片结尾时,青红和她的父母、弟弟挤在一辆吉普车中,在一个清晨偷偷逃离贵阳,他们的身后传来清脆的枪声,那枪声暗示着一批生命被严打——其中就有小根,在爱的梦想破灭之后,他强暴了她。吉普车载着半疯狂的青红绝尘而去……
《青红》延续了《二弟》中对普通人生存境遇、人生愿望的关注和《十七岁的单车》中对残酷青春的风格化抒写。在时代潮流的裹胁之下,青红的父母被抛置到离家千里的偏僻内地贵阳,像无根的浮萍。父亲的上海梦是可以理解的,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上海是他眼里的世界,梦里的繁华,回到上海重新开始生活是他下半辈子的唯一支撑。正是出于这样一份重新选择人生的心理渴求,他像押解犯人一样监管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尽管是荒僻的贵阳小镇,阴雨绵绵的窄巷中、沟壑纵横的山丘下,依然有爱情在潜滋暗长。哲学家怀特海曾给青春下过一个定义:“青春就是尚未遇到悲伤的生命”。然而,当少男少女青春的梦想与父辈们改变命运的人生梦想纠结在一起的时候,产生的不仅仅是悲伤,甚至是巨大的灾难,它见证的恰恰是人生的荒谬与无常,这或许就是那个谁也挣脱不了的叫做命运的东西。现实如此残酷,残酷到最后一切都变得支离破碎,有人在此结束了青春与梦想,有人却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影片中小根的一个面部特写镜头尤其打动人心:当他扭头看到停在工厂门外的警车时,镜头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钟,那上面写满怀疑、恐惧和绝望,这或许就是对人生荒谬本质的读解;结尾处,颠簸的吉普车里、昏暗的光线下、刺耳的枪声中,青红迷离的眼神昭示的恰恰是人生的无常。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的才女张爱玲就曾借她笔下的人物范柳原之口说过:“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青红》对人与命运的反思太沉重了,让人不由生出对生活意义的质疑,并为之深深叹息。
人物:“时代的囚徒”作虚妄的挣扎
在第六代的影像世界里,时代,向来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记载的就是小城的变化、人心的迷茫和时代的变动。2005年新作《世界》将京城西南一隅的世界公园作为时代与文化的载体,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里呈现出当下中国种种复杂性况味。世界公园的文化寓意相当明确,它是一个假的空间,相当于今天的现代化,它只是给人观赏的,很多人走不进去。当成太生骑着高头白马踌躇满志地在夜色中巡游、当赵小桃身穿崭新的空姐制服坐在废弃的图—154 客机的机舱里时,也许会产生一刹那的眩晕。然而,虚拟的浮华与卑微的生存真实恰好形成反讽。如果说《世界》揭示与诠释的是尚未过去的“历史中的现实”的话,那么《青红》记录的就是刚刚过去的“现实的历史”。不同于《世界》的文化寓言式构想,《青红》中真实的时代烙印随处可见:广播体操、地下舞会、高跟鞋、喇叭裤、日本电影《阿西们的街》。诸如此类的时代细节很能勾起人们心头的怀旧情结,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但是当记忆的潮水退却之后,只有活生生的人与人的命运真正记录下时代的脚印。
《青红》的叙事表层展现的是父女冲突,父亲心心念念要重返上海,女儿已全然“反认他乡是故乡”;当父辈们拼命为下一代谋求一种身份认同的时候,年轻一代却为抓住青春的脉动而奋力挣扎。表象的背后包蕴的是时代沉浮中个体的身不由己:女儿被父亲严管着,父亲被政令牵动着,女儿失去了那个时代最为宝贵的贞操,父亲的愿望似乎实现了,可逃离后的一家人又将以怎样的心境面对未知的生活?影片以看似开放实则残酷的结局传达出更为深刻的人生绝境。正像影评人程青松所言:“他们像一群囚徒,时代的囚徒,被流放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做疯狂的挣扎。”这个在传统意义上表现父女冲突的故事之所以不同寻常,正是因为它独具文化内蕴的时代背景。王小帅在片头片尾不忘打出字幕,将影片献给跟剧中父母有同样背景的,曾在“三线”基层饱受苦难的自己的父辈,其创作用心由此可见一斑。戛纳电影节评审团主席艾米尔·库斯图里卡这样评价《青红》:“从古典角度讲,表现历史如何影响个体的生命,社会如何影响人们的家庭,《青红》是最强烈的。”然而,导演是如此强烈地想把自己经历过的时代对人的影响表现出来,以至于将“时代”推到前台主角的位置,人物反倒成了后景和烘托。片中,父女间的冲突与对抗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包含着人与时代的对抗,人与命运的抗争,它应该是激烈暗涌的,在特定的时代阴影下,人物的内心可能灰暗,但绝不是不丰盛,但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永远是粗暴愤怒的父亲、沉默懦弱的青红。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小帅的《青红》和顾长卫的《孔雀》都在回顾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集体记忆,《孔雀》中人物的精神气质可以够得上丰满,姐姐的理想主义、哥哥的实用主义、弟弟的虚无主义表现得相当充分,而《青红》里的人物则多少显得有点平面和空洞。深究起来,这还是故事本身的问题。片中对父女冲突铺排式表现的是父亲的咒骂、抱怨和对女儿的跟踪围堵;对青春与残酷的设置也是司空见惯的送情书、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偷偷约会、偷尝禁果、怀孕、离家出走等等。青红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多是间接通过小珍和李军的自由恋爱来体现,男女主人公之间恋爱的情节线缺少更充分的铺垫。整部影片情节、节奏显得臃肿、拖沓,以至于最后的离开与枪决显得分外刻意,无法给人带来高潮与震撼。王小帅是个优秀的导演,但作为影片的编剧之一,他对故事的营构还缺乏想象力与创造性。
在冷峭中体察生活的电影品格
对于第六代的浮出海面,人们常会不自觉地在其创作中寻找“改变”的蛛丝马迹。这在贾樟柯的《世界》中有着清晰的显现。影片中除了时尚化的电子配乐,还有多处flash的插入。据贾樟柯讲,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配合电影的市场需要。从表现手机短信这个角度看,不管flash的制作效果有多粗糙,都要比对着手机拍一条或者出条字幕聪明得多,但它的出现还是显得突兀。这恰恰反映了贾樟柯和他电影中的主角们一样,面临着进入商业社会与另一个世界的困惑。《世界》所要表现的荒谬和忧伤有着一个十分严肃的内核,而动画运用多少削弱了观众对沉重的社会主题的思考,而且由于是多次穿插的形式,对影片的连贯性产生了相当的破坏作用,并与影片总体的写实风格相抵触。同是表现逝去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顾长卫的《孔雀》寄寓了导演太多的理想,它华丽、唯美,沉重中带着轻盈,残酷里透着纯真,色彩浓烈,长镜头充满旖旎的光彩。《青红》则延续了第六代电影惯常的纪实风格,王小帅用实景拍摄、自然光效、混录音效、长镜头所构成的简单却又极具穿透力的笔触,在最庸常不过又是最难规避的人生起落里道出我们日复一日,终难摆脱的人生困境。这里有较为冷冽的家庭关系,夫妻之间、父女之间没有起码的尊重与被尊重,在暴戾、埋怨、争吵中虚度光阴;这里,最动人的爱情被粗暴地虐杀,就像那夜色下散落在山丘上的两只红色的高跟鞋;这里,人的仅有一次的生命被践踏、摧折……王小帅在《青红》里捡拾起被许多新锐导演弃用的线性叙述,在一个家庭内部的生活实景里以不逼近的姿态示人,正像片中的中、近景一般,若即若离地观望着,色调偏冷,但冷得不彻底,保持着略带酸楚的冷峭。这种不干预生活,却能进入生活实质的电影品格,在《青红》里得到稳健的建立。王小帅从来不愿意充当一个浅薄的声嘶力竭的发言者,而力求成为一个体察者、一个观察家,这使他拥有了更为广阔的艺术表达空间。
《青红》真实而坚定地将个体置于人类史的长河中,并远远眺望他们的漂流。王小帅说:“希望能为观众带来伤痛后的珍惜与平和,回望与宽恕。”然而,阿诺德·豪泽尔也曾经说过:“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直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人物,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求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在通过美学方式谈论社会话题的艺术实践中,更为重要的让人们在洞悉之后获得救赎般的力量与希望。我们期待王小帅、贾樟柯等第六代影人继续其关注人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创作立场,并努力将作品升华到对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探寻、对人的整个精神世界的写照及未来出路的回答。
来源:《电影文学》(长春)2005年08期第2~3页
作者简介:朱洁,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