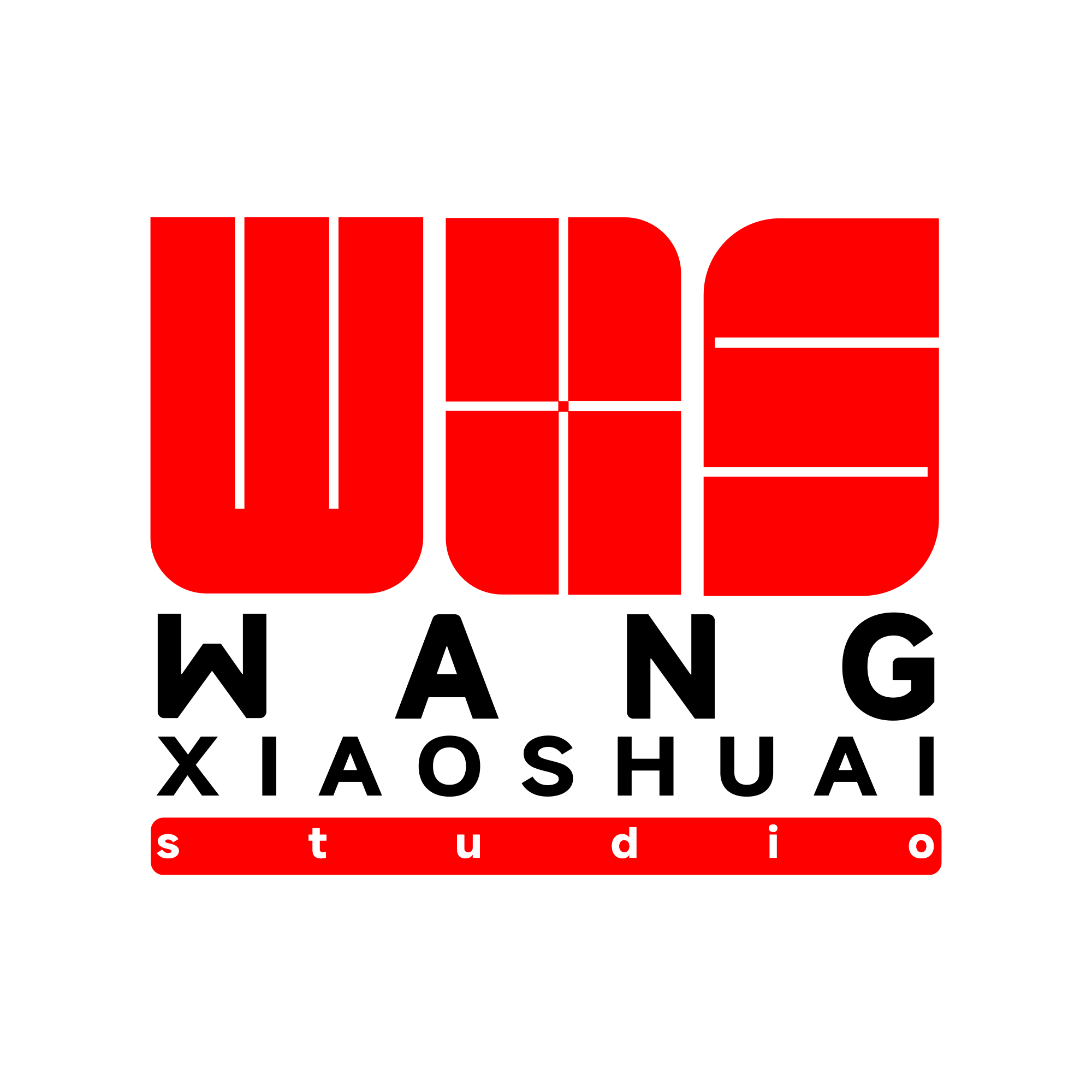Paul Kendall:请问您怎么对“三线建设”感兴趣?为什么三部电影都是“三线”题材的?
王导: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我从小是跟着我父母去的,我母亲的工厂原来在上海,上海光学仪器厂,在65、66年的时候搬过去了,等于是从一个单位去支援的三线建设,我妈妈是工人其中之一所以过去了,我爸也就跟着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出世。
Paul Kendall:是那个新添光学仪器厂?
王导:对,到那改成了新添光学仪器厂。几乎原来上海光学仪器厂有一半的职工都过去了,我妈妈就在其中之一。因为我刚刚出生才几个月,我父母没有办法分开,我父亲就自己的工作也不要跟着去了。我父亲原来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表演和导演的老师,也就中断了他的舞台和演员的工作过去了。所以我是从小在这个新添光学仪器厂、在贵州长大的。
Paul Kendall:那这个厂搬到贵州的时候是搬到哪里?是在贵阳吗?
王导:是在贵阳的郊区,那个地方应该叫新添寨。
Paul Kendall:哦,我知道,乌当区。
王导:乌当区,对,现在扩张了以后看起来应该跟市里面很近,那个时候感觉完全是在山里、郊区里面。
Paul Kendall:083的厂他们现在已经搬到新添寨了,原来在凯里。
王导:现在083搬到新添寨去了?
Paul Kendall:对,他们也在乌当区。
Paul Kendall:国外媒体认为您的“三线三部曲”的主题是以文革为背景的,他们并不知道三线建设,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导:因为当年拍青红的时候,应该说整个中国大部分人不知道、也没有人提,包括文学作品、纪录片、一些影像、还有电影,完全没有人提过,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我是从三线出来的,我们、以及很多人这样的生活经历是不被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去拍这个电影向西方介绍的时候,他们就更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我做了很多的解释,但是因为这个三线的建设是始于1965、1966年,整个到了1978年差不多也正好是跨越了文革的十年,基本上发生在文革期间,所以很多人就简单地把它跟文革结合在一起来说。那也确实正好赶上了文革这个背景,所以他们的评论我没有办法去一个个解释,只有他们通过一些更细的方面去了解。现在有比较了解我的人就开始越过文革知道有一个三线的建设,有些人开始慢慢介入和知道了。
Paul Kendall:国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影像作品是有关“三线建设”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导:对,当年做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主要因为是在戛纳电影节拿了一个奖,回来以后这边的反响和影响还是很大的。有上千万的三线的职工都想要看这个片子,甚至想要写信给中央,说要重视我们、我们现在被遗忘,在那个时期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轰动,所以有人开始知道有这么一个事。然后陆续就有像凤凰卫视,也开始做一些纪录片。后来有一个摄影,拍照片的,也到那地方去拍一些照片,然后这个事情就有一些人知道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小部分,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
Paul Kendall:“三线建设”还是保密的,除了您自身对“三线建设”的记忆外,您是通过什么途径对它有更深的认识?
王导:我因为在那长大,心里是比较清楚的,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自己的家人,旁边的大人,他们的经验、感受,作为一个生活在那的家庭,对那个东西有一个自己切身的体验。这个是一部分,不能说是全面的三线。而实际上我在拍片的时候在电脑去查这个资料,还是有一些的,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大家不说,所以这个三线就有除我孩子的记忆以外的一些官方的报导、介绍。那么当然了,从官方上看到的报导都是相对比较正面的,说那个时候因为要打仗,苏联、或者南海、越南等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就大面积地转移军工企业,可能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大部分的机器、基建的设备就建设起来了,那么大家都去了。这是官方的一个基本的报导,还是很详实的,多少人、怎么在那建设、到几几年开始不行,这些都还是有的。(但是一般这样一种报道性的东西不会带有过度的角度,比如完完全全的好、或者可能是人为的一次浪费,不会这么去说,更多的当然是说工厂到了西南,是帮助了大西南山里面整个社会和工业的起来。)
Paul Kendall:您认为“三线建设”的工厂与当初60-80年代的工厂有什么区别?
王导:其实为什么在西南一代去做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原先西南一代的工业就不是最发达。中国最发达的工业是在东北边、华北地区、东南地区,这个地方稍微弱一点,所以那么多高端的工厂进到那完全就是在一个我们说的工业的处女地,空降这么一个高科技的。当时作为高科技的大工厂的范围来说,刚开始它给大家带来的当然是一种新鲜感,当地的贵州人或者四川人过来一看,哪儿来这么多人,就会很羡慕。在工厂的大门你可以穿着工装去上班、下班,当地的人是没有机会进去的,所以他们对那个时候的工厂是非常羡慕的。而且有钱,因为那里的工资一个月六十几块钱,在当时的生活来说很好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些工人和当地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工人要买他们东西,工人很有钱,农民就种地、杀猪卖给工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到后来文革以后,慢慢这个工厂转型、就不行了,那不行了以后,工资就发不出来,而中国在76、77、78年以后改革开放,当地人开始变得有钱了,时间长了以后,工人的工资一直是那么低,而当地的人慢慢有钱,就倒过来了,工人就显得很低三下四的,要去跟当地结合。一开始是自己一个很独立的王国,有自己的医院、学校、食堂等等,是一个小社会,几乎跟外面的人不怎么打交道,到春节、节假日,大家家里有点钱的还要坐火车回到上海、北京的老家去看一下,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关于为什么要去西南一代,其实还有一点是为了备战,大山深处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工厂从一开始的建设到设想是,万一打起仗来可以有中国保留的军工实业,包括甚至能够带动当地,但是实际上真做起来了就发现远远不是那么简单。虽说我们去的都是很有水平的知识分子,但是到那边毕竟条件很差,什么都没有,也比较原始,从德国或者美国找来技术再自己弄了以后,它交通又不方便,都是很精密的仪器,像我们的工厂是做望远镜的,潜艇有个在海下面看的潜望镜,是很高精度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就会牵涉到一个运输的问题,还有很大的精密仪器,因为都是临时造的路,路也很不平,又在深山里面,每次要把原材料运进去,生产完了还要颠簸出来,所以产品的质量什么的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本身文革又是很困难的时候,所以发现慢慢到了后来市场化以后就没有竞争力了,因为运输成本、人工成本高了,跟真正在大城市或者沿海城市的就没法竞争,所以一点点就没落下去。
Paul Kendall:您刚刚说“三线建设”的厂区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就像《我11》的故事都发生在厂区里。那您小时候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王导:我们因为在一个小社会里面,小孩子也小,几乎跟外面当地的小孩既不认识、也不会玩。我们经常是离开家在边上玩玩,只要再往前就出我们的范围了,越过这个范围就是当地人了,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跑到那就回来,很少出去。我们要出到比如说新添寨,虽然也是一个很小的寨子,一般也都得跟着父母去,自己过去大家就很不敢。跟着父母去买菜、去看看,然后就从新添寨回来这样子。所以它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
Paul Kendall:在八十年代初,就像电影《青红》那样,当地人也有一些在工厂工作,他们和“三线建设”人员产生了交往,貌似有一些矛盾、还有结婚的,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导:我们小孩比如说玩的时候,只要沿着山出去到了接近他们那个地方的时候,山上的当地孩子就开始扔石头、扔土块啊(笑),噼里啪啦就打。我们在山下也上不去,所以我们就只是这样一种交流。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放电影。因为是露天电影,放电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控制了,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电影,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空场,拿着我们的椅子板凳坐在正面看,那很多的当地人没有办法和我们一起看就会在后面的山上,还有边上的山坡上、荧幕后面的山上,都坐着当地的农民。所以就形成我们在下面,他们在上面,有的时候上去对骂一下,追上去,他们下来,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在文革那个时期,当地人对工厂的工人还是觉得你们高高在上,非常敬畏、敬怕的,后来到了70年代末文革结束了,再到78年改革开放,原有的工厂迅速的改变、等于说是放弃了,因为竞争不好,好多的技术工人到那发挥不出来,青春都浪费了,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工人觉得我不应该在这呆着了,你看《青红》里面,到85年以后,那个是最困难的时候,改了以后国家不管了,就需要自己跟市场去打交道,去生产、去卖,那一下子就显出不行了。原来是生产完国家拿走,那个时候不行了,就开始一点点走下坡路。开始走下坡路,很多的工人就开始想这个问题,我们工资也低了,现在改革开放外面的工资也高了,我们怎么办?要不要回老家?因为上海是全中国最好的地方,我们离开了过后要不要回去?很多人在想办法,想要回去,想要离开。从78、79年开始,有个别的人家、包括我们家有机会就离开了,后来到了80年代、就是《青红》那个时候,出现了很多的人往外走,不愿意待在这里了,他们走了以后,这个工厂因为已经是私人股份制、像公司了,就开始对当地的人招工,当地的人觉得,哇,可以进工厂了!因为上海人走了,所以就有一些当地人进厂,就慢慢地融合进来了。同时还有没有走的人,像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比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就去上大学或者是技校,有一些上大学的人离开了那个地方,不管是到贵阳大学读书还是到什么地方的大学,考上了以后就离开了,通过离开就跟当地人开始有了交往。那个时候十七八九岁的年轻人,读大学认识了当地人,等到毕业了以后有机会出来就不回这个工厂了,就留在了比如贵阳、乌当区、或者贵阳市里面,然后就在那里才开始真正的和当地人交往、接触、甚至结婚,反正也知道回不去,就结婚了。年轻人,有了爱情就不愿意回北京、上海,那么就发展成如果和当地人结婚了,那些家庭相反就好过一些,因为离开了这个封闭的圈子出去了。中国毕竟是关系社会,有了关系,认识了人,慢慢他们就可以在那里过相对好的生活,可以挣到一些钱。那还有一些比较保守不愿意出去的,像我们这些孩子可能没有读到大学,没有考上,就读技术学校。读技校的主要的原因就是读了以后直接就能留在工厂,那个时候虽然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还是相对老的。至少工厂是保险的,每个月有工资可以拿,你出去做生意要是赔了怎么办?没有本钱做生意怎么办?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愿意在工厂,我们叫铁饭碗,就在那呆着。很多读技校的这些人就回来,爸爸妈妈早点退休,他们就来了,在这工作。这样一来就等于世世代代,上一辈在工厂,下一辈也在工厂。那时候这样一部分人就比较困难一些,因为要看工厂,工厂不好,没有生意、没有订单,他们就没有工资,所以有过一段很悲惨的境遇。
Paul Kendall:工厂除了上海人和当地人以外,会有其他的群体吗?比如说返厂知青?或者退伍军人?
王导:比较多。因为它还是一个技术性的工作,没有当兵的,但是会有各地方的人,比如我们这个工厂,是从上海去的,但是本身在上海的时候工厂里也不见得都是上海人,有的是毕业了分到那里去的,有的是东北的,有的是北京的,有的是南京的,他们组合了这样一个群体。像我们工厂,虽然主体是上海人,官方的语言是上海话,但是各个家庭的组成有北京来的、东北来的,大家只是在一个统一的语言系统里面可以交流,但是回到家,还是遵循着各自北京人的传统、东北人的习惯,怎么做吃的各自还是有自己的习惯,其他地方,像四川、甘肃啊什么的也都有。有的整个是东北的工厂直接过来的,有的是北京的工厂直接过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去拍电影,看到一些工厂,一进去,都说东北话(笑)。都是从辽宁、抚顺过去的,所以你跟他们讲话就好像去了东北一样。东北人讲话和上海人一样,永远不变,他不管到哪他就是都说东北话,所以老少几代全是东北人,习惯也是东北人的习惯,吃大锅炖什么的,就很有意思。
Paul Kendall:我觉得《我11》里面的那个厂特别集中,而《青红》会分散一点,会靠近城市一点,您当初拍摄的时候是有意这么设置的吗?
王导:也没有,拍《青红》的时候已经是04年了,拍《我11》的时候就11、12年了,其实到了04年的时候我就比较着急,因为中国变化太大了。从78年慢慢开始做房地产,工厂开始撤离,有的人开始离开,那个地方的环境改变了,你要去拍电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回到那个时代了。我们只能回去以后找了很多地方,寻找改变还比较少、没有完全被高楼大厦弄没了的地方去拍。所以《青红》是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环境相对还保有过去特色的地方。我们原来的工厂我其实是很想去拍的,但是现在那个地方看起来离贵阳挺近的,小时候觉得远,但现在从市中心到乌当区已经很繁华,新添寨已经像一个城市一样了,所以我们那个小区域其实都被侵蚀、侵占,没有了。过去的山上已经被老干妈集团那个家族盖成了别墅,有几个房子还留着,但边上新楼已经围上,所以拍摄的条件已经不允许了。等到《青红》拍完我再去拍《我11》的时候,原来《青红》那个工厂其实也很不欢迎我们去拍,因为那个时候拍的很困难,所以他们不欢迎我们去拍。再去拍的时候,就只能借助一点点他那个地方,大部分再去找一个新一点的环境。三线厂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就去寻找保存的相对还比较完整的一个去做。
Paul Kendall:所以这两部电影都是在贵州的三线建设的厂矿拍的?
王导:这些厂矿基本上都是三线建设的厂矿,但是也有一些是国民党时期的。蒋介石那个时候也做了一些工厂在那里,留下来一点。
Paul Kendall:难怪他们不大欢迎,哈哈。
王导:他们很不欢迎,因为他们对拍电影是很惧怕的,怕我们去搞新闻联播。他们的那些工厂一方面是军事,083、几几的代号都是军事,虽然已经解除了,但他们以前的这个军事的保密习惯不许你们去做。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拍《青红》的那个厂,它效益很不好,非常穷,他们怕你们去拍了以后好像把他们很不好很穷给宣传出去了,所以就不欢迎你去拍。
Paul Kendall:影片《青红》里面有很多的文青少年,他们听迪斯科,还看日本电影,当时这些元素是怎么进入“三线建设”地区的?
王导: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工厂在那个地方,厂长、大家都是上海人,心里有一种上海的情节。我们从上海来到这里,上海人过着上海的生活,上海有电影院,有吃的更好、穿的更好的东西,这边没有,怎么办呢?大家互相之间都有一个想要过好日子的心情,上海人嘛,所以就会安排比如看电影,所谓的给工人一天福利。那个时候的福利就是文艺活动、看电影,这是全国最普遍的。那么也是他们来组织,把那些电影调到工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三线厂普遍看电影看得比外面多。每个礼拜天都会放电影,一直放了很久,放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工厂变了就不放了。随着时代的变化放不同的电影,最早的电影可能放到南斯拉夫电影、阿巴尼亚电影、朝鲜电影,然后再放到日本电影,它是这样的一个演变。
Paul Kendall:当时工厂会公开放映日本电影吗?
王导:后来,一开始是没有的。一开始都是苏联电影或者是阿巴尼亚这种社会主义电影,等到《阿西门的街》,已经进入80年代以后了,开始接触,大家就开始看到这种电影。因为工厂当时的情况是,大家虽然生活在这里,但是向往更好的日子。所以后来到了76、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78年开始变了以后,有好多像上海、广州,南方一些新的东西就进来了,比如说穿衣服的样式时髦、新潮一点,我们那个时候流行喇叭裤什么的,虽然我们是在工厂里,周边这些乌当区的人还不知道这一切,但这边是上海的一个小的社会,所以他们的亲戚朋友就有这个信息过来,比如有亲戚是在上海、广州的,写信说外面怎么样,看你们在那很辛苦,寄点布料给你,或者寄一个新的衣服给你,就是这个把贵阳隔开单独跟外界再有一个联系。所以那个时候,收音机、录音机,或者新的裤子、衣服、食品、磁带什么的,就是这样到这个工厂里来的。
Paul Kendall:所以虽然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还是有这种城市文化。
王导:对,很重要的就是,虽然很偏远,但是在这个工厂比较稳定的十年里面,这些工人还是想尽办法去过一个曾经有过、或者和上海很接近的生活。想要去追求这样的生活。
Paul Kendall:有些学者认为“三线建设”是一种城乡之间的社会,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导:怎么说呢,也发明不出一个词去描绘这么一个特殊环境的群体。也不算城乡,因为其实完完全全是在乡下,像遵义、083,要开两个小时进山里面,我们完全是在山里面形成这么一个小的区域。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城乡之间,应该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包括人的思想模式还有生活方式,像东北人到那不变,我是在当地买的猪肉,我做的方式还是东北的。
Paul Kendall:我注意到您的影片《青红》中工厂与工厂是有矛盾的,那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导:那个是小年轻。因为小孩子小嘛,所以他都是在自己的一个范围里面,远处那个厂就只是听说或者是有一些交往。我记得那个时候,去那边看电影都要小心一点,因为不认识那边的人,小孩子很容易干架。不认识,所以这样。大人之间我就不知道,因为两个厂之间还是有一点关联的,但是跟其他厂就没有关系了。当时我们新光厂和赤光厂是配套的,新光厂主要来,然后赤光厂生产另外一种东西是配套这个新光厂的。赤光厂来得晚,好像小一点。
Paul Kendall:兄弟单位。
王导:对,兄弟单位,我们新光厂可能会有点看不起赤光厂。那个时候还配备了像肉联厂,就是因为去了以后要吃肉。我们那个时候、文革期间,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叫禽肉什么、鸡鸭肉联合的这么一个制造厂。
Paul Kendall:我知道还有一个公车站到肉联厂的。
王导:对,供销关系,肉联厂是单独配套这个工厂的这样的一个单位。
Paul Kendall:我看到有篇英文的导演陈述,其中用了village这个词来形容“三线建设”地区,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导:不是village,不应该这么翻译,应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山区里面,不能叫village,是新建起来的,根本没有village,对吧?
Paul Kendall:对。
王导:所以没有词来表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不应该叫village,也不能叫城市。
Paul Kendall: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可能英文没有这个词。
王导:没有这个词,对。
Paul Kendall:翻译不了。
王导:翻译不了,是的,就factory什么,zone什么。
Paul Kendall:factory,是的。
Paul Kendall:我注意到您的影片《我11》与《青红》的环境音中有很多火车的声音,是有何寓意吗?
王导:火车其实我们在真正的工厂确实很难听到,但那是一种我们小时候对于火车的向往。因为我们从小睁开眼就在山里面,不知道城市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上海、北京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其实向往的、想象的很多。我们从小虽然在山里面长大,但每个人、每个小孩都觉得我是上海人,因为爸爸妈妈是上海人,他们长大以后就觉得自己是上海人,只是没有去过上海。所以有很多家庭,稍微条件好一点的,都是在春节或者什么买火车票带孩子回上海,所以那个时候火车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一个连接。飞机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汽车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公路,就算有汽车也是公家的,所以我们没有私人汽车,唯一的是火车。作为我来说,我去过北京,因为我妹妹要生在北京,然后我自己动手术要去北京,小的时候唯一的就是火车,等于说要两天两夜在火车上一直开到北京。是这样的一种向往。我最喜欢、觉得最好吃的饭就是火车上的饭,我们那个时候叫盖浇饭。
Paul Kendall:哦,盖浇饭,知道知道。
王导:盒饭那时候是十块钱一份,对于那个时候来说是很贵的。但小时候就觉得那个饭是最香的,里面这个菜、那个菜,或者几个肉片,特别香,那个味道说起来还能有记忆。所以火车当然是跟外界唯一的一个象征性的联系。
Paul Kendall:哦,是这样的。
王导:还有一点,其实你们仔细去看这些片子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声音是来来自于高音喇叭。
Paul Kendall:嗯,对。
王导:高音喇叭是在当时这么一个区域最主要的特点。虽然很多家庭都有收音机,算是对好的生活的追求,有的家庭没有、有的有,但是不管你有和没有,这个高音喇叭是一个厂矿地区最典型的特征。上班的时候它要放音乐,下班也要放音乐。
Paul Kendall:还有广播体操。
王导:广播体操,对,我们广播体操也是要到工厂里做。这个是中国社会在文革期间非常典型的特征。所以《我11》的时候在法国录音,我们的这个剪接师和录音师老是觉得那个喇叭的声音太响了,他要把它放下,我说不响。他不可想象你一直生活在这么一个高音喇叭的环境里。这也是中国要统一思想,只有一个喇叭对着你说话,在当时的三线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的军队,去军队的军营、部队里面,他们也是这样放的。
Paul Kendall:那个喇叭到处都有吗?厂区、住宅区都有?
王导:它要根据每一个地区结构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山,这是山,那么山这边是工厂,从这绕出去,这边就是生活区,中间可能隔了一个山,那么喇叭就会竖在这个山上,这样的话,一放起来,这边也能听见,那边也能听见。还有就是像一般工厂的大门,大门的楼上都会有高音喇叭,下班一响,大家下班,上班的时候它也响,就把整个工厂区和生活区覆盖。这个是非常有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