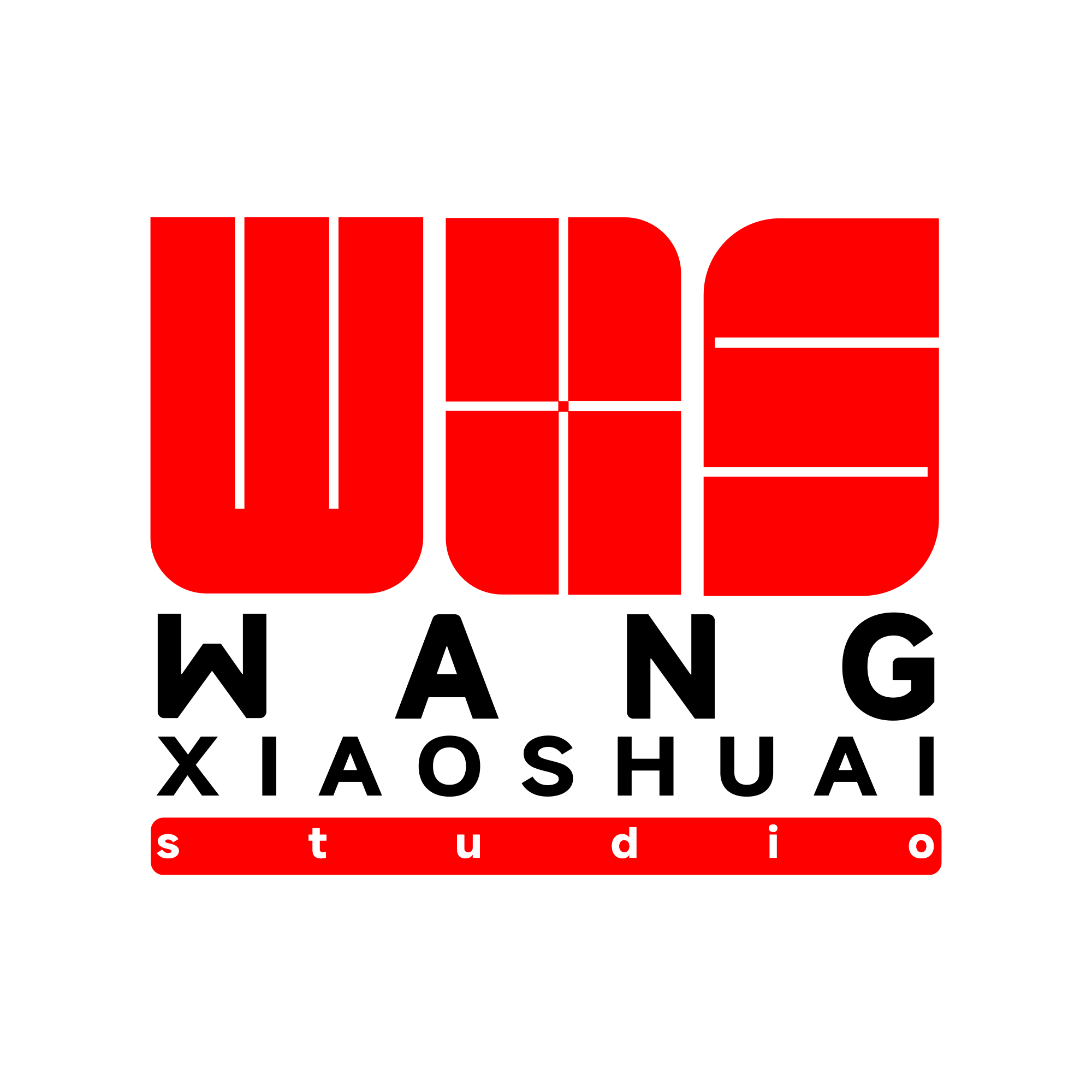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凤凰周刊》:《薄薄的故乡》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被评为2015“中国最美的书”,还将去参选2016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你对此有无期待?
王小帅:这是一本关于“我的家庭演变史”对历史的补充的书,有我的成长经历,父母的故事,出生地贵阳——那是个“三线建设”的西南城市,而我的十一部电影里有三部是关于“三线建设”,这也可以视为我对故乡的一种遥望和回想。关于参选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这件事,我觉得评委们不会仔细看书的文字内容,因为书还没翻译呢。他们应该更多考虑的是书的结构、装帧和设计,所以我觉得这个奖项是颁给设计师孙晓曦的,当然作为一个跨界的试验,我参与其中也很高兴。如果说这本书的创意上有什么突破,就是在铅字中插入手写的补充、批改和错误的划动。一般情况下,书有错误都要来回校正,就看不到创作和完成的过程。
《凤凰周刊》:这本书的创作和你的电影有关系吗?它的手写体设计很有趣,像个创意试验。
王小帅:我从2014年年底开始构思这本书,书的制作是独立的,和电影没关联。完成这本书时,我更像个演员,设计师像个导演。他想找手稿,但是现在大家都用电脑,手稿不多,所以我们就在书里做出手稿的感觉。这本书最有趣的是回忆部分。首先,回忆不是日记,难免有误差,我要把这样的误差感记录下来。其次,这本书里,记忆有错误就可以修改。书在排版印制前,有一个月时间我们都在设计手写体怎么加进来,注解怎么摆放好看而且有趣,也就是说这本书一边在印,一边加手写体。这些补充、修改和错误的划动,像是在把做书的过程实录下来,挺好玩儿的,像个试验。
《凤凰周刊》:曾见过你的阅读书单,你对中欧知识分子很感兴趣,比如帕慕克,还看到你看社会学方面的书,比如《乌合之众》,关于阅读,你有什么可分享的?
王小帅:帕慕克是马尔克斯之后影响我的又一个巨人。上世纪80年代的阅读特色是:瞎读。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被整个80年代的价值观照耀着。我起初读杰克伦敦,后来随着视野的开拓,诗歌、哲学和以前见不到的西方历史都进入我的世界了,比如说70年代前接触不到的西方绘画史,西方哲学史等等。我看书比较随性,看到推荐榜单会买来看。在学校时看书有点囫囵吞枣,现在是有时间看一本书就觉得很幸福,尤其是当你成长到一定阶段,开始阅读反刍,就做到了开卷有益。比如《乌合之众》,发现它时,我觉得里面的一切和我当下的思考都很接近,这就是开卷有益了。
三线建设:历史延续在个体和家族的血缘里
《凤凰周刊》:电影批评学者王小鲁说,这本书里有你的人生轨迹和电影的创作母题。你从2005年开始,用十年创作了“三线建设”三部曲,从《青红》到《我11》,再到今年的《闯入者》,你为何说它们是“生命三部曲”,它们是否完成了一个对生命轨迹闭合式的讲述?
王小帅:王小鲁看完这本书比较兴奋,他觉得这本书的出现,可以从源头去思考我这几年的“三线建设”电影。以前他觉得“三线建设”和大多数人没关系,观众会有疏离感。他看完书后,觉得自己误会了,原来“三线建设”和社会很近。在这个“大三线”中,除了贵阳之外,还有陕甘宁云贵川和青海等地的很多个城市。而且,在我的“三线建设”电影里,始终有“家庭”概念。一个人的成长除了社会影响外,潜移默化的家庭影响也非常重要。这本书是与电影平行的世界,印证着一个人的家庭观念。在我的三部电影中,主人公从少年到青年到老年,完成了一个闭合的讲述。从三线建设到现在,有一些第一代三线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就是完成了一个生命的故事。“三线建设”对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来说,是有完整性的。它作为历史概念已经结束,但是家族受此影响,生命和血缘上的延续一直存在。
《凤凰周刊》:什么是三线建设?新世纪以来的中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新一轮的产业布局调整和技术人群分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线建设”换了形式,却没有彻底消失。但是为何之前很少有人提及这个概念,又是什么时候解禁的?
王小帅:简单说,三线建设是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政府认为美国及周边国家危及国防安全,国内在13个省和自治区进行的大规模工业迁移和基础设施建设。整个西南部和西北部基本都是军事工业。当时我在贵阳,离城市很远,也不在农村,在军工厂长大的孩子和大院长大的孩子一样,都像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回顾那个特定时期,个体命运是随着社会政治的需要而变动的,大家普遍知道文革红卫兵、生产建设兵团和北大荒知青,但是“三线建设”因为是军事机密,多年来一直被屏蔽。“三线建设”经历者虽然多至上千万人,但是和中国人口基数相比,被提及的很少。但一直到我2005年拍《青红》之前,这个概念都没有人公开谈论。
《凤凰周刊》:“三线建设”三部曲中,能明显感觉到你在借家庭关系思考传统。《闯入者》中的老邓,《青红》里的父亲,他们代表的传统是否与时代一致,形成对子女的迫害?在特定时代里,时代对个体有迫害,个体之间相互迫害,人人受害,谁是施暴者?
王小帅:很多代人都曾因爱之名,把意图强加于人,尤其是家人身上。但在实施爱的过程中,他本身是缺乏自我意识的。《青红》的父亲和《闯入者》中的老邓这一类人物,虽然对时代给自己安排的命运态度强硬,但是并没有觉醒。青红父亲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被强制安排在贵州,很不舒服,想回上海。老邓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他又提不出自己的遭遇不公平在哪儿。三线建设史中有很多问题,很难说哪个个人能承担全部责任,就像《乌合之众》这本书里,个人在集体无意识中智商下降而盲目从众。作为大众群体来说,除了经常成为独裁或政治的被害者之外,有时会不经意的成为其中的参与者,施暴者,每个人都应该反省自己。所有的受害和施暴,即使是被裹挟,但你是此事的被害者,又可能是另一件事的施暴者。
《凤凰周刊》:三部曲的完成,通常代表一个阶段性话题的完结。十年的跨度里,你的拍摄过程中,社会现实是否发生了变化?针对“三线建设”的反思和忏悔出现了吗?
王小帅:我清醒地知道,改变不会在瞬间发生。有时候有些纪录影像被媒体曝光后,局部上确实会改变现实。我相信随着影像的成长,会慢慢的去激发观众的反思意识觉醒。虽然这段历史无法立刻被下定论,但是对几代“三线建设”者以及更广泛的大众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触动。《青红》上映时,上海的部分老“三线建设”职工想做一个大的游行。我劝这些父母辈不要因为一个电影形成政治上的诉求,后来这事没有做。但我相信,虽然没做这件事,却会让更多“三线建设”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人谈论这个事情。《闯入者》拍摄时,就有几个老红卫兵出来,向学校的老师道歉。人走向暮年时,突然意识到当年自己也是施暴的一份子,不能都把一切责任推给政治,这是一个自我良知上的审视。良知产生了一种内在的恐惧,引发的忏悔很人性化。随着未来的发展,还会有更多人反思。
《凤凰周刊》:在书里,你的故乡虽然很“薄”,但仍然存在。在电影里,故乡又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你如何理解传统?
王小帅:我们看《闯入者》,觉得那一代人的人生彻底被政治左右了。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断裂,都和社会政治环境分不开。一个清醒者回头看,会觉得那个时代太疯狂和无理性了,一切都能瞬间被摧毁,如果有人为此觉得心痛,说明他内心有一片温柔之乡。但凡有心痛,有对传统的怀念追溯,这就是温柔之乡在起作用,这才是生命力和价值所在。完全无法想象,在文革时有那么多人敢疯狂拆毁庙宇、老建筑和传统文化遗产,敢下手去烧去抢去砸,值得人类学家思考。我心中真正的故乡和传统是同一种东西,代表美好和理想。
创作立场:“去政治化”是用自己的语言直面现实
《凤凰周刊》:可以说,1949年至今,国家的历史是文艺创作的富矿。很多50后导演更关心宏大叙事,有人完全跳入历史。一些60后,70后导演则忙着拍个体命运,或创作故乡三部曲,比如你,比如贾樟柯,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选择?
王小帅: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特别值得去深入研究。为什么50后一代的创作视角往往是从家国和大历史出发?家国教育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导向,是不是会造成一种影响,把家庭和自身屏蔽掉了?相比来说,60后很幸运,没有有过早体会政治生活,不会被弄去上山下乡,文革十年也来不及当红卫兵。我们的记忆更多来自个人和家庭经验。进入青春期后,赶上1980年代宝贵的十年黄金期,对个体解放体会得更深。电影学院的上一辈导演,1982年可能已经毕业了,虽然当时也有了安德烈巴赞的现实主义美学,但他们之前受到的苏式教育可能更多。十年时间,两代人的些微差别就会产生巨大变化。国家确实有很多历史是创作富矿。而作为创作者个人来说,他的视角在哪儿?他的视线落在富矿的什么位置?这是更重要的。
《凤凰周刊》:你认为成长经历导致了60后导演对个体命运的关注,也经常提及“集体无意识”,那么你怎么看待“集体”在这个时代的消解?你在一些公开讲话里表达过会持续“严肃反思”,我们的现状是,历史记忆断裂,消费受众主体是年轻人,审美普遍追求轻松,反思还有舞台吗?
王小帅:“集体消解”这个现象应该是不存在的,可以理解成我们进入了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状态,变成用金钱、物质消费或追名逐利来给人们洗脑。创作者也面对着个人意志和集体无意识之间又一轮较量,你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历史断裂,逃避现实,包括年轻人把文艺形态当成娱乐手段,也愿意被娱乐而不肯去思考,商业片一统天下,独立电影的不同声音几乎活不下去,这种状况对吗?假如说你对这个时代还有看法,你就有权力去进行严肃思考或者批评。
《凤凰周刊》:“三线建设”三部曲呈现的是特定时代留下的政治创伤。但是人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糊文艺创作中“政治”这个概念,认为要“去政治化”。
王小帅:其实,“去政治化”的正确理解,是因为我们曾经被政治化的语言淹没和包围,所以不想再用它去表达。中国人确实被政治搞得有点焦头烂额,十年怕井绳,以至于到现在只讲娱乐。所以经常听说,现实太复杂,不谈政治,弄弄小文艺就行了。我觉得,你可以用自身的语言和视角来看世界。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无法脱离政治,国家施行的任何政策对我们和我们的家庭都是有影响的,鱼在水中,跳出水面只有那么一瞬间的脱离。摄影机就在那里,为什么要无视社会和政治带来的一切,避而不谈它呢?
出路何在:应该思考商业片和独立电影如何并存
《凤凰周刊》:据说今年《闯入者》的票房不大理想。从1993年你第一部引起关注的《冬春的日子》开始,你屡屡斩获国际大奖。反观一下这二十几年,独立电影和艺术片市场的整体大环境,有没有出现过回暖?
王小帅: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时候。如果说有回暖,应该是大家可以越来越公开地去聊这些独立电影,没有什么地下地上的区别了。地上地下,体制内外,本来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荒诞产物,过去大家觉得搞出一个地下电影不得了了,现在我觉得都无所谓了,因为市场全面转向经济和金钱。相反,如果说排除对市场的期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有这些电影,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并研究这些电影,我觉得这方面是个进步。
《凤凰周刊》:中国电影史上,提到张元和王小帅这一批人,说你们是中国独立影像先锋,你们也影响了中国独立纪录片群体的出现,现在纪录片导演们也在世界各大电影节拿奖,走的正是你们当年“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路。
王小帅:海外电影节这道风景一直在,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艺谋和陈凯歌他们就进入了嘎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都70多年了,电影发明才一百多年,有前人成功的例子鼓舞,后面的年轻人进来会越来越容易。只是在中国的整体大环境下,走海外电影节获奖这条路是越来越美好,还是越来越被屏蔽,我说不好。因为电影产业全盘市场化后,到了现在,获了国际奖项也不一定能对独立电影的处境有根本改观。
《凤凰周刊》:你对于市场有过一些很直接的批评,比如“假资本之手杀独立电影”“现在是商业片的春天,独立电影的冬天”,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
王小帅:其实现在投资倒是一直在向好的电影靠拢,独立电影问题主要是出口问题。我觉得现在的最高智慧应该去思考商业片和独立电影的共生并存问题,而不是谁代替谁。娱乐工业现在是主流,这种有趣的作者型电影(独立电影,或艺术电影)不是主流,但处境也有点过于艰难。现在只能民间传播,小范围的资金循环做不到持续,导演无法心无旁骛好好创作。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现状不健康,大的环境下很难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走艺术院线,走电影节售票,这么多年来,很多电影个案都在寻找院线播映途径,但是没有形成可持续的模式。
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