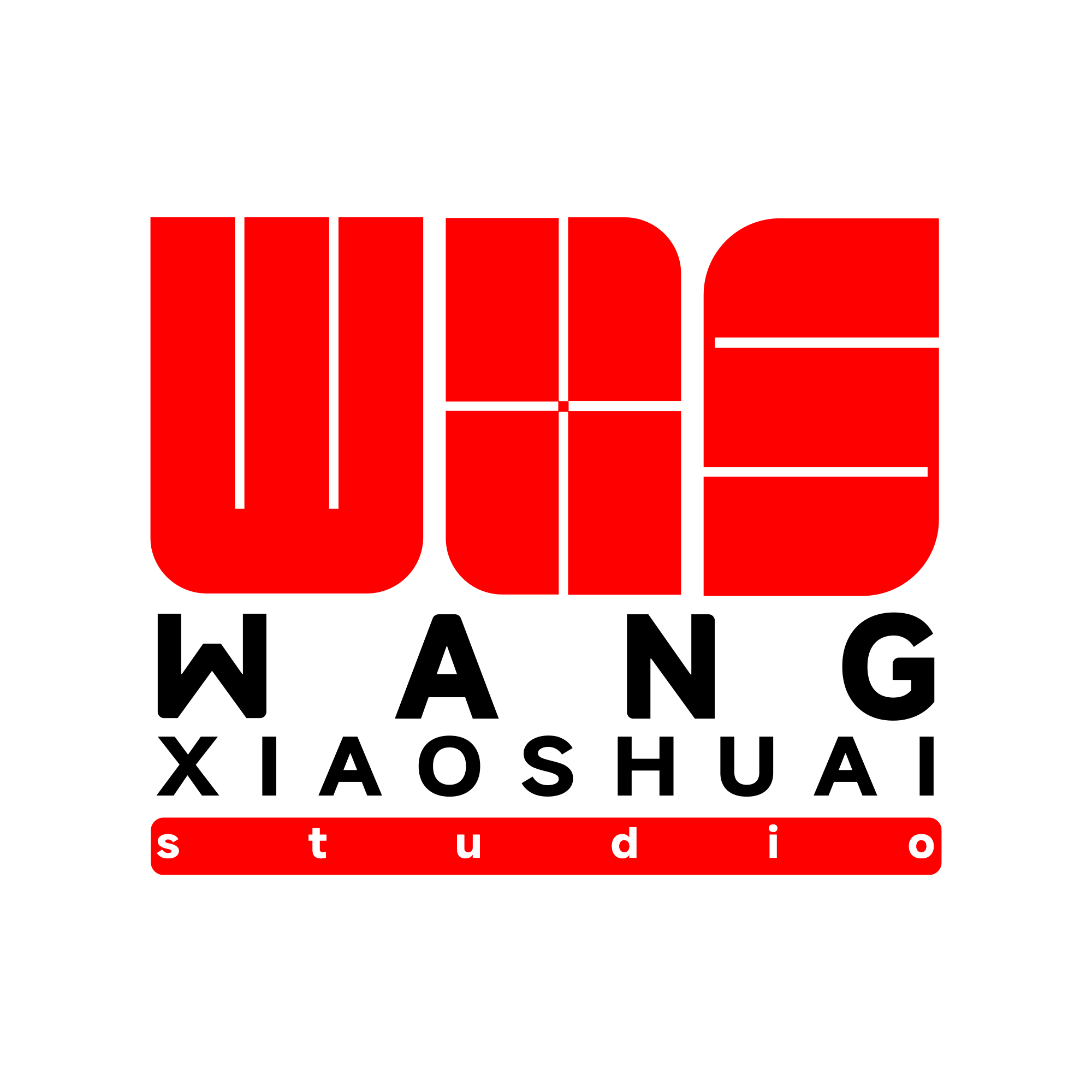那是1994年,《冬春的日子》参加完年初的鹿特丹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之后,又受邀参加了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电影节。一开始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的感觉不只电影节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更像是整个塞萨洛尼基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好吧,更甚至连一个亚洲面孔都很少见。唯一与我说话和照顾我的人是一个印度老太太Aluna,她后来开创了印度德里亚洲电影节,当时她在那里当评委。后来吴念真来了,也是一个人,我们就像是火星撞了地球,干柴遇见了烈火。他身上带有台湾电影节中心的生活补助,一天一百多美元,属于土豪级别。我就跟着他到处吃喝,听他讲台式黄段子,那一年我26。另外一个亚洲面孔就有点吓人了。我一到电影节就被告知过几天大岛渚要来,我一时恍惚了一下,大岛渚?他还活着吗?他不是已经在历史书里了吗?第一次看到他的《感官王国》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应该是86年左右吧。英国教师Tony Rayns 神秘地组织我们学生观看这部让人瞠目结舌的电影,随后大岛渚的电影就成为我们必追的电影。从黑白片《青春残酷物语》《日本夜与雾》到毕业后自己追看的《少年》《仪式》《绞刑》《圣诞快乐,劳伦斯》等等,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许多影片粗粝的黑白影像,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青春年少,并没有过多在意这些影片的出品年份,抑或是因为中国的特殊原因,等到这些影片,哪怕是很新的影片,以盗版碟的形式流入黑市也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所以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然觉得这些影片是来自于久远的历史里的,而大岛渚这个名字也很早就在历史里了。他是不可能以活着的身体出现在我的面前的。
大岛渚来的那天整个电影界的空气感觉都在躁动,电影节为他举办了一场大型的记者会,会场很大,人山人海,我挤在一个角落里,看着那个人。那个人一头银发,带着无边框的眼睛,穿一身纯粉色偏紫的西服,粉色偏紫,好吧,会场除他,一切暗淡。
记者会结束人们簇拥着那个灿烂的粉色人儿出来。我站在那里看着历史走过去,当时内心有一种奇怪的自尊,我不能像一个粉丝一样走上去,我就在这里,有缘分一定会和这个人坐在一起的。
快到就在二个小时以后,电影节主席过来找到我,说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我要请大岛渚吃饭,你要有时间就一起参加吧。我有时间吗?我一个人成天没事游游荡荡,我有时间吗?我说当然,我可以抽出一些时间。那时吴念真还没抵达,对他们来说我和大岛渚这两张黄皮肤的脸简直就应该是老乡。我知道我要和大岛渚坐在一起了。多年以后,我把这段经历说给了一个当年在电影学院进修的美国华人Henry听,我们当时正在一起小便,他大叫一声“什么,你和他一起吃过饭?”他当时的小便在极其顺畅的时候突然断流了,很生硬。
那顿晚餐除了大岛渚和印度的Aluna ,另外还有一个他们同辈的影评人和主席,记忆中应该没有别人了。中间没有细节记忆,只有在我历经反复的内心斗争后要求和大岛渚合一个影,当然,这个顺理成章。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候,你也别再装矜持了。
紧接着,事情的发展有点让人预料不到,吃完饭大家散去,我住的酒店离城较远,在一个偏僻的山上,从酒店一面频窗远眺就是蔚蓝的爱琴海,风景不可言说,当然,我的这一面,推开窗户,是整洁的停车场。大岛渚和助手有一个专车,我正琢磨着这大晚上的我怎么去到城郊,助手跑过来问我住哪里,我说了酒店的名字,助手跑回车边,又跑回来,说大岛先生和你住一个酒店,我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搭我回去。“你不介意的话?”日本人太客气了。好了,情况进了一步,不光光荣的同桌进餐,现在要上一个车了。路上大岛渚通过助理用英语询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关于年龄,我告诉他了,大岛渚说这很好,你很年轻就来参加电影节,他是从40岁以后才开始参加电影节的,要珍惜。第二天就是《冬春的日子》的首映,他说他会来看。我记不起当时我是什么反应了,矜持装的够不够,但用一个成语可以装下的话,可能可以用“心潮澎湃”这个成语吧。还没完,我们到了酒店,助手离开了,就剩我和大岛渚,你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们让了两三下进了电梯,客气的让对方先按楼层,最后“呵呵”,都是三楼。那一次我感觉着部电梯真的好慢,电梯真的很小。电梯到了三层,我们再次互让着出了电梯,来到要决定是向左拐还是向右拐的两条走廊的会和处,再次谦身互让,“呵呵”,都是向右拐,走廊很憋屈,我们很沉默,竟然一路走到走廊的劲头,我只能选择右边我的房间了。“呵呵”,我们笑了,大岛先生是左边那一间,我们竟然门对门,酒店真的也把我们当成同乡客了。当然我知道,他的房间是有阳台的,阳台外看出去是山坡下的城市屋顶,再过去就是蔚蓝的爱琴海,或者景观是会让人飘飘欲仙的。我们有点尴尬,互道了晚安。活着的历史就进了我对门的房间。大岛渚先生好心送我,竟没想到送成了这样。
我知道大岛渚会在电影节结束前提前离开几天,我犯了一个傻,竟然立刻返回楼下的前台,跟服务员说能不能在大岛先生退房以后,我可以换到他的房间,服务员答应了。但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发生,我应该是没有想到那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和我这个看得见车场的房间在接待标准和规格上是有差别的。即使这样这个情境还是足够让我迷糊了好多年,毕竟我离这个从电影史里走过来的人物真真只有一步之遥。后来那个和我一起撒尿断流的Henry 听我说完这段奇遇之后连续在厕所里大叫了几声美国国骂,说他是堂堂纽约NYU的毕业生,混到现在连科波拉都没见过啊。
第二天,《冬春的日子》首映,因为是竞赛片,所以首映是在电影节最大的影厅举行,也谈不上“举行”,就是到点开始放映,之前我到前面和大家说一下“哈喽”。印象中那个影院应该能坐千人左右,如果是记忆中的印象是被放大了,那至少也有五百个座位。我到的很早,影院里空无一人,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人来看,但是心里最复杂的是那个人会不会来看,毕竟昨天晚上在车里,他通过助手说了一句他会来看。心里的复杂性在于,人家不来吧,属于特别正常,自己云淡风轻一点也就过去了。人家真要来了,那面子可是大了去了。可是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人家从历史里走出来,和你吃顿饭,然后用车给你送到你房间门口,人家再遵守随意的一句承诺跑来看你的处女作,黑白的,凭什么呀!人家的头发已经是纯白色的了,在电影界随便什么地方一露面,空气都会随之躁动起来的。正胡思乱想着,同时又装着云淡风轻着,大门口涌进来一群人,被围在中间是那个人,今天没有穿粉紫色的衣服,我在一边,没有上前,他们径直进了影院。当时影院里已经有些人了,不多,离放映时间还早,大岛渚他们这群人几乎是第一拨来到影院的。他选择了很靠前的,正中间的一个位,挺着身,仰着头,坐下来就一动不动,助手和随行的人离他远远地坐着。后面陆陆续续来的观众都坐在靠后的地方,这样一来,白头发大岛先生成了坐在最前排,最中间,最孤零零的一个观众了。当时突然间感觉到什么是气场了,后面来的观众应该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气场就自然而然的在那里了。它可能来自于安静,专注,亦或是孤独?
当银幕上投射出《冬春的日子》那粗粝的影像的时候,我在想,一定要好好拍电影啊,要不然到这个时候,有多少后悔都来不及了。
放映结束的时候,我在门口等着,大岛渚出来的时候径直向我走来,他说很喜欢,这样的中国电影他是第一次看到,让他想到了他年轻的时候。很简短的几句对话,我能说的只是“谢谢”随后他被簇拥着离开了。
2013年1月15日,从互联网上看到大岛渚去世的消息,享年80岁,按照这样的推断,当年在电影节遇到时,他也才61岁,不算老。从网上看到他去世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要喝酒。”这一下子让我有点想不起来,19年前在塞萨洛尼基的那家餐馆里,他喝酒了吗?
今日正好是2014年1月15日,写完这些文字,我决定倒上一杯酒,为大岛渚先生的一周年忌日,敬上一杯酒。
王小帅 2014年1月15日 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