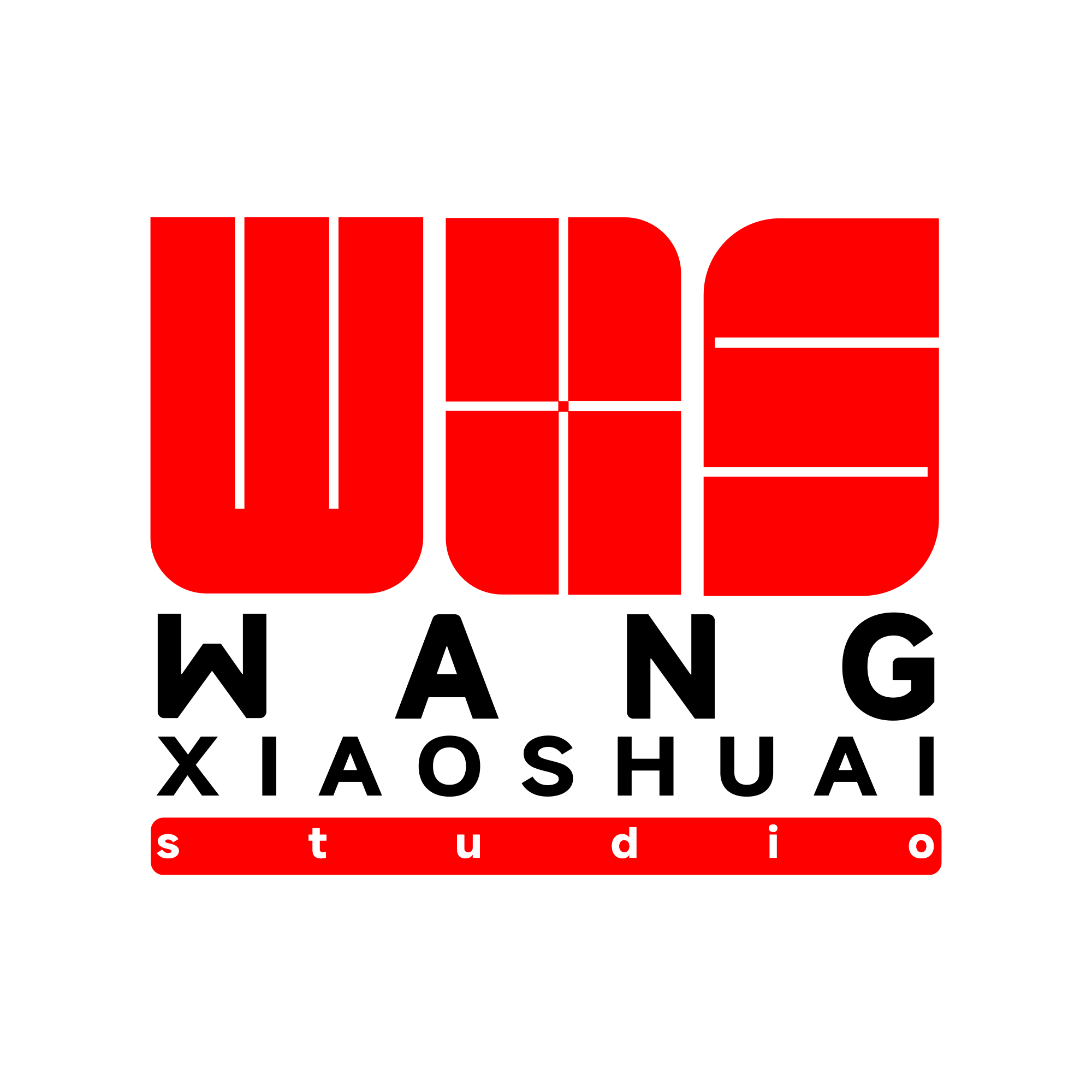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一席》演讲
大家好,我叫王小帅,出生在上海,就在这个地方,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就是我叫王小帅这事儿好像我能比较确定,我出生在上海这事儿也比较确定,静安医院,完了以后,剩下的就好像不太确凿了。
我觉得我,比如说,身高,不详,胖瘦,我现在这样子也不详,算瘦算胖也不详,智商,不详,情商也不详,还有一个,比所有不详的东西加起来还让我困惑的,就是我是哪儿人。
离开了 ,我转到那个武汉大学理工学院的附属中学,转学过去。我说转学过去,我该用什么心态过去,我不能怂啊,我虽然是贵阳来的,可是我是上海人呐,我出生在上海啊,我上海比你武汉也不小,这个城市虽然我没去过,瞅都没瞅过上海长什么样,我就,哎,挺着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哇,那个班人多,我们那个贵阳的学校小,乌泱泱的,几十个人,都戴着眼镜,他们学习好你知道吧,全戴眼镜看着我。没座儿了,最边上那个坐下,我就靠紧门,门一开就是我,坐那儿,最边上,黑板这么看,然后就呜呜呜,他们就轰隆轰隆轰隆,有些议论我,我一直在听,议论我什么。
突然有几个词儿蹦出来了,乡里伢,乡里伢就是那个,武汉话就是乡下人,你知道吧,这个乡里伢来,我当时醍醐灌顶,我是乡下人,哦,我才明白我跟武汉没关系。
于是我就很小心,我的性格就变成我到任何地方,我就变成我在边上了,我不可能是中间那个人,我永远是在边缘待着看。好了,我就变成在武汉混了两年,以为是自己慢慢想演变成武汉人,我觉得我自己像,用现在讲时髦的话像格式化一样,那我必须命令自己重新格一遍,把过去的东西全部扔掉。
我现在重新输入我是武汉人的这个概念,但很失败,两年,但也是因为我努力,学画嘛,就两年之后呢,按一般的讲法,就永远在武汉待着了吧,不,因为我学画画什么的,诶,这运气特别好,81年,哐~,就考到了这个北京的中央美院附中,诶,我要去北京了。
我就问,北京那去那儿读书怎么着,我的户口要不要过去的?当然,他们说当然要过来咯,欸,我心说这好,我的户口到北京了,我不就成北京人了吗?我就到北京,在北京一待,等于说中央美院附中,四年,然后附中完了以后,电影学院,四年,都集体户口。
好了,到分配了,分配的时候,就我这个弦没有绷紧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当时很贼的。我那个时候学习成绩好啊傻乎乎的,我是第一名啊,学分总分第一名,老师说,欸,过来过来,你先挑一下啊,你是第一名,现在你要抓紧挑哦,现在唯一一个要你们的地方是哪儿啊,两个地方,两个地方要你们。
哪儿?一个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当兵了,不行。还有地方说是福建电影制片厂,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就要么没了啊,没了。
那时候人傻啊,我想没单位了,我怎么办,我怎么拍电影啊?那个时候拍电影是计划经济,要有厂子,要有厂领导,要有国家指标。好吧,我就矛盾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人呐,我是觉得,有的时候不能在一个过程中过于,什么学分高啊 ,学得好好啊,这很难办,你冲在前面让你挑,人家都可以不挑,就我挑。
那我就很难了,要么我就很被动了,我没得挑,听天由命。现在让我挑我,诶,就这个对我是一个重要的事情,那我最后傻乎乎地答应了,一点头,完蛋了,人生改变了。为什么?那些人都贼在后面瞄着,你先挑先挑,挺好的,去啊,挺好的。我还问我爸,我爸说好啊,到海边啊,看渔民,然后对面就是台湾。
二十岁啊,二十一二岁,傻,好一点头,哈哈,点头了,点头了,好好好好,王小帅同意去福建咯,他们就等于说把一个户口和档案就算给你,出去了,要不然很多人当时待分配的话,都要留在电影学院压着,有时候压了好多年。
那些底气足的人,或者那些城府比较深的,就压着不管,天天在街上晃荡,压着压着这些户口档案就慢慢就随着社会变化,就留在北京了,所以现在所有人的户口都在北京,就我一个人傻乎乎地,bong,出去了,为了电影事业,为了心目中那个神圣的电影,就出去了。
那出去以后呢,户口,档案,关系嘛,当时讲关系。后来我后悔了,因为那个要我的厂长吧,是我们附中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很著名的一个人,叫陈剑雨,他是《红高粱》的编剧,他专门要我来,有个本子给我,我来了就当导演。
我就冲着这本子,跟着本子就去了。结果一到那儿呢,他待了一年就离开了福建厂。这一错一回,我是往这边去,他往这边回就错开了,所有的承诺全部泡汤,新领导没给我承诺。谁给你说拍个本子,你才二十几岁,会拍电影吗?我就傻了。
当时我觉得,就是也是对我人生,完了,我说,十年,我就想起,我父亲就是也在北京待了十二年,哎呀,我怎么这个阵地都没守住,好像我们家就是这样飘来飘去。我一个人又背着个行李包,踏上了火车,就往福建走。
哇,那次经历对我来说是影响太大了,因为我不知道,从贵阳到北京已经够远的,两天两夜,我觉得中国够大了,从北京到福建,哇,那个概念,怎么会三天三夜都在开火车而且不停的?
白天吧,你还能看到窗外,晚上躺在那儿,睡一觉起来后,一睁眼火车还在开,第二天火车还在开,而且风景就变了,因为从贵阳回到北京,你还能看到这个到了,那以后你就觉得这是越南吧,还在哪儿啊,或这是哪个国家啊,太大了,就这个树都不一样了。
当时就慌了,懵掉了,说完了,这这个事情有点糟,我的人生有点糟糕了。我说不行我拿行李,我就在火车开的时候收拾行李,跟我一块去的凌云说,你干嘛?我跳火车,我跳车,它现在那个速度不快,你知道吗,我看这方法行,差不多我要跳。
凌云说,别别,你干嘛?我说不能去那儿,我说去那儿就完蛋了,按我的家里这么颠簸来来回回,去那儿之后,我就变成真正变成福建人了,这事情就落实了。他说没事儿,去那拍电影,我说你是没事,因为他老婆在那你知道吗,他等于说是坐三天火车回家,高兴得很,见老婆去了。
好了,没办法,就去了。去了之后,厂里安安静静的,设想一下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在写本子啊,写啊写啊,拼命写,我觉得唯一改变自己的就靠自己了,没有任何其他了,就写写写写,写了好多,递上去,递了五六个剧本。
那两年里面,好像90年到92年吧,一直递剧本,厂里面根本就不理你,也就说你好好的,好好的在这边,买个家具,买个电视,弄个沙发,弄好你就把这家置起来,等着,将来有你机会的。
我一想坏了,这话就是个陷阱,就让我等着,你还找个媳妇儿,你就是福建人了嘛,吓死我了,我说不行,我就心里想,我要警惕,我说这不能这样,就是说,这一定不是最后的结果,这是假的。
我就在每次发工资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在那个枕头底下,准备点儿几毛,就把粮票买好,烟买好,买瓶酒,平时喝的,这都差不多,剩下的钱就放枕头底下,一个月一个月攒钱。
我想,到时候实在不行我会跑的,当我写那么多剧本没有机会,最后证明没有机会了,我肯定要走,我不能够永远属于这儿,但我得留点钱,为什么?买机票,我再也不能经历这三天三夜往回走了你知道吧,立刻要飞回去,瞬间到北京。
就这样,然后不买东西,什么东西都捡,沙发捡一个,捡一个能坐就行了,然后他说你买个电视,我实在我憋不住了,买一个黑白电视,那么小,当时12寸,那个频道哒哒哒这么调,看不清楚,有点儿声就行,反正就陪伴我过日子嘛。
就这样,然后唯一的家具是一个长条凳,公园的长条凳,一棱一棱的,那个牙刷牙膏什么的都放在上面,毛巾搭在上面就这样,这就是我家。因为我想,如果把家按他们这样的弄好了,我就走不了了。就像我的体会,就像我们家,当时从上海一家端到贵阳,想走,太难太难了,所以呢我就一切都临时化。
那么等到最后一天让我彻底放弃这个希望的时候,就是北京电影资料馆有一个领导到那开会。厂里全来了,坐好,他开始说,诶,你们这个厂里不是有一个叫大学生叫王小帅嘛,他学习成绩很好,你们应该让他赶紧拍电影啊,锻炼锻炼啊,欸,王小帅在吗?
我说我在我在,我要争取,我说我正在争取,正在争取,说得很中肯,把那个话要传递到那个厂长的耳边听,正在争取,结果那厂长打断了,他说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大学生啊,还年轻,就是要至少要锻炼五年,当场记,当副导演,锻炼五年。
五年。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在递各种申请,一直在瞄领导的眼色,到底他这个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是喜欢我还是不喜欢,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没表情,始终没表情,我绕着看,看不清楚,他一直没表情。
到这天突然说,五年。五年,好,明确了,还五年呢,话音未落我就站起来了,还开着会,站起来从我这个地方走出去,上到三楼我的宿舍。其实我们一个小楼嘛,福建厂,二楼是办公室,开会,我就上到我的宿舍三楼,从进屋,到我离开福建,就十五分钟。
方便吧,没东西,拿几件衣服备用,有些衣服太重了扔掉。枕头底下把钱一掏出来,我说谢谢你啊,这有远见,卷着,出门的时候,拿了一把那么小的钥匙,把那个门别上,叭,一锁。这个将军那么小,只要有个将军在这儿就不可能有人进我的房间,就交给了我边上的一个同事,王力军,现在是制片主任,交给他我说你保管。
他说,你干嘛去,我说我走了,走了你你去哪儿?我说,北京,别说啊,我不回来了。他懵里懵咚地,我说你守着,给我看着钥匙,拿着,你只要它在,不能让人进我的房间,我不定哪天回来,但现在是不回来了。
他说行行行,放心放心兄弟,从此我就溜着墙根啊,溜着墙根因为我害怕,怕他发现我走,发现给我抓回去怎么办,或者哪个领导一出来,欸,你拿着包干什么,解释不清啊,我跑跑跑溜着墙根儿跑。
好在厂里人少,都在开会呢,都被敌人封锁在那儿,我就溜出去一直溜到大街上,打了个车,一屁股坐到车里,那个心,啪,算是塌下来,没人追我回去,从此我就又回了北京,就重新找到一个北京的感觉。
但到那个时候我已经什么都没了,户口、档案还远在福建呢,我是跑回来的,流浪汉,一分钱没有,看着北京,哎呀,千家万户都是灯,我曾经在这十几年,现在,什么都没了,那必须靠自己了。
那个时候就开始琢磨着我的主项,就是电影啊,于是开始就历经了各种顿悟啊,最后,写那个《冬春的日子》,算是借点儿钱,就开始拍所谓的地下电影,也不要什么国家的,不看领导眼色了。你看着我黑乎乎的眼睛,我根本就不判断了,我来判断我自己吧。
因为我们的家庭曾经从六十年代响应号召,到了那个地方,整个命运在周转,改变,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听着,这个人家的话,都在忘记自己是谁,都没有一个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说我来吧。
虽然那个时候还计划经济,还不能自由拍电影,所以拍完之后就把我封杀了嘛,就嘣一封杀到现在,我现在身份始终不清,这方面也是不详的一点。在这个期间,你知道就是我,作为我始终的王小帅是谁,没有,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去怎么回应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性格,现在你看,我在北京也是,这边一热闹吧我就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这边一热闹我又搬到远的,我现在住四环以外,北京再热闹下去我得搬五环去,实在不行搬农村去。就永远躲在外面,我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中心我可以进去。
那么这个期间我是很尴尬很尴尬的,就是非常的痛苦,就对于一个没有故乡的感觉非常痛苦,等到后来拍着电影拍着电影,想着这个问题,想得越来越多以后我觉得,就这样吧,不要再去像大家一样去找这个所谓的根和故乡了。
因为我相信像三线这样的命运的人和事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我,而且就是这样的感觉你把它抛掉之后,反而就自由了,我就是这样的我,是一个个体。所以我在电影中就潜移默化,下意识越来越主张对个体的关怀,可能是一坨,是一个家乡人,但是这里面每一个组成的都是一个一个的人。
每一个灵魂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很弱小的,都在寻找什么,都在担忧什么,都在惧怕什么。去关心它,就等于说我把我的摄影机关心了他,也解放了我,我能够找回我自己。
我生在上海,可跟上海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你祖籍是哪儿,我说祖籍,户口上给我写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叫辽宁丹东。我父亲他们怎么闯关东,丹东在哪儿我不知道,没去过,从来没有。然后说那你父亲呢,父亲青岛人,青岛跟我也没什么半点关系,于是这一圈,然后我又在贵阳长大,就这怎么乱七八糟的说不清楚了。
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呢?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有些人知道,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虽然我已经做过一些工作,做了一些片子或什么来介绍,但毕竟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事情在整个中国一个大的历史事件中,是被屏蔽了很多年的,就是三线,支援三线建设。
现在大家看到我怎么老说三线,就剩你在那儿叨叨叨,像祥林嫂一样。那我说不说不行,因为它确实一段历史,它曾经存在过,那么现在被忽略,被屏蔽掉,那么总有人说它,总有人必须要提提它。
那么我跟这个三线的关系就很特殊了,因为我66年出生之后,我母亲的工厂正好在上海,是一个军工厂,叫上海光学仪器厂,正好跟着三线就去了贵州。那三线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座的很多人不知道。
1960年的时候,中苏关系交恶,不好了,不好了之后呢北方有上百万的苏联军队压过来,这他们说的啊,当时也不知道然后呢,再往下走到了62年的时候呢,就中印边境这块儿出现冲突,打起来了,完了台湾那块,天天唱着反攻大陆,就觉得这整个是个包围圈。
然后到了1964年八月份,一下子就是那个北海湾事件,炸弹都落到中国的境内了。这时候就整体就慌了,说不行,这打仗不行,那么中国大部分这个军工企业和重工企业都知道,中国这个布局全在沿海,东北沿海一带大城市。
那么就结合到当年打仗,当年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推到重庆就推不进去了,因为重庆的大山里面还保留了一些军工厂,还能为这个打仗提供一些军事设备和那个基础设施,可是这要打起来,美国一轰炸上来整个包围,那完了,几颗原子弹就把工业体系就全摧毁了。
所以当时毛泽东就很着急,赶快往中国的西部转移,那边高山峻岭,可以把工业基地设在那里,这将来打起来我们至少有的退,那儿好守。所以应该是64年决定的,64年八月份到65年的四月份,大概大半年的时间,把整个工厂就一下子全部地搬过去了。一声令下,不用讨论,全过去了。
那这里面涉及了多少人呢?就是整个的三线吧,从那个云贵川一带,叫西南三线,甘肃宁夏,这叫西北三线,大三线,然后从那个京广铁路,往西,长江以南这块呢就算是个二线,那么沿海就一线,大概有400多万个家庭吧应该,400多万个高技术工人一下子挪过去。
然后这里面按中国的说法就是四百多万个人,一个家庭,一般那个时候我们年代都是4口人,对吧,3到4口人,那么一算的话就是上千万人,就轰隆轰隆就开到。我们上光厂当时是调了最好的2000多个人,直接到了贵州。
那时候的这个选址啊,部队选址,就都是开着飞机往深山里开,往下看,啊,哪个山,山底下一看,这个地方没人,空的,就这儿,一指,好了,领导一下令,下面的人就开始要往里推进,就把整个的工厂,又一边修路一边把器材就开始建设这个所谓三线。
那么我66年出生的时候呢,只跟上海沾亲带故了4个月,还稀里糊涂的时候呢就上了火车。我妈妈那个时候生病嘛,说哎呀能在医院里赖一会儿,说不去了吧也不行,就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人都很积极地一定要去,不去会被人说话的,你不听党的话,不行,就过去了。
那我爸也随着过去了,就是说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在表导系毕业已经毕业了四年,教了八年书,我是最近才知道,我父亲竟然在上海待过十几年,那已经是一个应该是纯正的上海人了,但因为我还小,又怕打仗,就整体搬过去了。
所以我的这个童年的记忆,就整个是在那儿长大的。在一个那种地方是什么呢,一下空降了一堆上海人,当然我们的厂还不光是上海人还有,东北人啊北京人啊很多混杂的,但主要是上海人,一下空降到这个山沟沟里面,跟周边的是没有任何交集的,所以就自成一体。
什么这个厂里面,一般我们厂里面有医院啊,自己的医务室啊,学校啊,附小啊,什么都有。还有卖菜的,食堂,什么都有,很全,还有放电影,娱乐活动就是放露天电影,非常全。所有三线人,我相信有三线记忆的人,都有这个共同的经历,我们就在那儿,kuang就待下来了。
待下来之后呢,就等于你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作为孩子来说你是懵的,就都知道家长都在说上海话,他们有的时候哔哩叭啦说上海话,然后你觉得,这是哪儿啊?而且不让我们出这个圈,一出去就到当地了,当地农村很危险的,不让我们出到这个区域外面去。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我们不知道是哪里人,这是三线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就三线人出来啊,你问他,你是哪儿人,就懵掉了,都回答不上来。因为有一部分人呢,就至今还留在那里,就像三线人说的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子子孙孙就这么下去了。
那么上海人的一家人,bong就在那儿扎根了,那个扎根不像,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家都听说过上山下乡,知青,对吧,大家都很清楚,都知道,可是知青那个时候只是一个人,比如一个家庭,一个老大或者老二,你们派一个就广阔天地去了。
可是这个三线呢,是整体的一家人就过去了,孩子,甚至还有带老的,把户口档案一端,就离开了上海。那么这样一下子呢等过了这么多年,那三线的整个的建设无疾而终,也搞不清楚它是怎么回事。
结束以后,这一家人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比如北京、上海,就难于上青天,因为户籍制,你的户口档案根本就进不来了。就算现在属于相对比较自由迁徙了,可是也回不来了,为什么呢,几十年在那儿了,他的根都扎在那儿了,一回来亲戚都老了。
像我们上一辈的我父亲、母亲都老了,回来以后不适应了,没有地方是你的了,那说在那儿,奋斗吧,回到上海奋斗可是已经没有技能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在山沟沟里就在工厂,见不到任何人,没有任何关系,回到这儿也没有技能,也没有关系,就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又没有钱,在上海可能买个厨房这么一个地方的钱都没有,怎么办?所以这些人就落在这儿了。
以前刚去的时候很高兴的,工人阶级啊,到那儿。那么当地我们苗寨赶集的时候,哇,一看工人来了都很欢欣鼓舞的,他们要砍价的,你这个葱几毛钱一斤几分钱一斤,很厉害的,就是工人来买他们东西。
可是到了76年文革结束了,结束以后,啪,就没人管了,原来的军工企业就改制了,就变成民营啊民企啊,到了78年什么就开始改了,又走市场化的道路了,那么一走市场化道路那就不管了嘛,原来是国家管的,国家统购统销,国家发工资,现在没了。
那么山沟沟里,那山里面就很难办了,因为他们生产的每一个东西,所有的成本都要比外面贵好多好多,因为交通费,现在是物流,原材料运进去加工,加工完了再出来,出来之后这整个来来回回,这个费用,还有时间成本,就使得他们的竞争力就慢慢就没有了,荒废了。
我有一个同学吧,从小跟他玩,一家五口,两个兄弟,一个妹妹,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考技校。为了能够保证铁饭碗,就考了技校,那么考了技校以后呢,等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就接班到了工厂。
可是一接班到工厂之后,正好碰到最糟糕的时候,到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整个工厂就发不出工资了,他们就完全靠着父母的一点点存款,吃劳保,就这么活着。我去拍《青红》的时候看景,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待着那儿,完全不敢出去吃饭,因为什么?几年没有发出工资来了,那是非常惨的。
那么我们家呢,对我来说很幸运,就如果没有一些命运的小小的蝴蝶颤动的翅膀,能够改变一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在那儿。
在1979年的时候,我爸爸,哎,一下子接到一个电话,他在家里,哇,晚上,在那个远处工厂的大喇叭,因为我们家里没电话嘛,大喇叭叫,哎,王家驹,快来接电话。很远呐,要从那个生活区跑到那个工厂里。
我爸想,完了完了,妈妈死了,就等于我奶奶死了,完了完了,平时谁打长途电话啊。跑啊跑啊跑,跑到工厂喘了气,好在人家没有挂,接到电话,等于说是他的老同学,就是上海的老师啊同学,还惦记着我爸爸说,哎呀,在山里面没事干,说武汉军区要排话剧,排得很好,愿不愿意来。我爸爸说,好啊,那是一个机会,就出去了。
那我爸爸之前在干嘛呢,我爸上戏的,怎么会到工厂呢?因为没办法,你必须来啊,一调就来了,来了以后,当时是分到工厂里当工会,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没事干,然后领导开会的时候他就跑过去,给人家把那个话筒扶好,啵啵啵,好,哦,响了,好,下去坐那儿,人家领导讲话。
他是个导演,他是个演员,他就在那儿待了几年,实在没事了,结果就是贵州的省京剧团什么的要排样板戏,听说你们厂有个导演,人才浪费了,到我们这儿来行不行,所以我爸就到那儿搞京剧去了,样板戏,其实也没排出几个来,所以就整个在那儿耽误和浪费,其实是浪费了十几年。
那么等到我们到了武汉以后,那么我作为我个人的,刚才我说了就是所谓的故乡和他乡的这个困惑,开始真正开始了。因为什么呢,我在贵阳,不刚说了嘛,我就是贵阳人,而且我喜欢这地方,青山绿水,真的很好,小孩也不上学,瞎玩儿,60年代初期人多,天天在外面玩。
好,等到我要走的时候,我不同意啊,我跟我爸商量,跟我妈商量,我说你们走吧,我不走,你随便给我搁哪家,说我就在这儿。因为我当时那个时候小,你别看小,我有可能是不是成熟得早,还有暗恋对象。哇,那小姑娘,简直是五迷三道的,当然也从来没说过,没表白过,不像现在那么早能表白。
那时候说不行,我离开了以后怎么办,那这一切都没有了,我的初恋暗恋对象也不可能,我也没机会说了。但是没办法了,已经阻挡不了这一切了,那人家说你要赶紧走啊,这个地方,大家想走还来不及呢都,赶紧走,我们就走,所以我们就离开了。
我最近拍一个电影叫《闯入者》。为什么我到了拍了两部《我11》《青红》之后,还在拍《闯入者》呢,为什么絮絮叨叨这么半天呢?就是因为我在拍《闯入者》之前和这个期间,这个社会有个流行的看法就是叫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向前看。
那我对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要得到质疑的,要重新思考的,因为你怎么可能忘记过去呢?一个人到现在的人格的形成和成长,跟过去是有丝丝缕缕联系的,你斩断过去,你不可能凭空蹦出来你这个人。
那么国家也是,不管那个时候,六五年,这个大三线的这么一个建设,匆匆忙忙地这么一上去,那个时候还合着文革,其中那种疯狂和非理性的东西在主导着所有这些东西,等到你现在过去以后,你斩断,不要想,我认为这个不妥。
一个国家更需要去面对它曾经的过去,曾经不管你犯过的错误也好,取得的成就也好,都去面对,去总结,以防止未来能够再重犯。《闯入者》其实就正好说明了这个,一个人的一生到晚年了,实际上他年轻时候做过的事情一直在追随着他,一直萦绕他的心里,是去不掉的,心魔是去不掉的,那么必须面对,把它解决。
其他国家对历史的这种正视和面对,我觉得都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这种影响为什么到现在还有,其实从我的判断里来说,理性对待很多事物是至关重要的,就目前为止,大家看到的影响,就比如说水库啊,哟,大坝不得了,能给全国都发电,现在呢,是不是一些地质灾害是由它引起的不说,但那个时候也是有几百万的移民,从那个库区移出来,移到了他乡,那么这些人的命运一定也会受到改变。
还有现在大量的城镇化,拼命地发展,哎呀无序,哎呀不得了的发展,致成的环境污染雾霾。这都不说了,还有很多农村的土地扔掉不干了,因为没法活嘛,都要到大城市里来,挣钱数钱人民币这个时候,那么大量的土地在失去,大量过去的家乡也都失去。
所以中国的这种几次大范围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欠缺一些很理性的看待,很理性很科学地去安排,让以后不再重犯这样的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个人现在秉承的就是说,不随大流,在疯狂之外,我保持一点点理性,一点点判断,这是我要做到的,包括我做电影也是这样。
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我的公司同事说,你呀,你说这话题肯定太沉重了,确实,你看,刚才多么欢声笑语,现在特别沉重。他说你在结束的时候一定要编几个什么心灵鸡汤,因为心灵鸡汤大家爱听,心灵鸡汤可以传播得广啊,点击多啊,开心。
我想了半天,我不会想心灵鸡汤,没有那么幽默,但是我想,回到我自己吧,就是说,有人劝你说,哎呀你呀,老想这些事儿干嘛呢,累不累呀,你多拍一些好看的好玩的电影,把票房挣好了挣些钱就完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那可是我在想,我是干什么的呀,我能干什么呀?我不就是一个导演嘛,摄影机不就在我的手上嘛,那么,我面对发生的一切,面对曾经的一切,我怎么能够无视它,怎么能够不把我的权力用上呢,去关注它。
给你们看看这个,这是《闯入者》在去年拍的。是这样的,当年的三线红红火火是这样的,就去年所以历史其实它并没有结束,并不像你们看不见就以为结束了,它没有,它还在这里,活生生的,只是人去楼空。
所以我《闯入者》里面这个女主人公,直接就是坐了一趟火车,从北京到了这个地方,就穿越了历史。像这个东西为什么在我心里压得那么重,而我是掌握摄影机的人,中国这样的变化,这样的现实,我为什么不去表现一下,为什么不去记录一下,以免到未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像这样剩下这样的东西,我重新再去造它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的摄影机在当下社会的不缺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作为娱乐化的工具啊什么,大家很开心地看一些电影,这也是必然的,应该的。所以说,于我来说就是,虽然我身在他乡,但是我认为我心里是有故乡的。
我心里这个故乡,它经历的一切,它的痛苦,它的欢乐,包括它现在有好的有糟糕的现实,还用它未来我们期待,它的美好,这一切的一切,我认为我和我的摄影机,都不应该缺位,也不应该缺席。
谢谢大家!
2015.03.22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