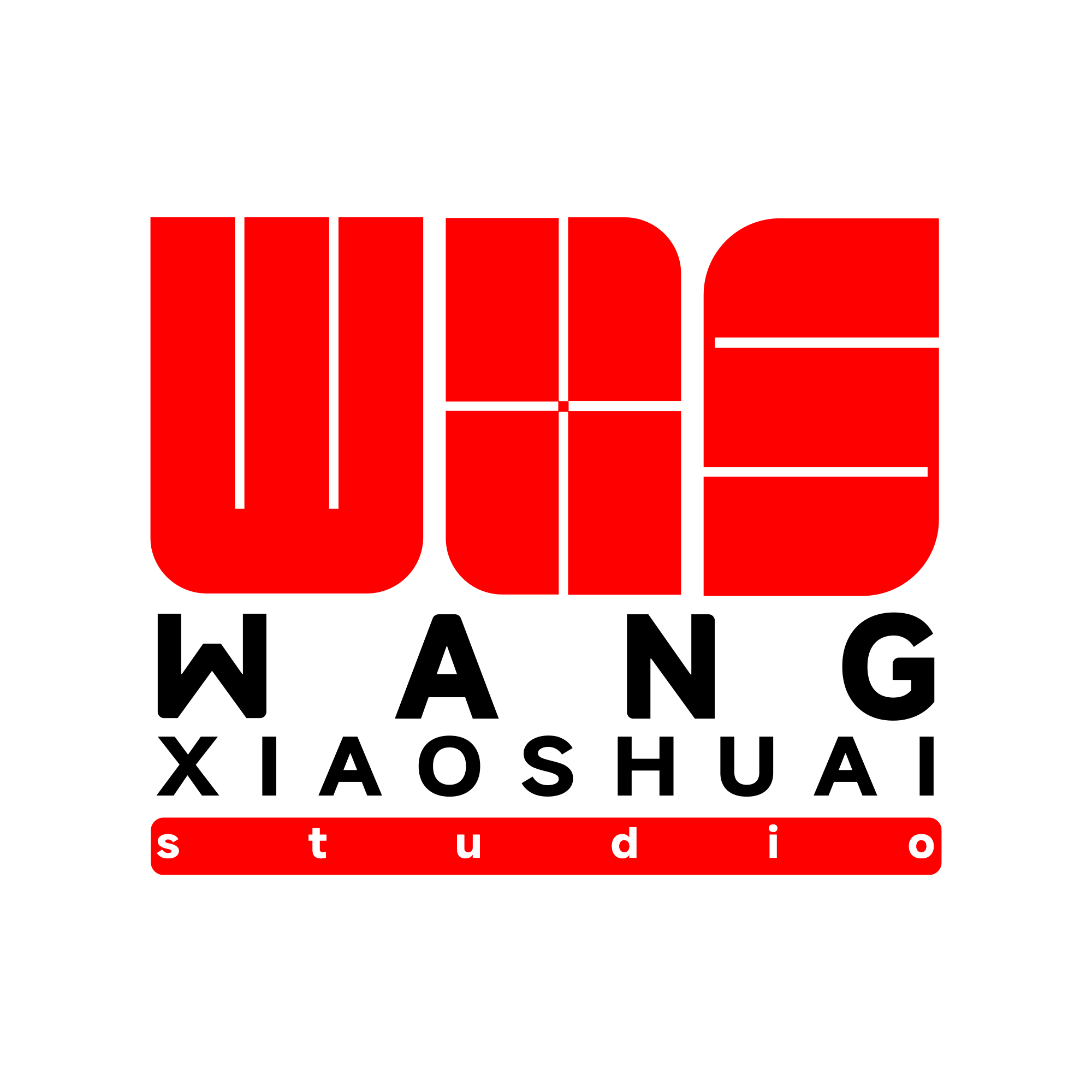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薄薄的故乡》序
这是一个中国人见面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对付,或者说这几乎不是一个问题,只是一种互相打招呼的客套而已,就象问你“吃了吗?”一样。但是对我来说每每遇到这个问题,就真的成了问题。因为我无法就象回答“吃了吗?”“吃了”或者“还没呢”这么简单。而不理会这个问题,又会使发问者觉得纳闷,“这个问题很难吗?”
熟悉我的朋友这时就会为我打圆场,说这个问题可复杂了,我来替他回答吧:他出生在上海,祖上闯关东去了丹东,父亲是山东人,然后又到了合肥,不过这都是他没呆过的地方,他从几个月开始就去了贵阳,在贵阳长大,然后又去武汉,在武汉上中学,十五岁就到北京上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福建,现在人在北京,但是户口在河北涿州。所以,他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朋友说的这些全是事实,因为我自己已经重复过无数次这样的回答,我也确实无法回答我究竟是哪里人。所以我说“你老家是哪里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问话的人会说,这不难啊,你出生在上海,就是上海人啊。
可是我出生才几个月就随父母内迁走了,连户口都没有上过,我怎么好意思说我是上海人呢?
问话的人又会说,那你户口本上写的是哪里呢?我说我的户口本上写的是“辽宁 丹东”。父亲不愿意填写“贵阳”,就把祖上闯过的地方当成了我的祖籍,而那个地方连我父亲都没有去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讲出生地,只讲老一辈的祖籍,直到现在,我莫名其妙地当着辽宁人。
每到这个时候,发问者就垭口了。
实际上一直到我拍“青红“之前,为了让这个问题简单化,我都会回答“贵阳”,因为我从有记忆起就在那里生活,成长,那里是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老家,或者说“故乡”。
事情的变化开始于拍“青红”的时候。为了看景我回到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少年时的伙伴们重又聚在一起。那一次我以为我终于回到了我口口声声的故乡,可是不曾想在他们眼里我更象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者。虽然众多少年时的记忆重新被唤起,这些记忆于我来说是全部,而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遥远而模糊的片断,它们存在过,但早已被后来漫长的岁月覆盖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用纯正的贵阳话交流着,偶尔冒出的两句上海话似乎是在照顾我这个外来者,也正是这偶尔的“乡音”让我确信眼前的他们还是他们。“贵阳话听不懂了吧?”“我是贵阳人怎么可能听不懂?”就在我说我是贵阳人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用一种从鼻孔里冒出来的声音讥讽到,“你怎么可能是贵阳人?我们才是贵阳人呢。”
这句话瞬间击碎了我心中本来就脆弱的幻影。是的,一个十三岁就离开了的人,还有谁会接受你是他们中的一员呢?
贵阳作为故乡这根稻草就此断裂。心目中自以为的故乡在同学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中彻底化为乌有。
从那次起,我在那句问题面前开始凌乱。有时候为了象听到“你吃了吗?”这个问题一样简单应付,就说“我没有故乡”。
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却要去写故乡,可能正印了人们说的,越没什么越想炫耀什么吧。当然不是为了炫耀,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在和编辑冬梅讨论书稿的时候,她说,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故乡感已经越来越淡化了,哪里都一样了,更多故乡的意味都只能在记忆里去寻找了。这使我释然了许多。是的,物理上的故乡正在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保存记忆其实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乡。
因此,你可以失去故乡,但不可以失去记忆。记忆将成为另一种故乡本身,很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记忆回到故乡,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处。
写下这本书,就是试图用文字找回“故乡”,或者是用文字把“故乡”变成记忆,然后压缩进这几页薄薄的纸里面,以免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