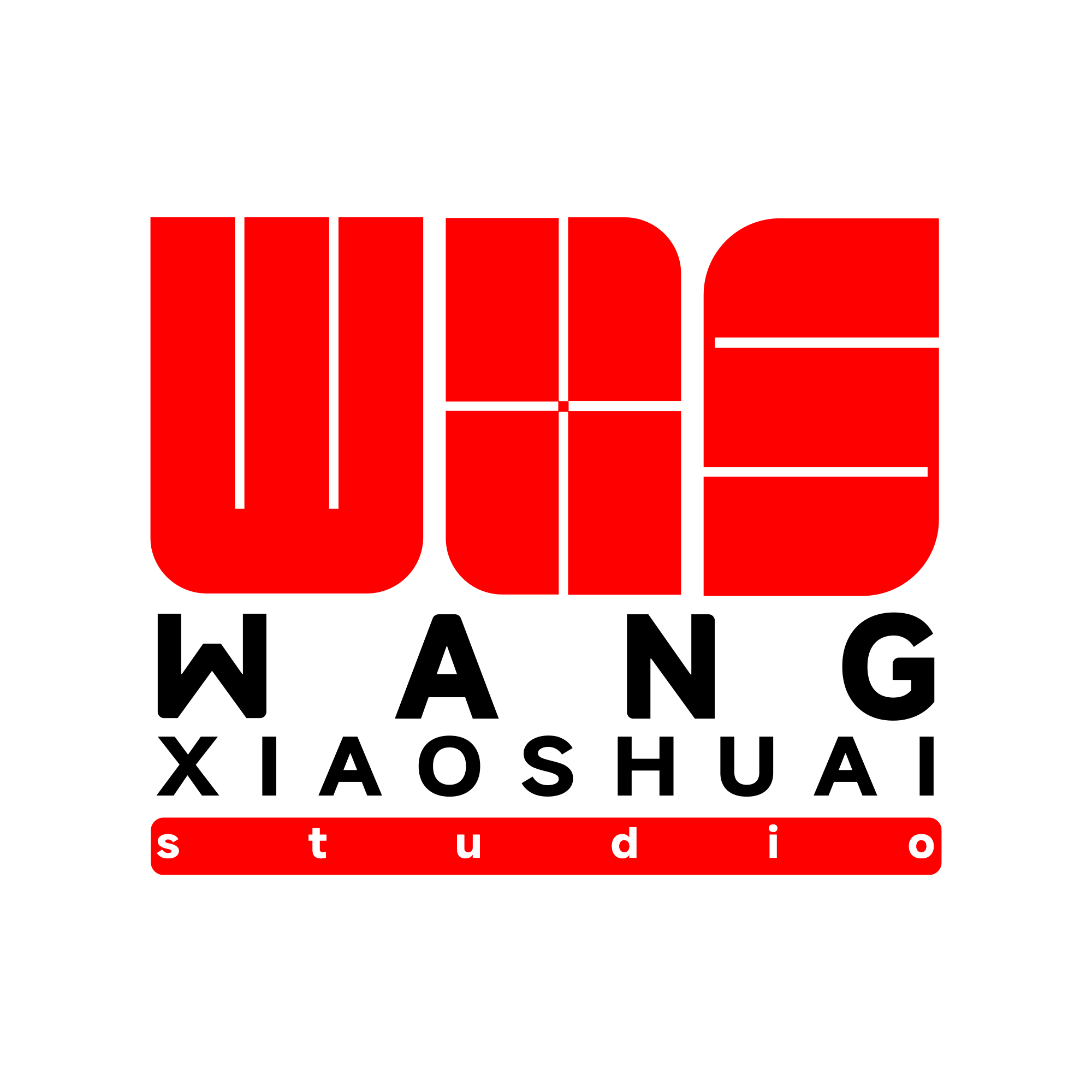重新回到北京已经是90年代初了。街边多了许多临街的大排档,店主用电线直接把灯泡吊在外面,有的铺面外面用了一种当时很时髦的小灯串起来的灯帘,人们叫它满天星。黄昏来临的时候,满天星亮了起来,使得北京看起来更加热闹了。
我们坐在东四和隆福寺交接的一家饭馆外面,这是一家广东大排档,据说是两个广东的姐妹开的,在当时的北京城能吃到粤菜,是一种时尚。刘小东和我喝二锅头,喻红喝汽水,吃的什么记不起来了。从1981年我考入美院附中,就和小东认识了,那时我15岁,小东18岁,比我高一届,和喻红偷偷的谈恋爱到大家一起玩耍已经是他们进入三年级的时候了。之后他们先一年进入美院,我后一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89年我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这意味着我将永远离开学习生活了八年的北京,离开许多的中学和大学的同学,包括他们俩。
其实我真正到福建报到是89年一年以后的事情,这期间刘小东举办了他个人的第一个画展,并且一次性把画卖了出去,成为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和有钱人。我后来在福建期间,我们通过仅有的一封信,我说出我的绝望,他在信里说要赶快干事,这样友谊才能持续并平等。
我是90年9月份到的福建,92年初回来,然后我们就坐在东四的这个时髦的大排档前,喝着二锅头,吃着粤菜。我们有两年没有见了,我说我回来了,而且不走了,重新当回北京人,就算当不回北京人,我也要赖在这里不走了。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北飘”这个词,算起来我应该是第一代北飘了,并且一直飘到现在,用每年一换的暂住证维持着我在北京的合法性。每次推开辖区派出所的门,那个管事的警察大哥就会说“哟,来了,我就说你该来了吧,最近又有什么大作啊?”因为他认识我,使得我每次像做贼一样心理稍微缓和一些。
就是在那个粤式大排挡里,我决定流浪北京,并且为了让小东放心我这个朋友不会连累他,会像他信里说的会做点事,不要拉大差距,我正式宣布我要拍电影了。显然我还不知道要拍什么,只是恐惧让我必须要先把它说出来。当时的座位是我一个人坐在小桌子的一边,小东和喻红并排坐在对面,我看着他们俩,念头就冒了出来,我说就拍你们俩吧,当时我的样子一定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们说为什么是他们,我说没有别人,因为还没有一分钱,不可能找正式的演员来演。他们说他们能演戏吗?我说不用你们演,呆着就行,就拍他们,也就是拍我们。他们同意了,就是为了帮我成就自己的一个事,这样将来可以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们同学,导演王小帅。
其实冒出这个不靠谱的想法以后第一个不是找的他们,先找到的是邬迪。我在学校期间邬迪已经以机械员的身份拍过几部戏了,按当时的说法算是跟过组的人,后来他又参加了一个留学生的学生作品的拍摄,我们认识了并成为朋友。
邬迪因为父亲是儿影厂的职工,所以他在学校边上儿影厂的家属楼有一个小小的一居室,那个一居室就成了我们的窝点。那时候能自己拥有一个一居室完全像已经拥有了天堂。读书期间,毕业之后等分配的那段时间我们就在哪儿喝酒,打牌,谈恋爱,留下了许多轻狂记忆。分别两年之后再次找到他,他已经有了正式女朋友,小窝点没法长住了,只能背着随身唯一的一个挎包,开始流浪北京。记得在学院边上专利局招待所10元一铺的地方睡过一晚,小月河一个剧组的美术的床上睡过一晚,第二天一早等剧组乱烘烘地出发之后,自己再顺着墙边溜走。有一天转移到小月河后面的一家不知名的旅社时,彻底绝望了,巨大的恐怖伴随着寂静的黑夜笼罩了下来,难道就这样了吗?那个从贵阳到了武汉,又从武汉兴冲冲来到北京,做了将近十年临时北京人的我,就这样在无边际的无助中再一次被彻底遗弃了吗?北京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户口,没有了档案,没有了可以和朋友平等的座位。街边新建的一栋栋楼房,每一个窗户里亮着的温暖的灯光,街边新起的饭馆,大排档,人们坐在那里喝着啤酒,这一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恐惧和孤独压迫着每一根神经。回想自己义无反顾地奔向中国地图上最偏远的那个省份,那个之前几乎没在意过的城市,以为电影的大门会为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敞开。而现实是你几乎是用生命在给自己开一个天大的玩笑,如今没人能够挽救你了,学校跟你的关系结束了,朋友也都一样年轻迷茫,这天下只剩这么一个幼稚无知的大傻子了。在那个深夜,自己咒骂着自己的愚蠢。但这不是最后,生命和世界都没有走向最后,明天天还会亮,你还要离开这个旅店,在街上寻找下一个可能免费的床铺,你必须做点什么!我是干什么的?我想干什么?
天亮的时候,我找来了邬迪,还有何建军,我说我要拍电影,马上,不能等了。他们说你有投资了?我说一分都没有。他们说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去找九个导演,九个摄影,一起当导演,一起当摄影来拍我们的第一部电影。我认为这样不行,导演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工作,人多了会乱,还得分着干,自己闯出一条血道。集体创作的事情被放到了一边。
再后来我找来了刘杰,加上邬迪,我认为摄影师我有了。刘杰和我跑回了他的老家取得了保定胶片厂的同意。保定乐凯胶片当时已经不生产能用于电影拍摄的大本胶片了,大本胶片出厂时都被裁成35张一卷的照相用的胶卷,我们说服他们再次振兴国产胶片,他们同意将在我们拍摄期间特意为我们保留一些大卷,这样我有了胶片。我们又在北影厂的器材库里找到了一台早已弃用的摄影机,这台摄影机不能用于同期录音,一开机哗哗地响,像是拖拉机从你耳边开过。我不管那一套,只要能挂上胶片,把人拍动起来就行,声音后期再配,这样我有了一台摄影机。
这期间,我坐在东四街口的广东大排档里向小东和喻红宣布我要拍电影了,演员是他们俩,这样,我有了演员。
剧本在美院的学生宿舍里完成了前半部分,取名“冬春的日子”。我向小东和喻红道歉,我说这个电影里的他们还没有办过个展还没有卖出过画,还没有成功,这个电影里他们是迷茫的两个人,连爱情都要走向绝路。我拍的是他们的影像,可附着的全是我现在的心境,一个恐惧迷茫、失败的黑白世界,这个世界还连接着我们89年毕业的人的所有境遇。后来拍摄的过程中还找来了娄烨,让他以一个89年6月之后一个逃亡者的身份出现,扮演一个有气无力的逃亡者,在他身上放置了一个我。
十几年前,一个抱着当一个画家的理想青年,一个人离开武汉,开始了在北京的独自生活,那个时候的他,完完全全想不到他的职业未来会是一个如此遥不可及的梦。父亲苦心经营的绘画理想结束了。虽然父亲曾反复劝告自己不要走有关戏剧或电影的路,说这条路太辛苦,所有的一切你都决定不了,演员可能一辈子等不来一个机会,导演可能一辈子无法自由表达,因为除了戏剧电影本身的集体创作形态会使一个作者很容易就被淹没掉个性之外,更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国度,我们特殊的意识形态特性,很多时候导演只不过是个傀儡罢了。而绘画就不同了,绘画你可以独自一个人完成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可以是山,是水,是花鸟,无关乎别人,无关乎政策。在绘画艺术里,你可以自由自在。
因为父亲一生的经历,我相信他说的话。
父亲的一生,跟戏剧有关,最后又跟戏剧无。父亲195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导系,后留校任教八年,我完全可以设想,这八年是父亲一生中最美好的八年,戏剧、艺术、教学、演出,完全沉浸在舞台的迷幻之光中。改变来自于1966年,中央提出开发大三线,中国沿海的工业大城市里的军工企业,大部分要被迁到中国西南一线的山中,以贵州、四川、云南甘肃一带为最重,母亲所在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因为生产的是潜艇上的潜望镜,属于军工企业,几乎整个工厂被迫迁到了贵州。那一年我出生。父亲无奈放弃了八年的教学生涯,随母亲和我去到了贵州,从此,戏剧舞台在父亲身上就名存实亡了。那一年,父亲31岁,母亲28岁。父亲以31岁黄金年华就告别了舞台,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支配。唯一的曙光来自于13年后,父亲受邀赴武汉军区文工团演出话剧,从此从军,希望以武汉为天地重新回到舞台。但好景不长,44岁的父亲刚刚准备开启他生命的新一轮活力不久,军队文工团遭到解散,不到50岁的父亲便早早退休。失意和落寞是如此纠缠着父亲的一生,所以他对我反复说的话我不得不信,并且也在一直饯行着他的愿望。但当美院附中即将毕业,面临高考的前夕,自己突然决定大学转读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时候,父亲只能长叹一声。但一生虽落寞,但性格乐观,崇尚自由的他没有阻止我,只是说导演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我人生第一部影片的拍摄现场的时候,我心里只能说对不起了爸爸,你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影片拍摄了5个月左右。 拍摄期间那么长主要是因为我的唯一的两个演员只能在每周六的下午和周日拍摄两天,其余时间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两人已经分别在美院附中和美院本部留校任教。这样,我们周五把机器从北影厂借出来,周六、日拍两天,然后还回机器。周一我独自拎着拍好的胶片,坐火车到保定冲洗。唯一的经费是从摄影系同学张洪涛处借来的5万元,主要用于基本的吃饭,交通和所有的后期费用。那时候已经时兴拍摄广告,张洪涛有经商头脑,早早开设了广告公司,开始经商了。
主要的场景在中央美院附中院内,小东留校任教,学校在过去我们的四楼的顶头给他分了一个小间,当卧室兼画室,很多他早期的作品都是在这不足20平米的小屋里诞生的。
重回母校对我这个已经和北京没有了关系的人来说,心情是无法言说的。四年的时间就生活在这个封闭的小院里,记忆中临着美术馆街的那个门房,每天盼着家信能够插在门房的小木箱子里。进楼的大门上悬挂在那里的老破铃,总是在每天凌晨你睡的正香的时候把你闹醒。宽敞而幽静的走廊,地面幽幽地反射着冬天的阳光,摆放着同学们的画架的画室,油画颜料的味道似乎融进了空气里。小院里唯一的一棵枣树,每到秋季开学的时候,我们围着它打下树上成熟的大枣。从79年恢复招生至今,这个红砖砌成的四层大楼和楼下不足两亩地的小院,迎来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和他们青葱时光。
我决定放弃考中央美院本部是在1984年,决定选修课以备考大学的头一年。具体什么季节我记不清了,那一年学校组织放映了一场当年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中国电影《黄土地》。那一刻让我意识到电影可以和绘画很像,电影不一定都要像是《渡江侦察记》或《春苗》一样的。也是在那一刻,让我知道了除了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之外,北京还有一个叫电影学院的地方,而且这个学院还有个专门教导演的导演系。原来电影也是有导演的,我意识到我未来可以做什么了。在这之前,我遇到了和我在武汉华中工学院附中上初二、初三时一样的困境,那时我的数理化已经完全无以为续了,往普通学校考虑,我怕连高中都上不下去。幸运的是我有绘画,这一在当时所有人看来奇怪的技能,而这一技能的考试,文化课方面数理化的成绩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当时报考美院附中,多少也有一点逃跑之嫌。现在这一困境再次重演,经过了三年附中专业绘画的训练,我竟然连一幅油画创作都完成不了,我本计划在一幅长一米,宽八十公分的画布上完成创作,构思是这样的,华北一望无际的农田,丰收过后的土地,农人在田里忙碌着,马在边上悠闲地吃草。可是没开始多久我就陷入了窘境,然后就在画布上一遍一遍地改,把天从有着薄云和夕阳 的黄昏改成一碧如洗的蓝天,马儿从画左画到画右,本来有的农人被油料抹掉了。三匹马变成了一匹马,这一匹马又从棕褐色涂改成了白色,那是一次无能的徒劳努力,我对着画布一筹莫展。老师和我都很清楚,油画系不太可能了。而上不了油画系,那还能叫画画吗,还能叫画家吗?老师善意地提醒我可以考虑报考连环画系。连环画?那是什么?小人书?我们小时候人人热爱的一页页像插图一样配着文字的小人书?那是画画吗?老师说我平时活泼好动,好模仿,会讲故事,连环画应该适合我。我始终感觉到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失败和挫折总是在恰当的时候出现一下,但却总是出现在你还来得及去思考和改变的时候。1984年的某一天,在接连看完《黄土地》和《一个和八个》之后,我放下了那张已经被我涂抹得像墙皮一样厚的油画创作,走出画室,来到了一楼的图书馆,在电影类的目录中,找出两本书,《世界电影史》和巴赞的《电影是什么?》。
与电影学院不同,附中占据着北京市可以说最中心的位置,美术馆和隆福寺的街口,门房出门对面是中国美术馆,身后是隆福寺,右转上街走到北兵马司、宽街,左转上街过美术馆和华侨大厦的十字路口再前行,经过人民艺术剧院就进入王府井了。而当时的北京电影学院远在北京的北部,由今天的京八高速一路往北,经马甸、清河、回龙观、沙河,然后在一个叫朱辛庄的站下车,再拐上右边的农田沙石小路往东走出约两公里,在沙石路北面出现一个普通校门,门的右柱上竖挂着“北京电影学院”几个书法字。我们计算过,从校门出来走过沙石路到大路上大约用时20分钟左右。上了开往城市的公共汽车一路到今天的马甸桥,用时大约40分钟,从马甸桥转111路公共汽车到隆福寺的美院附中用时大约也在40分钟。这就是最顺畅的一次旅途。我知道,我一旦考上电影学院,当了四年城里人的我又要再一次被扔到乡下去了。从贵阳乡下,到武汉乡下,如今要到北京乡下去了。我这个被武汉同学称为“乡下娃”的人名副其实地离不开乡下了,但心情是无比愉悦的,毕竟自己要成为一个大学生,而且是一个导演大学生,并且虽远在郊区但毕竟还是在北京。
真正一次觉得自己彻底乡下了是在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我在地图上第一次认真查找了一个叫福州的地方,它在离北京,或者说中国版图上最远的东南角,甚至已经超越了西南贵州的位置。贵州的下面还有广西,而福建的外面,就是海了,海的对面,是台湾。我被告知正式分配到那里,福建电影制片厂,户口和档案已经离开电影学院,如果我不去,我将无处安身。记得是1989年8月左右,当时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著名编剧陈剑雨先生亲自到学校要人,陈厂长的女儿是如今著名雕塑家向京,我在附中的同学。陈剑雨找到了我们,承诺我只要同意去福影厂,那里将是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我答应了。可是,手续还没办完,陈剑雨却已先行离开福建厂。我永远记得一年后的那次报道旅行,在福建。
很小的时候坐过时间最长的一次火车是从贵阳到北京,2天2夜。但是因为年龄太小,过程已经记不清了。另一次是15岁时只身从常州的大伯家坐火车赴北京,那次是去美院附中报道,从上车就被堵在车厢边的厕所门边再也挪不动半步,就这样两天一夜地站到北京。然后就是9年之后的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漫长的火车之旅,整整三天三夜,头两天的窗外基本还是曾经熟悉的景色,对时间的概念还有以往坐车的记忆。进入第三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不对劲,怎么火车还在开啊,我这是要去哪儿啊。望着窗外墨一般的黑暗,看着铺位上睡得很香的同学凌云,和一整个车厢沉入梦乡的旅客,恐怖和孤独感如凉水般慢慢地浸透了全身。他们睡得多香啊,他们有的是回家,有的可能只是短暂地出差,游玩。凌云虽然也和我一样被分配到福建厂,但他的爱人已经早早地安定在了福州,他这也是回家啊。而我是算什么呢?奔赴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不是暂时,而是永远要生活在那里了,自己23岁以后的人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朋友,同学,未知的一切要在那里展开了。崩溃出现在第二天早晨,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的时候,车轮枯燥声音粗暴地持续着。还在开吗?窗外的景色已经全然变了,眼前一条宽阔的河流跟随着前进的火车,河面上蒸腾着一片蒙蒙的雾气,使河岸两边的树木、山丘掩映在一片朦胧之中,初升的太阳血红而无力地悬挂在那里,就象一个刚刚睡醒的人打着臃懒的哈欠,它的光芒还没有完全显现,但是日的光芒已经逐渐代替了值更的黑夜,时间无情。这是哪里啊,这还是中国吗?这是我二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视觉经验。“闽江”凌云说,“我们已经进入福建了。”“遥远”这一概念第一次那么真切地呈现在我脑海中,它已经不单单指物理上的距离,它还含有心里层面对未知的无望和恐惧。
这已经是第三个白天了,虽然这一天我们也将抵达我们这一次旅途的终点,但不行,这一切都错了。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等到了终点,等这趟列车真正到了终点,一切都来不及了,一切都没法改变了,我就要站在那个陌生的土地上,成为那里的一个居民,不是过客,不是游客,而是一个真正的本地人了,一切就都是真的了。我跟凌云说我要在下一站下车,我不要到那个地方去了,我以为只要我中途停下来,对某个东西说我错了,我就能改变一切,从新回到过去,让一切从新来过。我急切地重复着,表露这不加掩饰的恐慌。我要下车,我要坐火车回去,不能等到一切都变成事实。
我在那辆载着我奔向那个不可逆转的结局的火车上做着徒劳的挣扎,我跟凌云描述着我想像中的情景,那里没有人会来接我们,我们到了那里,会有一个门房老头问我们是干什么的,然后会有人把我们领到一个招待所的房间,然后我们就被扔在那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对,不是我们,是我。因为你会直接回家,吃你老婆已经给你准备好的饭菜,睡上你和你老婆的床,然后第二天早上你会穿着拖鞋,睡衣,在自己家门前的小院子里散步,喝茶,你的一切都会尘埃落定,你心满意足。凌云看着我,无言以对。
太阳终于显现了光芒,白天冷酷地驱走了黑夜,时间继续着冰冷地脚步,无论你如何挣扎,都已经无法改变在前方等待的事实了。
那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终于被这个毫无感情的庞然大物驮到了终点站福州车站。
没有人来接我们,甚至凌云的老婆都没有来,完全陌生。我乞求地看着四周,巴望着哪怕有一个可以抓住的同情的眼神,这个眼神会走过来说,我知道你不属于这里,来,我送你回去。
凌云陪着我先到厂里,谢谢他没有直接回家。一切与我预想的一样,空空的厂门口,门里一个不大的小院,院子中间一个小小的水池,池边用铁栏杆围着,水池后面是一座三层的小楼,灰白色。这个楼除了是办公楼还兼着一些职工的宿舍,厂长室在二层左手靠近走廊的第二间。厂门口左右各有一栋宿舍楼。绕过办公楼有一个小广场。比篮球场大一点,再绕到办公楼后面是一个四层楼的招待所,厂里不拍戏的时候这里空无一人。自从我进厂后,它一直空无一人,我曾经是它唯一的住户。在招待所的边上,小广场的后身是一个摄影棚,不算大,但已经是一个正式的摄影棚,听说当年“木棉袈裟”“欢乐英雄‘等很多戏都用过它。就是这些了,门房的老头问过了我们的来意,叫来了一个中年妇女,是管后面的招待所的,她把我们领到了后面的招待所,我们爬到了三楼,停在随便的一个房间前,妇女打开了门。屋子里没有窗帘,四张生锈的铁皮床架子,上下铺的,可以睡八个人,没了。妇女说食堂在楼下的平房里。可以先找她来换饭票,一会儿她会抱一床褥子和被子过来。记得那时已经过了中午,阳光灿烂,除了我们仨和门房,整个过程中未见到一个人影。宁静中可以看到阳光下飞舞的小虫和偶尔被我们唤醒的粉尘。妇女给我抱被褥去了。凌云和我抽了一根烟,“我走了,弄好了哪天到我家吃饭去。”
随着他脚步的最后消失,尘埃落定。
在死寂一般的空气中,我,只有我和我在一起了。
我确信这是一个幻象,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的确信不起作用。我坐实了这里,这间屋子,这些铁床,这里的空气,有一点发霉的灰墙,是我,是真的我在感受这一切,一切都是真的。
不知道在招待所究竟住了多久,有一天,厂里终于在办公楼三层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房间,可以算作我的家了。因为厂子太小,需要固定上班的人不多,一层和二层就够用了,三层实际就成了宿舍,有家和单身的都在一个走廊里生活着。我的房间左手边是女厕所,斜对面对着楼梯的是厂里第一个分来的大学生,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文科生邓洁,男性。据他自己说是全福建第一个由外分来的大学生。我们成为酒友,大部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们会从食堂打上饭菜,然后边吃边喝到凌晨,有时候到天亮。他能喝,也能聊。那时我的工资是这么安排的,我知道注定有一天我要走的,就把每月工资的一小部分留在枕头下面,一部分买一瓶金奖白兰地,一部分买烟,剩下的全部买成饭票,这样每月发了工资的这瓶金奖白兰地就是我们神仙一样日子的主要支柱了。压在枕头下的钱几个月以后就足够可以买一张联航的机场直飞北京了。我知道,我要离开福州的那天,绝对不会再去坐那趟火车了。邓洁现在应该已经属于退休状态了,后来的几次回榕和他来北京,我们都是不醉不归的。当时单身的他,在我离开不久就结婚了,育有一女,生活美满幸福。夫妻俩热爱茶艺,也收集大量的紫砂壶。作为文人的他,多年来一直说要写一个惊世骇俗的电影剧本,但至今还没有等到他完成这个愿望,喜爱和研究茶壶倒使他在福建茶壶界小有了名气。走廊的中部,我的右手隔两个门住着王利军一家,那时他已经可以当上摄制组的制片主任了,女儿刚刚会满地乱爬,我随便一窜门,就可以在他们这正式的家里坐下来吃一顿家里的饭菜了。以后每次回榕基本就是在他们夫妇的安排下渡过。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太太用摩托车带着我穿过福州的大街小巷去帮我办理护照。我们约了多年的合作也在13年“闯入者”的时候如愿了,他来做了“闯入者”的制片主任。王利军家的斜对面住着郑文昌,那时已经经常不在厂里干活而在外面单干了,用他幽怨的话说“厂里哪有活干”。文昌的老婆孩子不在身边,大部分时间是他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上好的铁观音的茶香味就从他屋子里飘满了楼道。“来,喝茶。”文昌声音永远不大,一口闽南普通话。可惜极端善良的应雁去年去世了,他当年也在电影学院进修摄影系,我们算是校友了。我到厂里的头些日子就是拜他和他爱人的照顾,几乎天天顿顿在他家里吃饭。应雁高大魁梧,在做摄影之前是福建省水球队队员,一个潜水能从五十米泳池的这头潜到那头,可是没想到最后却结束在这里。听他们说,那天他按时去游泳馆游泳,这已经是他这几年保持的一成不变的规律了。他潜了下去,再也没有上来。应雁走后的不久,我正好去福州,在和他妻子拥抱时我流泪了,他妻子见到我大声地喊,“小帅啊,应雁没了。”
现在的我,每每想起在福州的日子,想起那些善良的同行朋友,心里竟生出与当年刚去时完全不同的感受,我要感谢命运把我带去认识了他们,他们使我在中国遥远的东南角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他们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财富。
就这样,我当了一段结结实实的福建人。北京似乎已经是一个远挂在天边的概念了。偶尔接到邬迪的电话,这个概念才又清晰起来,“哥们,那儿不行就回来吧。”他的这个话像极一棵希望的稻草,但我不知那是进路还是退路。小东来信说“沉住气,坚持住,我们都还在呢”。很多年以后的一次整理东西,又看到了这封信,我蹲在那里起不来,泪流满面。
我知道留在我前面的唯一一条路是争取拍片。只有拿到了拍电影的权利,才有改变的希望。
我在福州的二年里写了五、六个剧本,这在厂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一个天天平静如水的小厂里,这个小青年的一个个剧本像是一颗颗小小的手雷,同事们议论着,希望厂里能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导演,属于自己的摄制团队。虽然那时的福建厂已经拍出“木棉袈裟”“欢乐英雄”“阴阳界”几部异常成功的电影,但全部是借出自己的厂名而已,主创人员也全部来自外面,厂里的人大部分跟着做副手,好的时候通过厂里争取到和别人联合挂名。所以我这个出生牛犊的小年轻不经意间引发了这些议论。
时间在一次次的希望和失望中流过。当时的电影是计划经济时代,每年摄制的电影都有国家统一指标,福建是小厂,一年只有一个指标,拍好拍坏只有一锤子买卖,所以外借厂名合作最为安全,而让一个刚刚毕业的小青年来拿走这个人人渴望的指标是个多么天真的想法。
幻灭来自92年初的某一天,北京电影资料馆的领导来厂里视察,然后举行了一个会议。会议上资料馆领导说听说你们厂里有个叫王小帅的人,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你们应该让他拍片子啊。我说我就是,我在争取。厂领导发言说我们这里的大学生还年轻,要想独立工作恐怕还要锻炼5年。5年,这是一个我等待了无数次之后唯一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个信号清晰到厂领导的话音还没散尽,我已经站起来离开了会议室,我拐上楼,打开我的小屋,用二三分钟收拾了一个背包,从枕头底下取出我预备好的钱,转身锁上门,往右转到王利军的门口叫出了没有参加会议的王利军,把手中一把小小的钥匙交给他保管。他惊愕道“你去哪儿”,我说回北京,可能不再回来了,你帮我保管这把钥匙吧。这把小到不足小拇指的第一节大的钥匙王利军随后帮我保存了两年,当我两年后再回来办护照的时候,他骄傲的把它举在手上,他说有它在,没人敢踏进你房间半步。
然后我下楼,二楼会议室的会议还在继续,我想和谁打个招呼呢?这个想法没有让脚步停下。
从听到那个信号,到踏出厂门,用时应该不到十五分钟。
再见了福州,两年的光阴,两年的欢声笑语,两年的幻想,在走出厂门口的一瞬那,留在了身后。我嘱咐王利军不要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以为这是一种逃离,在这种逃离还没有安全完成之前,一切都是不安全的。在急急拐过街角,穿过菜市场来到大街上,确认后面没追兵之后,招手打车。车子启动的时候心还砰砰直跳。
重回北京,物是人也是,只是我已不是。一切都是从头再来。一个离开学校的人,早已不可能再有当学生时的骄气,社会就这么硬生生辽阔阔地铺展在你面前,家庭的支持,朋友长辈的赞美这时已如沉在水中的石子,河水就这么无情地流淌着,你要成为你自己水中的掌舵手,再无人能依。
母校中央美院附中和电影学院一如既往地热闹,一届届的学子犹如当年朝气的我们,而我已经踏不回这条河流。
但是变化已经在发生。90年代初的中国,经历了80年代整整十年的洗礼,压抑下的觉醒已经在发芽。当我坐在东四大排档和小东、喻红久别重逢的时候,张元正在筹备和拍摄他的“北京杂种”,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正在被人们谈论,一切都在变,一切又有了希望。暗流在涌动,北京还是那个北京。而我,又回来了。
拍摄了五个月的影片最后在新影厂完成了后期制作,它是那么粗糙,经历了太多不可想像的磨难,但是它就在那里了。
93年底,香港影评人舒琪和英国影评人汤尼雷恩把它介绍给了温哥华电影节,随后又开始了鹿特丹和柏林之旅。在鹿特丹,我们被放进了黑名单,我们通过香港来的传真看到了香港报纸上的大标题,其中有“七君子”几个字样,包括了当时在影展参展的七位导演的名字:田壮壮,张元,宁岱,吴文光,段锦川,何建军和我。这几个导演的作品都没有申请当时的拍摄指标,有的是未通过审查。记得电影节主席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转述了来自中国官方的要求,要求电影节方面停止放映我们的作品,同时要求我们主动撤片。事关重大,主席要我们自己做出决定,无论我们做出怎样的决定,他都会尊重。
我们一致选择了继续放映。我们几个围坐在一起,意见统一以后,我们静默无声。第二天,香港报纸就登出了国内对我们的处罚决定。当时看到传真,“七君子”这几个字还是着实的吓人一跳,让人联想到清朝末年的那几个人。
随后,“地下电影”和“独立电影”的称呼开始出现
1993年不算久远,1993年已经很遥远。如果从“冬春的日子”以无任何厂标的电影第一次于93年在温哥华电影节首映,到2003年中国电影自上而下的市场化行政指令,整整十年。而这十年正是传统体制下的电影,和边缘性独立电影运动共同组成的对立的十年。其中体制内的电影,一边羞涩地吸纳着外界资金,一边固执地不放开计划经济的指标制,致使许多独立兴起的民营公司,即使自有资金也无法独立拍片,挂靠国营电影制片厂厂标是唯一可循之路,而许多电影制片厂靠出卖指标完成着一部部规定动作。而同时,早期独立电影却顽强地,可以说“违规”地坚持着没有挂靠的制作方式,虽然在国内无法上映,但一步步地在海外拓展。这是一条暗流,是后来中国电影市场化之前的先行者。
除了电影应该走市场经济还是保留计划经济的模式,在这十年里迂迂回回之外,版权意识也不停地成为矛盾的焦点。到底出资者和挂靠单位哪个才是这件产品的版权拥有者?旧有体制下电影厂归国有,电影生产由国家计划投资,则版权可以说当然国有。但是这十年的后半段,社会资金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国有电影厂渐渐只是厂标的拥有者,甚至很多已经仅仅靠出卖厂标为生,那么,这样生产出来的一部电影版权还是国家的吗?当然03年之后,国有电影厂改制,市场开放,民营制片公司可独立拍片等一系列问题改变之后,原国营厂的垄断资源依然变身为民营公司不得不依附的大象腿这一现象依然持续了很多年。
时光荏苒,站在2014年的今天回看当年,那个惶惶然回到北京的青年从决定拍出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开始,两个十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电影也从市场之初的九亿票房跃升到两百多亿,这个青年也已经不再是青年,但是对电影的惶惶然之心却依然如初。记得03年,因为单车和二弟还在被禁止拍片的我,被通知去参加那个对我和其它的独立或所谓地下导演在内意义特别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除了得到一个我们可以拍片了的信息之外,也得到了一个从此电影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信息。那次会议被主要点名的有贾樟柯和我。同时参加会议的张元和娄烨正好在此之前已属解禁,虽然娄烨后来因为“颐和园”再次被禁。还有崔子恩,何建军,王超等。会议结束当天,我们并未像人们想象中那般欢欣,相反,新的担忧却悄然来临。因为独立影像的表达根本上无关乎地上地下,体制内外,它本身是一个自由创作的反映,体制外的自由和体制内争取自由同等重要,市场化只是一个基本的基础,这个基础本身比之其它行业就晚来了许多年。市场化当然是早就该有的必然之路,但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市场化?而在目前根本管理理念和意识形态不加改变的前提下,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表达,自由的创作能否在新的夹缝中得以生存以至发扬,共存于这个“市场”,这才是问题所在。
娄烨、贾樟柯和我,我们仨找了个酒吧,坐下,没有人乐观。我决定做“青红”,娄烨决定做“颐和园”。我们知道在新的市场化,商业化之后我们应该做什么,但心里却告诉自己,自己仍然想做什么。
很多人说你疯了,太不识时务了,我承认。同时我也知道,中国电影市场会突飞猛进,工业化制作会越来越成熟,中国电影新的高潮会扑面而来,投身于它的人们会越来越多,这一切当是极好的现象,这一切当是中国这个大市场所应得的。但有一条窄路也必要有人去走。这条路不会比头一个十年好走,相反会越来越难。但埋下的种子多了,破土的几率还会少吗?
从92年重回北京至今,我作为外来人口已经在这儿又生活了二十多年。这期间除了拍摄电影,一直没有断过身份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为了方便,2001年,通过朋友的帮助,我把在福建的户口档案落在了离北京半个小时路程的涿州,隶属保定地区。从那时侯开始,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涿州人了。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去,和我落户的人家吃一顿团员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已经真真地把我当成了涿州人。
“反正你已经这样了,就踏踏实实地做我们涿州人吧”
听了这话,心生温暖。确实,用现在的话来说,你是哪里人还重要吗?哪里留存过你的记忆,哪里就是你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