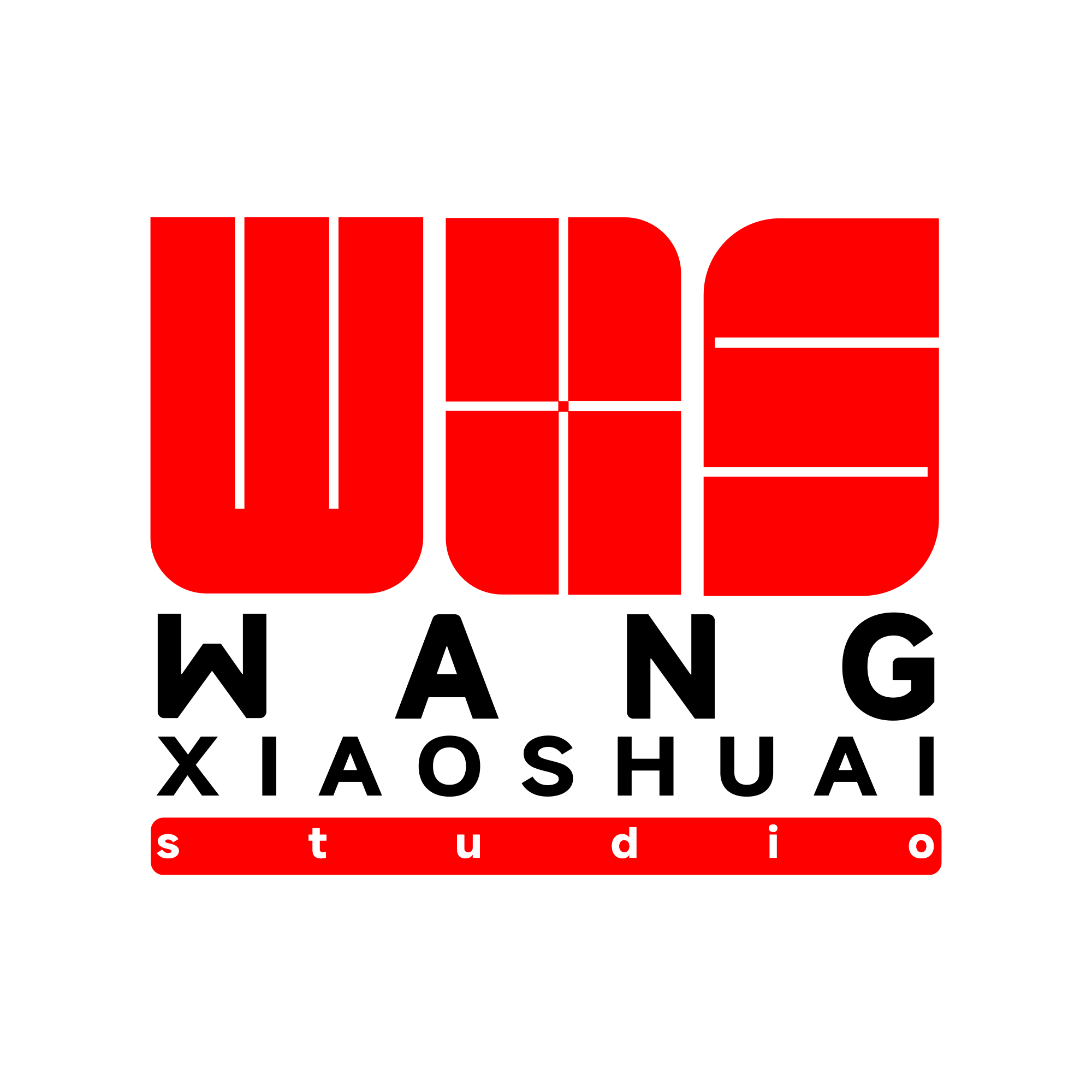物理上的故乡越来越同质的今天,保存记忆其实就是在保存精神上的故乡。你可以失去故乡,但不可以失去记忆,记忆将成为另一种故乡本身。
——王小帅《薄薄的故乡》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故乡是一个既定的标签,它代表着一个人的来处,但对于一些人而言,故乡则是可以被建构和重新定义的。这种主动性的背后却又蕴含着一种时代的被动。
时至今日,导演王小帅更愿意选择自己的故乡是贵阳,背后的原因是,他是一位“三线”建设者的后代。在拍了《青红》、《我11》和《闯入者》三部关于“三线”建设的电影后,王小帅依然觉得不够满足,关于自己的童年和自己父辈的人生,好像总有什么没有说够,于是又写作了一本《薄薄的故乡》。
不像我们惯常以为的那样,家乡总是温情脉脉的,有一种明确的召唤意义,王小帅笔下的故乡具有了更多的思辨性。《薄薄的故乡》里开宗明义就点明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这种无根的感觉伴随着王小帅的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当人们谈及家乡的话题,总让自己有些“自卑”。他是没有家乡的人,是像“浮萍”一样的人。
所谓“三线”,网络搜索给出的答案是: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而“三线建设”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布局,集体意志的体现,也标志着一种地区发展的不平等。
回忆自己父辈的“三线”经历,王小帅认为这是一段“理性”规划出的历史。活生生的人成为冰冷的机器,甚至出现白天还在上班,上头一声令下,下午就要搬家的情况。人们仓皇迁徙,以为不过几年时间就会回来,谁知道一走就是一辈子……
被动的迁徙和主动的迁移是不同的,在王小帅看来,改革开放后,很多人离职下海,主动去闯荡深圳。这种选择,即使经历千辛万苦那也是值得的。问题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都是由一个理性的概念改造的,人和故土的关系被暴力地改造,一代人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写。
1966年,王小帅出生于上海,但4个月后他就跟随父母远赴贵阳郊区支援“三线”建设。父母告诉自己是上海人,但成长在这个抬头就是山的地方,上海的概念实在过于模糊。
“我记得我是对上海的印象是通过一张明信片,第一个感觉是不知所措,明信片上是一张从高空拍摄的上海外滩的照片,和我此前所接触的所有关于中国的影像完全不同。震惊于中国怎么也有像纽约或东京一样的地方,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向往,既然我是从那里来的,我就想要回去。”
这种情绪后来被写进了电影《青红》(2005年),少女青红爱上了贵州当地的小伙子,却被父母告知自己是上海人,早晚要回到上海……青红想要扎挣,结果却是毁灭性的,她的青春被永远地葬送在三线的历史中。中国严格的户籍限制和特殊年代的管理,人往往被固定在某个地方,一些人挣扎着离开了故地,另一些人则永远被抛弃在故土的千里之外。
2011年的《我11》几乎可以看作是王小帅的半自传,电影中的许多人和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电影以孩子的视角切入历史,展开了一段既温馨又残酷的回忆:一代人的成长里隐藏着巨大的暴力。在对这种回忆反刍的过程中,历史的荒诞性昭然若揭。
四年后的《闯入者》是“三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独居老人在北京过着安静的生活,但看上去岁月静好的中产家庭内部原来隐藏着一个来自贵州腹地的秘密,随着一位闯入者的到来,她不得不面对来自历史的拷问。这部电影充满了强烈的象征性,“闯入者”提示观众历史债务总要偿还,只是时间或早或晚。
“整个中国的变化过程,新一代的2000后是不理解的。他们降生在上海、北京、深圳这种建设完成的城市。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出门就是汽车,进了房间就是空调,电脑马上可以勾连世界。给他们这代人建立故乡的概念,探索什么来龙去脉,人家是不理解的。”
拍完《青红》,王小帅才发现很多人是通过这部电影才知道“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这让他的使命感又增加了几分。面对历史,电影不仅仅是戏剧冲突的演练场,也成为物质现实最好的传承手段。重视个人经验是王小帅创作中很重要的部分。就像他所说的,当故乡不可避免的同质化之后,保存记忆就是保存故乡。
13岁那年,王小帅一家得以迁居到武汉,15岁他考上了央美附中去了北京,继而进入电影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被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在福建厂的日子,作为年轻导演基本无片可拍,王小帅不甘心就这么混沌度日,他自筹资金,拍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独立电影《冬春的日子》。
这部电影的意义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那样,这是第一次,一个年轻导演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按照自己的思考说出来,不像以前那样被人左右。本来只是想要表达个人对时代的看法,却无意成为了体制的“叛逆者”,一度被打上“地下”导演的标签。这些经历让王小帅非常清晰地感受到社会变动中个人的被动性,也让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反思和批判性。
“在被动的变动和迁徙中,人和整个社会机器的结合与互动体现出的弱小,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深刻体会的。面对社会机器的巨大冰冷,关注人在社会中的生存挣扎,将人处在机关和机构下的恐惧尽可能的削弱,给予人温暖、自由和安全感,这是一个良性美好的社会的终极理想。”
逃离因此成为了王小帅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叙事线索,如他所说,这是一种内化的潜意识。因为历史暴力介入个人的生活,他电影的主人公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地厌恶此地,而向往远方的倾向。对此,王小帅的解释是,人不能自由地选择“此地”,处在一种缺乏认同感的夹缝里,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这类人的处境。
“三线三部曲”之外,《扁担姑娘》《十七岁的单车》《地久天长》莫不是如此。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真相:在大时代里,鲜少有人是幸存者,但正是如此,微末的反抗都是值得书写的。我们不难在这些创作中看到时代无名人的清晰的画像,三线建设也好,计划生育政策也好,亦或是打工潮也好,在王小帅的电影里,这些名词不再是一个个冰冷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灵魂。
某种程度上,这些不被时代接纳的人就是王小帅的无数个“分身”,他始终关心那些被时代抛下的人,在变动中的“局外人”,他个人的命运和电影人物的命运因此巧妙地发生着共振。
身份的焦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伴随着王小帅,在北京生活多年,王小帅依然觉得自己是贵州人,那是他身体可以感受到的故乡,父母一辈的经历已经无从追溯,而当下的自己只是生活在北京,并不属于这里。
回想起15岁来北京读书,颇有些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时代除了几个大城市,资源分配严重不平均,能来到北京似乎就是奇迹。依稀记得少年时代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对北京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敬畏。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会询问本地同学是不是见过毛主席,仿佛那是属于北京人的特权。他们自小住在皇城根下,说着需要外地人模仿的儿化音,但这些都与自己无关。
渐渐地,身边一些朋友努力弄到了北京户口,慢慢地在这个城市扎下来,后代也成为了所谓的北京人。但王小帅却依然选择做一个局外人。何况,这座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现代化,变得和其他城市没有两样,这是让人伤心的。
“现在的北京不如从前可爱了,虽然它的外表很光鲜了,但是内核的热情、文化的底蕴和包容性、创造性在慢慢消失,当然可能因为年纪的原因,有些东西我看不到,也许现在依然如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呈现:年轻人依然在创作着,活跃着,享受着,但这可能不一样,时代的变化是不容置疑的。”
他依稀怀念上个世纪的北京,见证自己青春的八十年代。那时候,北京聚集了最有力量的一群人,是真正的文化中心,人们对文化艺术具有强烈的渴望,充满了活力,玩摇滚,拍电影,创作文学……甚至连纽约都不看在眼里。如今这种气象没有了,商业蓬勃发展,而文化艺术要如何发展,却似乎不在讨论中了。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当下的电影创作保持这样一份真诚,在变动中把握时代的脉络,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是十分巨大的考验。在这样一个浮躁的行业里,太多人想要跟风。王小帅却觉得,真正搞创作的,还是应该把自己的理念和思考放进作品,要大胆地审视自己,把自己的心思和焦虑拿出来。
有人说,第六代导演的一个特点就是个人化,抛开宏大的叙事,关注具体的人。王小帅的电影大多与个人经验有关,但恰恰是这种十分私人的记忆,让历史拥有了具体可感的肉身,让我们得以去理解一代人的命运。进入到知天命的年龄,王小帅反而更有意愿去回溯历史,脱离开年轻时候的本能冲动,现在的眼界和知识结构更有助于一位导演处理历史题材。
另一方面,个人的主体性是微弱的,总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吞噬,但人毕竟不能没有尊严的活着,总是要奋力挣扎,和不公对抗,因此也会迸发出更有力量的艺术表达,这种张力让王小帅的电影拥有了独树一帜的品相。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20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