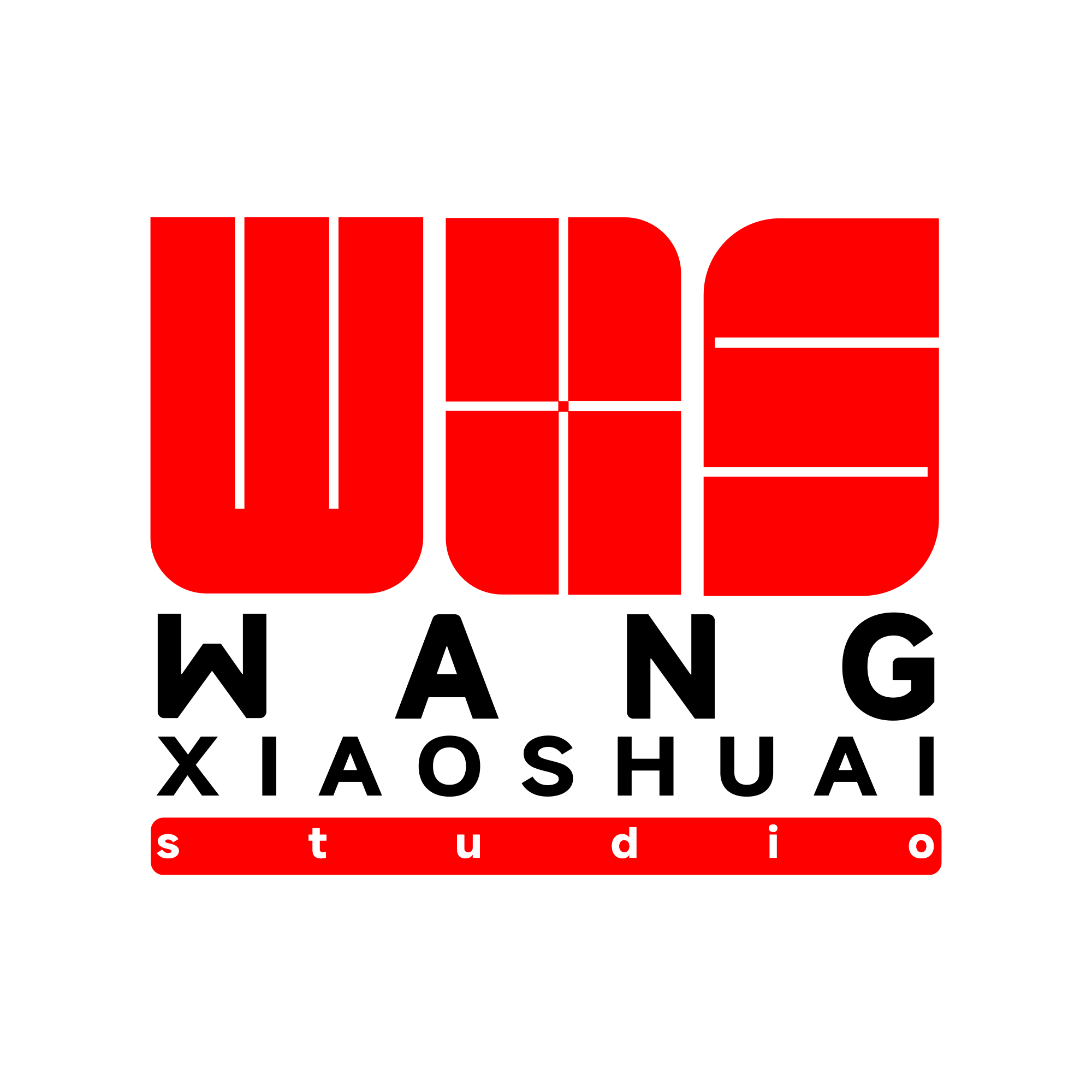阳台前二十米左右,是几棵郁郁葱葱的大树,密密的树丛间,有一个不小的空档,枝叶稀疏了许多,透过它正好可以看到夕阳下闪着波光的东湖。常常在下午的四点多钟,你会看到有几只赛艇划过水面,整齐的桨一排排齐刷刷地起落,桨的一头齐齐地插入湖水,上面的人把桨往怀里再一拉,这只小艇就迅速划过这道树丛间的空档。因为距离遥远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无声无息的。
七十年代末期和八十年代初期,我经常站在父亲文工团分的房子的大阳台上,看着这个景象。它是真真实实的,却又象极了一个幻影。这就是武汉吗?一个大到直到我离开它都没有认识清楚的城市。你来到这里,你知道你是一个外乡客,所以你希望讨好它,让它知道你的到来,让它接受你。可是有时候它就象眼前这个景色,它存在在那里,无所谓你的讨好,自顾自地张显它大城市的庄严和淡定。我知道,无论我怎样想要否定这个现实,已经无能为力了,贵阳已经不存在了,现在你要面对的是新的生活。象一台电脑,需要重新格式化,把贵阳的一切格掉,然后开始用我这块全新的硬盘,往里面一点一点地加入新的内容。
跟母亲和妹妹下火车站站在接站大厅里是1979年的春节之前,中越开战前夕。生活里永远稀里糊涂的父亲那次继续发挥,他竟然忘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女儿这一天要从千里之外的贵阳来到武汉。人都差不多走光了,我们还没见到父亲的身影。我开始痛恨这一切,痛恨父母把我从贵阳带走,这个事情违背了我的意志,我不愿意离开我生活了13年的地盘,我要求回去。武汉的车站让我联想起了当年右臂戴着白毛巾去北京时北京的火车站,一样第一时间没有见到亲人,一样是冷漠而高大。整个一列车的人快走得差不多了,还没见到父亲的身影, 正在我无比沮丧的时候,边上有两个扫地的妇女在那里说话,第一个印象是他们说话声音很大,两个人的距离只要正常开口,应该对方就能听见,而他们就像隔着一条马路在喊叫。我听了很长时间,突然意识到她们说的话我都能听懂。原本我以为地方和地方之间的语言差别会大到如同上海话和贵阳话,互相之间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我跟母亲说他们怎么在说贵阳话?母亲听了会儿,说是像,但是他们说的是武汉话,两种话里确实又许多接近的地方。母亲说我在四岁之前,就是在寨子里和少伯少妈生活的时候,我说的就是一口贵阳话,上海话和普通话是后来回到家里之后才开始说的。通常在外面和孩子们玩,我们就用上海话交流,回到家里和父亲就用普通话,父亲虽说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的也是表演,后来又留校任教八年,算了一算父亲应该在上海至少生活了十二年,但他只能听懂上海话,说却是不行的。因此,如果从最源头上说,我使用过的第一种方言应该是贵阳话,虽然很快就不说了,但语言的记忆已经在那里了。而湖北武汉话从基本的发音和声调上和贵阳话极其相似,这就说明为什么,我在听那两个扫地的妇女在那儿叫喊的时候,我对她们所使用的语言完全没有陌生感的原因。
这一发现让我的心莫名地安静下来,最初对于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恐惧和排斥有了一些缓和。回想我一年前第一次来武汉看父亲,之所以没有这次的焦虑感,可能是因为那次我知道那只是一次短暂的逗留,就象旅游,很快就会回去。后来母亲给团里打了电话,父亲才猛然想起我们。一辆212吉普被派来接我们,是一个年青的司机,穿着军装的解放军。父亲依旧没有出现,听说他正忙于排戏。
我即将开始新的生活的地方叫南望山。按照这个各字推理,人们生活的区域应该是坐北朝南,但也可能正好相反,人们站在北边往这边看到有一座山,所以叫它南望山。反正我是很失望的,原以为全家搬到了武汉,而父母都曾很兴奋地表露武汉可是一个大城市,我们终于逃出了那个山沟沟了,而我也可以把自己算做大城市的人了。可是这个南望山,却是在远离市中心的郊区,三面被著名的东湖环绕。公共汽车一直要开出市区边缘最后的几幢房子,然后继续往前开出七八站,你就会下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小站,公路继续往前延伸,车站的后面就是农田,农田的尽头可以隐约看见闪着波光的东湖一角。然后就要开始沿着更小的一条小路向东湖走去,穿过一个把东湖这一小角分成两块的湖堤,湖堤上是两排笔直水杉树,堤上面可以开车,宽度刚好可以对错两辆小汽车,但是市政的公共汽车已经不往里面开了。穿过湖堤就进入了南望山腹地,然后要继续沿着山脚的沙石路行走,拐过山角的第一道弯,右首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掩映在树丛中的第一幢房子,是那种老式苏式的大房子,有两三幢这样的房子,这两三幢房子组成的是武汉军区胜利文工团的歌舞团,走过歌舞团,继续沿着沙石路行走,这时路已经是呈上坡的角度了,这条路后来我出去画画写生骑着父亲那辆老式德国倒刹式的自行车行走过无数次,特别是到了这一段上坡路,下来推行是很痛苦的,因为坡虽然不陡,但是很长,所以我总是努力地骑上去。这段路右手边是山,左手边是农田,农田的外面就是东湖,原本应该是一条风景优美的乡间小路,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靠近湖的一边被砌了一堵红砖墙,比一个成年男人还要高出一头,一直延伸到山顶,能看见东湖的视线就这样被堵住了。也是因为这堵墙,在山和田野之间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那堵墙就象一道回音板,每次我喘着粗气往上骑行,我的喘气声和车轮碾压着地上碎石子的声音就像被什么东西挡住了,像是回声一样地回荡在我和墙之间。碎石路上行一会就会看见第二批类似的建筑,那是属于京剧团的。然后再继续,坡会突然陡起来,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没有人能继续骑行上去了。最后一段必须推行,这段坡不长,大约就是百米左右,但却异常的陡,平时要是从家里骑车出来,母亲总会加一句:下坡的时候小心点。从陡坡开始的地方往坡顶看去,就能隐约看见一大丛一大丛树木的后面出现了一些房子,那就是我们的话剧团了。我在开篇说的那个阳台以及透过树丛看到的东湖,就在你推着自行车往上看到的第一幢建筑上,我的新家。整个建筑群他们叫它“工字”楼,说从天空上看这几幢楼正好连接形成一个“工”字形。每幢楼只有两层楼高,但每层的层高都比普通的居民楼要高。
我在文工团最鼎盛的时期来到这里,每天都用好奇地眼睛看着一个个意气风发的演员们咿咿呀呀地吊着嗓子在排练厅、饭厅,宿舍间进进出出,满眼的绿军装让人羡慕不已。这一切和在贵阳的生活如此的不同,虽然在贵阳时我也曾到宇宙的中心-父亲的京剧团看过,一是因为太小,二是每次都是周末,这样热闹的景象还是没有印象的。
我们一家在南望山一直生活到整个文工团被解散,最后只剩少数不多的几家人家,包括我们家。去北京上学以后,每次放假回来,都看着它一次比一次凋零,最后我们也要搬走了。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家,新的朋友,你正在逐渐的熟悉它,喜欢它,接受它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你又要离开了,巨大的感伤再次包围了我,以至我直到现在还无法肯定,究竟是一个要走的人和一个只能留下来的人之间,谁的伤感程度会大一点。
记得有一次回来,昔日热闹的走廊里空空荡荡,一个演员叔叔蹲在自家窗边的土地上,用一根树枝在沙土上划来划去,抹平,再划,四周寂静,他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听别人说,他的老婆受不了了,在他出差回来之前,卷了铺盖,跑了。当时我也蹲在他边上,不知道是希望他的存在能带给我一点安慰,还是我能给他一点安慰。
没有搬走的几个邻居里还有王兵一家,幸好有他们,使得萧条落寞的日子之外保持了仅有的一点生活气息。
王兵比我大一岁,这就已经算是同龄人了。一来南望山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们家也不是武汉人,可是他从小就生活在文工团,除了上学在外面,其余时间都在这个小圈子里,如同我在贵阳时的情景。那时他竟然一句武汉话都不会说,张口就是不伦不类的武汉普通话。他喜欢打架,这在那个时期是一种普遍的时髦行为,并且自以为是这方面的高手。每次都跟我仔细描述在外面参加群殴的细节,他说他不带刀,见人上来顺手抓起什么就是什么,他说这样万一不行了别个也不会把他弄死。严重的时候,有人就在南望山下面堵他,他上学必须出南望山,走过那条湖边的堤坝,他说这条路经常是九死一生。你打架怎么样?他问我。我说我在贵阳的学校里,单打无对手。父亲教会我几招,其中一招是等对方上来,用左手在他眼前虚晃一下,在对方下意识躲闪的瞬间直接出右拳直击对方的脸,要快,狠,就一下便可解决问题。具体目标选两个,一个是对方的眼睛,一个是鼻子,我认为眼睛太过残酷,鼻子好点。后来的几次实战中这一招被我运用的最好,至少三个不服的被我一击暴鼻。并且我还练过打沙袋,很专业的那种。
王兵说好,但表示这样具体的打法在对方人多的时候就不适用,人多就是乱打,然后跑,跑狠重要,你跑得怎么样?我们试了一下,六十米的距离我把他拉下足有十米,他比我高半个头。他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因为在整个南望山话剧团里,同龄的男孩就只有我和他。有几次他让我陪他下山,穿过堤坝,他会说我感觉今天会有人堵我。我只硬着头皮答应过两次,只有一次碰到过人。
为了面子,那次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和他下山,然后和他穿过堤坝才分手,其实我去学校的路是可以直接从山上走过去的。我们下到山底,开始走上堤坝,我们穿着父亲的军装,戴着军帽,王兵把军书包抡在背上,手在前面拎着书包带。我看过去,长长的堤坝上没有人影,两边的水杉被湖风吹着,祥和而宁静,虽然如此,我依然感到堤坝长无尽头,并且这宁静显得异常诡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面出现了几个人影,大约四五个人影,我说有人了,他说可能不是,我们就装做没事一样就行。
他突然转身朝来路狂奔而去是我们和那几个人走到了大约二十来米的时候,“我操,这个逼”留下一句汉普。我停住,一时不知该跑还是不动,我选择了不动,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始料未及的,以前每次他都说自己会抡着书包杀出重围,后来他解释说其实在堤坝上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只是担心他们会在这儿堵他,因为这里路太窄,抡不开,只能不吃眼前亏。我没有怪他,因为至少真的有人堵他,说明我一直怀疑他在吹牛可以不成立了。向他追去的人经过停在那里的我没有停下来,我继续向前走已经毫无意义,站在这里也不是事儿,我回身返回。后来我们分析说我站住不动是对的,毕竟我是刚来的人,和他们毫无过节,也没有人见过我。
“一看你就是新来的”王兵说。
记得我是在中央美院附中快毕业的时候听说他被劳教了。
再有一年我放假回来,正是团里的萧条期,他说他参加工作了,在武昌洪山区的城管大队里干。城管和这个新兴的职业名字我就是从他口里第一次听到的。他把我领到他的管辖范围,指着街上的小摊贩说,你要什么,我们过去就拿。他走到一个烟摊前,直接拿了两包烟。
“别给我惹麻烦啊”
“没得问题”小贩说。
王兵说我不可能象你了,搞艺术,我就这样了。
“我们一个监室的哥们出来现在都在城管里干”他说。
快三十年后,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王兵突然联系到我,用微信发来文工团子弟聚会的照片,我问他还在城管吗?他说是,都快退休了,什么时候你回来看看啊。
依稀记得他也跟我一起学过画画,后来还考进了湖北省艺术学校的美术专业,可是进了艺校的他怎么后来又成了进了劳教所的他这两件事情我始终没有对上号,可是在城管里干得如鱼得水并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应该是和他从小喜欢打架分不开的吧。
其实刚刚来到文工团的那个冬天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叫青海,比我们大几岁,他不是文工团的,是王兵当地的一个朋友。我们一共只有两次接触,第一次是王兵把他叫到团里来给我做了介绍,说他叫青海,但跟那个青海省无关,说这哥们疯了,报名当兵了,马上就要去打越南了。我是知道要打越南的,因为我自以为贵州还比武汉算前线,我们小孩都在山上挖过防空洞呢,厂里还天天拉防空警报呢。但是你们贵阳有军区吗?我们这里有武汉军区,王兵说。青海不怎么说话,王兵担心以后在外面打架没人手了。
对那次只有一个月的战争我在记忆上产生了偏差,因为我觉得那次仗打了很久,打到青海都战死了。
只记得那次之后青海就上了前线,而且感觉过了很长时间,突然有一天王兵说青海回来了。我们在我家里见面。我们迫不及待地听他描述打仗的事情,青海的讲诉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连队第一次上去就是伏击一个越军的车队,车队进入伏击圈以后,他们就开火了。青海说根本不象电影里那样,他们的火力向山下打去的时候,整个山谷里硝烟尘上,他一枪未发,爬在那里看,可是除了烟尘他什么也看不见,他说在他边上的是一个机枪手,是他刚入队就结识的一个好朋友,这时机枪突然不响了,他一看,那个战友歪在一边,半个头都没了,他说他的火一下就起来了,他的描述是他跳了起来,整个人站在战壕上,端起战友的机枪就向山下扫射,尽管下面什么都看不见。他是被连长一脚踹下来的,连长后来跟他说,机枪里根本没子弹了,只有他自己抱着枪还在狂叫。就这一下,他被连长看中了,这次他回来是让他来训练侦察兵,然后还得上去。
对于青海的这段记忆我始终理不清头绪,首先是他怎么突然参军,然后又马上上了前线,难道我军没人了吗?要一个未经训练的大头兵冲上去,这不符合逻辑啊。其二是,就他这个表现,虽说算勇敢,但至于马上让他回来训练新兵吗?小小一个连长有这权利吗?其三是时间,查资料确认正式开打到停火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记忆中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起伏?或者是他第二次带侦察兵上去到牺牲是停火以后的事情了?但无论怎样,那天他是实实在在坐在我床头说的这些的。那天晚上狂风大作,不知为何父母和妹妹都不在家,停电了,我和王兵坐在床边地上,他坐在床上,身后窗外的微光把他衬托成了一个黑糊糊的剪影,气氛诡异恐怖,炸雷和暴雨就在那一刻突然而至,闪电聚集的白光穿透黑夜刺进昏暗的房间,我和王兵大呼小叫,青海却始终一动不动。后来我们说起来,他的架势确实有一种经历过大阵仗以后的淡定,且多了一份威严。
那天过后不久,就传来青海的死讯,王兵说他带了一队侦察兵在前线侦察,那时已经没有大规模战斗了,一颗不知从何而来的流弹击中了青海的头部。王兵用汉普说个把麻倒霉,仗都快打完了,要是他不死,回来升个连长应该不成问题。
团里还热闹的时候,我们家每周末都会搞一次大吃大喝大聚会。团里有几个年轻人,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的大学生,上海人。他们中赵葆康、李辉等,成了我日后学习绘画的真正的启蒙老师。父亲为了能请他们教我学画,每周末就会去集市买鸡买肉,然后招呼他们来家里聚会。大家又吃又喝,天南海北地聊天,戏剧,艺术,音乐,历史,即使我感到再无聊,父亲都命令我坐在一边不许离开,他管这叫熏陶。吃喝结束,大家就来到对面楼里的电视房,平时那是一个供大家看电视的空房间,有一个琐在木箱里的电视,一些散落的板凳,这时候就正好被我们用上,大家就会各自摆好画架,父亲也会给我摆一个,然后就开始画,静物、人物、色彩、素描,周末的时光大部分就是这样度过着。有时候父亲不让我画,只在边上看他们画,父亲说,这也叫熏陶,他们画你看,你画,他们给你指导,这样的氛围,这样的机会,“在贵阳到哪儿找去?”
除了绘画,最吸引我的是赵葆康和李辉夫妇家的一台双卡录音机。很多的下午,不自觉地就会走到楼对面他们家去。李辉喜欢哲学,康德,尼采,柏拉图,她会不厌其烦地把她在书上用红笔画了线的部分念给我听,赵葆康就笑她,说我都听得稀里糊涂,他怎么可能听得懂,她说没关系,这也是熏陶。她特别推崇柏拉图,她说她和赵葆康除了肉体上的夫妻以外,最重要的是他们精神上的爱。赵葆康喜欢听古典音乐,音乐从那台大大的双卡录音机里流淌出来,弥漫在他们的小屋里,你推门进去,他会对你笑笑,并不说话。听完一段,他会来一句: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或者贝多芬的悲怆。他的烟一根接一根,冬日的下午,阳光从他身后的窗子外照进来,蓝色的烟雾缓缓地笼罩着他。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听到德沃夏克的至新大陆时,他会冲你灿烂地一笑,“嗲伐?”用上海话来一句,然后就会说到出国,他说他们的理想就是能出国,他们不能就这样永远在这里窝着。当时我不能理解,武汉这样的大城市,怎么还能算窝着?李辉想去美国,而他想去法国,去卢浮宫,奥塞美术馆看油画原作,他说一个画画的,连那些大师的原作都没看到过真是笑话。
那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不久后的萧条期,他们双双调回上海。几年以后,在他们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李辉去了澳洲,赵保康的法国梦没有实现,留在了上海,一边在美术学校教书一边带女儿,从此天各一方。李辉有十几年没有回国,直到女儿十几岁才回来把女儿接过去,赵保康也不再坚持法国梦,办了澳洲移民,一家人重新团聚。这期间,每次我到上海,看见独自一人带着女儿的赵保康,总是会想到李辉推崇的柏拉图。
自己出去写生的日子是非常愉快的。骑着父亲又笨又重的德式自行车从山顶一冲而下,可以沿着东湖转。一个少年,可能心里已经自以为是个青年,一个人享受着无人的东湖。武汉大学离南望山不算远,那里依山而建的欧式建筑、三月校园里盛开的樱花始终吸引着我。后来老师说要保送我进武汉大学英语系,为了那些美极的建筑和樱花,我还真正地动心了很长时间。
最远我骑到过长江边上。父亲鼓励说要画就去画码头,画那些挑担的扁担,画那些码头上的船工。这样的单程旅行应该花去二小时左右,而且还是一个少年飞快地骑,肆意挥霍体力的结果。那时是第一次一个人体验着武汉这个大城市,喧闹的码头、汽轮、大声喊叫的人们,夏天里沿街横七竖八光着膀子躺在街边凉椅上的男男女女,横冲直撞的汽车。关于街边横七竖八光着膀子躺在凉椅上的男男女女,我在“扁担姑娘”筹备的时候是我一直想要的一副画面,可惜因为当时不允许我拍片,为了解禁的问题耽误了很长时间,等我们可以拍了,夏天早已过去。
就这样,日复一日,在一个被重新格式后的少年心里,重新输入着新的内容,大城市的内容。
母亲一开始没有工作,只能四处托人,很快就联系上了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在改叫华中理工大学,工人阶级出生,从来没有当过老师的母亲最终进入了华中工学院,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对于这个结果,我猜测可能是母亲在贵阳时,子弟学校要开设高中部,苦于没有老师就把母亲临时拉过去充数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母亲的原因,我也得以进入华中工学院附中继续初中学习。
入学的第一天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虽然说在贵阳生活了十三年,但工厂的那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里的人始终是把自己称作上海人的,并且有互相之间上海方言为证,这在我们孩子心里也一直是形成了这么一种认知的,即我们和贵阳没关系,我们是上海人,上海是什么地方?上海有的确良,有大白兔奶糖,有大冰砖,有永久牌自行车。所以其实当我被告知武汉是个大城市,心里是不屑一顾的。我们上海才是大城市,虽然从来没有去过上海这个事实会让这种底气变得虚弱一些,但上海和我的关系总是天然相连的。所以武汉算什么?为了证明这一说法,父亲专门把他的一件还算像样的中山装给我穿上。深灰偏蓝色的咔叽布,有点大,套在一个十三岁的少年身上,正式得有点不伦不类,但至少希望做到不要让人看不起我们从贵阳来的人,我们也是很洋气的。
这里的每间教室是我们贵阳小学的两倍大,一个班的人有三倍多,把教室挤得满满的。已经没有我的位子了,只能把我安排在一进门门边的一个加坐上,基本只能70度角看黑板。当我穿着那件于我的年龄相比显得过于老成的中山装得意地以上海人的心理状态坐在这个加座上的时候,整个我身后的班里响起了一片“嗡嗡”声,其中有一句清晰的声音刺入了我的耳朵“乡里娃”。这三个字一瞬间击中了我,它无比明确地界定了现在,在武汉这个大城市,在他们眼里,我不仅仅是个外来人,而且是个乡下来的人,没有人会对你的“上海”血统感兴趣。就是在那一刻,我的心理防线垮塌了。我承认他们是对的,我来自于贵阳,来自于乡下,我接受,我是个外来的乡下人,我不属于这里,或者说这里不属于我。这种认知一直贯穿了很久,无论后来到了北京,又去福建,再回北京流浪,外乡人是一直跟随我的一道心理印迹。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用一种外乡人的视角去观察我所处的这个城市,这个社会,甚至包括这个时代,有时候,我觉得我都是这个时代的局外人。
华中理工大学所处的位置比南望山还要僻远。除了那条通公共汽车的大路,还有一条从山上穿过的小路,可以缩短不少从南望山到学校的距离。在母亲从学校分到一套宿舍之前,我每天就从这条山路穿过,去到学校,或者从学校回家,那条路会穿过几个小小的村落,那里有养鱼池塘,农家的院落,有无数的野狗和农人家养的鸡鸭。除了心里的不甘,但我知道,我还是在农村,在山和水之间。
但华中理工大学一个学校,就已经远远地大过了我曾生活过的贵阳的工厂,无数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连接着数不清的各种苏式教学楼、宿舍。每条马路两边都种满了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斑驳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树枝洒在大地上,那是一个新奇而庄严的世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保证不至于在里面迷路。很快,我那颗“乡里娃”的小小心脏彻底被它征服了。本来在贵阳,我在我们整个学校学习成绩都是最上流的,可在这里,仅仅一个班,我就是垫底的。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心里暗暗感激我的父亲,因为他的强压,我手里有了一个别的同学所没有的手艺,我要把这手艺放大,以此来逃避普通文化课的落后。自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背上画夹,骑上自行车,以画画的名义逃避现实,逃进我的天地。
还有就是英语,不知是从几年级开始,我们贵阳的子弟小学居然开设了英语课,在老师一张口说出的单词引来全班人的哄笑中,我却发现那里面的神妙之光,难道“万岁”还有那样的念法,难道“square”就代表了“广场”?这些奇妙的发音立即吸引了我,更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觉得这一切遥不可及,相反,它们和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好像似曾相识。于是,我对于英语学习的自觉性甚至更早于绘画。那时家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是父亲专门用来偷听“美国之音”的。那时收听“美国之音”属于收听敌台,是不被允许的,所以父亲经常在“美国之音”对华人广播的特定时间,人整个趴在收音机上,用极小的音量收听着那来自遥远地方的声音。信号时常被干扰,但父亲不顾这些,饥渴地捕捉着那些时常冒出来的汉字,这些汉字的组成和传达的意思和平时听到的是那么的不一样,这一切都造成了强大而诡异的气场,有一丝恐怖,又有一丝激动。记忆中在全厂,甚至全国人民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关上收音机,颤抖地跟母亲说“周恩来去世了”,在随着袭来的奇异的沉默中,恐怖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四口之家。
就是这台收音机,就是这个“美国之音”,每天到晚间9点左右有一档英语九百句的教学课程,随后是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小说英语连载。在每天晚上父母和妹妹都睡觉之后,我就会悄悄地打开收音机,像父亲一样趴在收音机上,音量调到正好自己能听见又不会打扰他们睡觉的高度,沉浸在英语九百句和汤姆索亚的世界里。这一切现在想来是如此的不真实,在74、75或76年的中国,在偏远到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山沟里,一个少年,在夜深人静的时刻,耳朵贴着红灯牌收音机,屁股翘的老高,极力地捕捉着每一个穿过干扰而来的遥远的异国之音。因为这一段奇特的经历,也让我在后来的学校多了一份不错的技艺,在我的数学、物理、化学已经差到无以为继的时候,英语成了我的另一根救命稻草。
在武汉的时光就这样静静地流淌着。新的记忆卡继续存储着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环绕着美丽的东湖,少年慢慢地变成一个青年。终于在15岁那年,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准考证。这一张准考证,意味着我可以堂而皇之地从普通的文化课上逃之夭夭了。在准备赴京赶考的前夕,我的英语老师找到我,她害怕我考上,她说如果我考上了,也请我好好想一想,因为就我现在这样的状况,再过二年,她可以保送我进武汉大学英语系学习。我记得我们是站在一颗巨大的法国梧桐下做这一番对话的。当时的我心里早就飞向了那个远在北方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心脏,是小时候无比向往的毛主席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新的宇宙中心,特别是那个学校,以中央开头,而中央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
我答应老师,我会认真考虑她的嘱咐。最后我说,我应该是考不上的,她说那她就放心了。
但是暗中,我加紧了步伐。在南望山的家里,绘画聚会多了针对性,赵葆康、李辉、汤志良们(汤志良是父亲的密友,演员,也习绘画)似乎突然神秘起来,那个遥远的美院附中好像也给他们上了一个考题,过去泛泛的赞美突然变得不容易出口了。在他们眼里,这个孩子已经不再是涂鸦少年,准考证的神圣性让他们变得谨慎起来。每一句话,每一个指点开始透露出一份审慎的专业性。很多年以后,在上海重新又见到赵葆康和汤志良,他们已经随着文工团的解散各自回到了上海,我们在路边的小餐馆里喝着黄酒,我也已经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他们说,说实在的,当时在那个时候,那个条件下,他们自己也完全没有信心我可以考取那个学校。赵葆康说那是什么学校?中央打头,全国招生,而且只招13个人,想想都可怕。后来你还要上电影学院,这个想想更可怕。那天我们至少喝了六瓶黄酒,而且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当年我叫他们叔叔,其实他们也才二十多岁。
“不好叫了,不好叫了,现在已经不好叫叔叔了。”
另人奇怪的是,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个夏天在我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记得那个注定重要的时刻是怎么到来的,或者是赵葆康夫妇正在上海探亲?汤志良已经参加了野战军?可以确定的是那时侯父亲正好被上海借调过去演出话剧“陈嘉庚”,所以那封通知书就这么平平淡淡地来了,除了母亲和妹妹,没有人在身边,没有特殊的庆祝和欢呼。和同学们也是,原来预备好的激动也被悄悄地压抑回去了,因为在大部分人眼里,这和我当时转学来现在又要转学走一样,没什么区别。
1981年的那个秋天,借着去北京报到,我做了人生中第一次独自旅行。顺江而下,从武汉坐船前往那个传说中我的出生地,上海。
在向排练的父亲炫耀完那张录取通知书之后,父亲就把我推给了我从未见过的汤志良的弟弟,他带着游玩了这个从小的梦中之城,吃遍了传说中的大白兔奶糖、大冰砖、城隍庙鲜肉月饼、小汤包⋯不知何故,当这一切实实在在来到面前的时候,当我自认为真实地踏在上海的地界上之后,那份自以为会出现的激动却并未降临,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这个我出生的城市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产生任何改变,它以及生活在它脚下的人们自顾自忙碌着,我熟悉的呢哝牙语飘散在各个角落,可是没有一个字是飘到我头上的。我在一个个景点中留影,尽量掩饰一个外地人窘迫的摸样。就像当时刚刚到武汉时,一个来自贵阳的大上海人的心理重新涌现了出来,上海算什么?我是武汉人,武汉也是大城市,有长江,有长江大桥,武汉三镇加起来比上海还大,武汉是中国的中心,有九省通衢之美誉,我曾经骑着车,自由地穿过它的大街小巷。虽然在那个时候,我的骄傲恰恰并非因为我来自贵州,而正是来自于脚下这片陌生的出生之地。而现在,当我真正来到我的骄傲之地,却突然发现在这个冰冷的大城市里没有找到丝毫关于故乡的温暖,更没有找到这个城市可能和自己有关的任何证据。它庞大地存在着,完全没有理会一个少年心里对它的纠结。
多年的幻觉破灭了。记得那一刻,快要离开的那天早上,在父亲的房间里收拾好行李,突然有一刻不记得自己是要去哪里,有一种心被挖空的感觉,似乎这一走,什么都会没有了。贵阳没有了,武汉没有了,上海也终将没有了。
父亲没有去送我,他站在门里,让我自己走出门,就像每一次的抵达和离开一样。汤志良的弟弟在门口接上我,他对父亲不去送我很吃惊。我跟着这个陌生人,一路由他把我送到车站。
我独自踏上火车,离开这座在心里找了很久但始终没有答案且显得莫名其妙的城市,经常州暂停,看望了从未见过的大伯,父亲的哥哥,然后由常州北上,扑向另一个陌生。那一年,我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