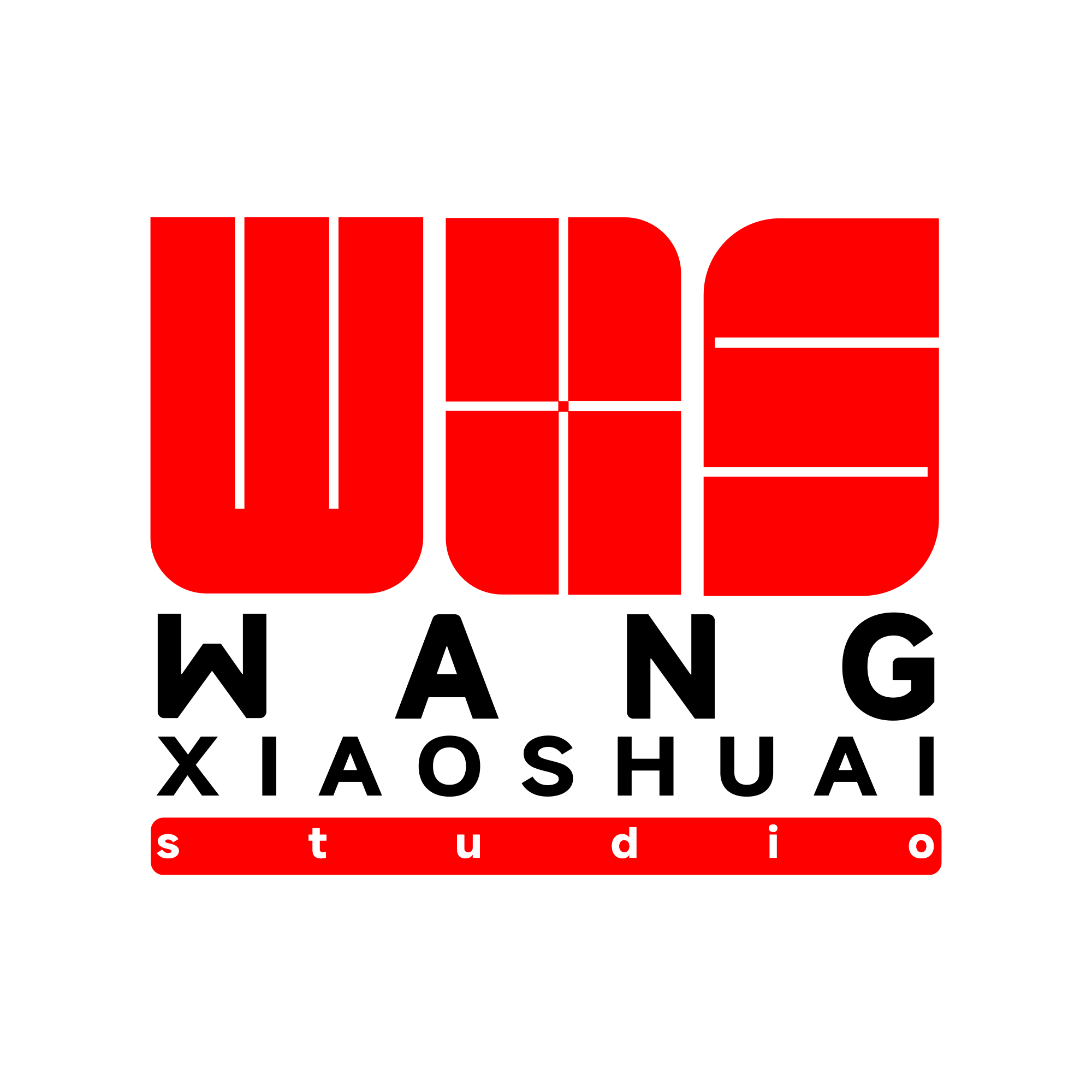戛纳电影节于5月如期迎来它的第68载盛宴。
从二十余年前陈凯歌、葛优等先后在戛纳夺下大奖,至后来第六代导演先后亮相,近几年,戛纳电影节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人、艺人、甚至名媛们最乐于展现自己的舞台。戛纳的中国电影人生态圈由此也渐渐形成、壮大。
那些在戛纳风生水起的人,他们是谁?他们为何获得戛纳的青睐?中国电影人与戛纳之间存在着怎样微妙的关系?进入戛纳生态圈的条件又是什么?
此番我们拔筋抽骨,试图在纷纭热闹的戛纳电影节生态圈里总结生活和生存的规则,为中国电影的进阶和发展找到一条正确清醒的路径,也让带着梦想或野心前往戛纳的人们看清局面,玩儿得开心。
戛纳电影节上的中国人,他们是谁?
《嘉人》精挑细选了以下五位受访者,他们和戛纳电影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离那片沙滩最近的人,他们以艺术家的身份见证了戛纳作为艺术殿堂最令人敬畏的一面,也深入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风浪里搏杀过好几个回合。
他们告诉我们,戛纳电影节是什么,中国电影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在那里汇聚,他们的牵连与互惠,牢固坚硬而彼此不可或缺。
黄璐: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曾与多位中国“第六代”导演合作。代表作《盲山》、《中国姑娘》、《推拿》、《这里,那里》、《红色康拜因》、《对面的女孩杀过来》等。2007年《盲山》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那一年她22岁,首次作为演员代表参加戛纳电影节。
耐安:著名电影制片人、演员。她作为独立制片人制作的电影《周末情人》于1993年获得曼海姆海德堡国际电影节导演奖。而后作为导演娄烨的制片人,完成了作品《苏州河》、《紫蝴蝶》、《春风沉醉的晚上》、《浮城谜事》。曾四次作为入围作品的制片人参与戛纳电影节。
isabelle Glachant(伊莎):独立制片人,Unifrance电影公司大中华区首席代表,长期致力于中法文化交流。独立制片作品《青红》,《日照重庆》联合制片人。与导演王小帅、李玉、陆川等都有过密切合作。
Benjamin Illos(本杰明):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Director’s Fortnight)选片人。
王小帅: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1999年执导第一部体制内电影《扁担姑娘》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注目”单元。2005年执导的影片《青红》获得评委会戛纳电影节大奖。2010年影片《日照重庆》再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他们在戛纳电影节,做什么?
戛纳是顶级艺术大师汇聚的殿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买卖交易市场。5月的初夏,全世界最厉害的导演、演员、制片人们都将在这里现身,觥筹交错,往来无白丁。
演员:首映那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个公主
2007年,李扬执导的电影《盲山》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女主角黄璐那年还是一个大四学生,5月初收到正式通知将受邀参加戛纳时,她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答辩,身边的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反应都不太激烈,毕竟,戛纳电影节离他们显然有点太遥远了,“仿佛还不如某一个偶像剧女主角来得更让人激动”。
时间已经有点紧张了,黄璐打电话给之前在一个剧组中结识的服装设计师Laurence Xu,请他帮忙赶制出一套礼服来,对方欣然答应,当天晚上就赶到黄璐家里来量尺寸,商量设计方案。最终缝制了一套水白色的小礼服,上面有手工刺绣的梨花和小鸟图案,前摆短后摆长,黄璐年轻而不失优雅的气质被衬托得恰到好处。“那时候我们都没有经验,以为有一套礼服就够了,根本没有找品牌赞助的概念,高跟鞋是临时买的,项链是我爸爸从藏族人那里买的银饰,结果没想到跟裙子还特别搭。”黄璐回想起自己的这一次戛纳之行,形容自己真的是“无知者无畏”。
黄璐出演《云的模样》
她在开幕式遇到了诺拉琼斯,王家卫的《蓝莓之夜》是那一年的开幕影片,她和这位女主角跳了一支舞,说喜欢听她唱歌。后来她又在戛纳唯一一家中餐馆偶遇侯孝贤、舒淇和张曼玉,还在一场饭局上见到了刁亦男,他的长片《夜车》也入围了那一届戛纳。“那时候他好羞涩,一整顿饭都不怎么说话。”
这一切都和她对戛纳最初的理解相差不大,满街都是大师,谁也不把谁当明星。擦肩而过,见怪不怪。
后来的首映礼给了她一个意外的震撼,“那一天,我觉得自己像个公主。”除了走红毯时受到的关注外,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影院里感受到的来自戛纳的专业。“黑暗里,我看到身边有记者和影评人,一直拿着本子在记笔记,写得飞快。”
那天她看自己的片子看哭了,最后一个画面里,剧中她饰演的被拐卖到农村给别人做媳妇儿的姑娘一刀杀死了自己的老公,“当时感觉大家都压抑了很久终于呼出一口气,一起大声鼓掌,鼓了5分钟。我还觉得蛮激动的。那时候忽然体会到电影的乐趣,拍摄的时候那么苦,那一刻觉得都是值得的。”
艺术家:大家都“飘了”
在戛纳,每一部入围主竞赛的影片真正的亮相,都集中在一整天里。
新闻发布会、photocall、红毯、放映。“只消这一天,全世界就都会看到你了。”耐安这样描述艺术家在戛纳的作为:“他们会受到国家元首级别一般的礼遇,电影工作者在那个时刻,会自豪的意识到自己像国王一样,受到了世界最高级别的尊重。红毯从你一踏出酒店的门就已经铺设好,你的脚就不会再踩在泥土上了。坐上礼宾车,那段时间里道路全部封锁,只允许载着你的车通过,沿途警察都穿着最正式的服装来迎接主竞赛影片的主创们。闪光灯像满天的星星。”
王小帅导演的《青红》在戛纳斩获评审团奖
王小帅回忆起这一场景亦有美滋滋的表情攀上眉头。他说那一天下来,大家都“飘了”,秦昊尤甚。对了,他还补充说,这礼遇只有主创可以享受,这是电影节给艺术家的礼物,投资方、制片人们享受不到。“电影节大概知道拍戏的时候导演和演员没少让制片人‘压榨’。”王小帅开玩笑地说。
“由衷的自豪,神圣而崇高。我眼看着我们的导演和演员,因为这样的场景,内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此不再会离开这个令他们骄傲的事业。”耐安说。黄璐也是从自己职业的开端就明确了自己对艺术片的热爱,“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消逝。就喜欢在那里头转,不想脱离出来。”
他们言谈中都吐露了一个相同的字眼:洗礼。
制片人:想办法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电影
伊莎第一次去戛纳,还要追溯到1993年,她记得清楚,因为那一年的金棕榈奖得主是中国导演陈凯歌。那时候她还在法国一个电影频道工作,和同事一起执行开幕和闭幕的颁奖活动。她原本被安排在颁奖当天返回巴黎,忽然传来消息说中国导演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得奖了,当时大家都没看过这部影片,伊莎随口说她知道她看了片子,“结果我就没走成”,完成了采访导演的工作。后来每每有中国电影人来戛纳,她都有接待和采访任务,张国荣、王家卫、张艺谋、杜琪峰等,都是由她的报道介绍给更多法国观众的。
“我希望法国的电影频道可以做更多关于中国电影的项目和报道。那个时候电视台好像对中国电影没有那么感兴趣,感觉他们还没有那么有名。后来每次,我会自荐去帮忙。”
后来伊莎做了独立制片人和法国电影联盟的大中华区联络人,也常常往来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参加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论坛、酒会,把法国的制片人、发行方和中国的电影人勾兑在一起。寻找有益的合作项目,寻找合拍伙伴一起投资、合作。从去年九月份开始,她的公司开始做亚洲电影的代理和海外买卖,她的工作即是和公司的同事一起联系国际电影节,介绍新的中国影片,也会寻找新的项目,联系各个国家的发行方。
耐安的工作与伊莎有一定程度的重合,只不过她是一张中国面孔。
“在戛纳,我的工作不是参赛、走红毯、接受采访,而是想办法让导演的电影可以让尽量多的人看到。世界各地最好的买片人、投资人,那段时间都会在那里,所以其实我基本上每天都不会闲着,结束后还会顺便去巴黎,推广和销售已经完成的影片,也会为自己下一个计划和项目做准备。”
为什么是他们,受到戛纳的青睐?
戛纳电影节已有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积淀,拥有一套坚固的评价体系和审美标准,同时不落窠臼,一直坚持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优质的电影艺术作品,并为各国电影人提供交易平台。中国电影人在戛纳电影节的生态圈,说到底是由戛纳的品位、门槛和游戏规则决定的。在谈论这条生态链条时,无法避开的话题是,中国和戛纳电影节的关系,到底为何?
选片人:作品本身才是进入戛纳的唯一门票
作为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Director’s Fortnight)的选片人,Benjamin向我们阐释了“导演双周”的选片过程和标准。
1968年5月,法国的“五月风暴”正劲,并不满足于电影节“戏剧性落幕”的新浪潮代表人物特吕弗等人联合其他成员在法国导演协会的帮助下,创建了名为“导演双周”的崭新单元。他们的宣言简练而有力:所有的电影生来都是平等自由的。
“导演双周”旨在发现和展示发展中国家青年电影导演的全新作品,关注国际区域下的电影生态。在之后几十年中,导演双周单元极速发展,风声水起。作品完全打破了拘束,甚至屡屡有视觉先锋的出现。中国导演武仕贤和尹丽川的作品都曾入围。
第63届戛纳电影节《日照重庆》获得金棕榈提名
成为“导演双周”单元的选片人,让Benjamin的观影维度不断拓宽,他对于各国电影行业的最新发展都了若指掌,这其中当然包括他“如数家珍”的中国导演。袁牧之,这样一个如今在国内都不常被提起和熟识的名字,却赫然出现在了他挚爱的中国电影导演名单中,他说《马路天使》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中国电影,那是一部可以让他在一秒钟从笑脸变成泪目的电影。“它美好的角色是生活本身,而在拍摄多年后它的社会背景依然生动。”
Benjamin说,他认为电影人应该葆有高尚的运动员精神——为过程而比赛,而并未为了终点。“竞争力与创造毫无关系,竞争力是完全相反的,它是尝试制造某种产品来满足假设得客户需求,观众可不是水壶。”
制片人:大家一起玩,不存在谁去迎合谁
2003年,耐安执行制作的《紫蝴蝶》第一次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她回想这一次入围的过程和原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是一次国际联合制片项目,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法国的电影公司,还包含其他的海外联合制片方。电影完成后,水准上乘,参加他国的电影节,没的说。
在“作品是进入戛纳唯一的门票”这一说法之上,耐安补充了自己对“中国电影与戛纳电影节”这一命题的看法。
她不关心戛纳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看法和中国电影人在戛纳的“生存现状”,她关心的是,我们艺术家在创作上的进步,是否跟得上戛纳的步伐。
“戛纳不是为中国人准备和工作的,而是在为全世界的电影工作者服务。他们一直试图在引领,而且还在不停地改变自己的眼光,调整自己的状态。他们对中国电影没有额外的关照和注目,他们在不停地突破自己,为的是寻找世界电影艺术新的风向标。”
在耐安看来,戛纳本身就是一个作品,一个巨大的片场。戛纳的高层决策人,就是戛纳电影节的导演、同时也是演员。
我们和戛纳,就是“大家一起玩,不存在谁去迎合谁。我们就做好我们的事情,艺术家的创作如果能够始终保持在同样的高度和水准,自然就可以和同样保持进步和高度的戛纳影展契合,这是互相的。”
当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法国人伊莎,她的第一反应是诚诚恳恳地说,现在目之所及全球范围内,最欢迎中国电影加入其中的,就是欧洲。
还有一个误区她想要极力澄清:“戛纳电影节如果没有选择你,绝对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你,就只会是因为他们不觉得你的片子真的好。他们的名额少,为的是要给世界介绍现在真正最有意思、最能代表当代的作品,不管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
如果要参与“一种关注”或者“导演双周”单元,直接寄DVD过去就可以了,“你不用非得认识他们法国人。”
但她也贴心地提醒年轻的中国电影人,寄DVD之前,要小心检查英文字幕的翻译,“小心翼翼地翻,有时候只是差了一点,就差了很多。字幕放得太快,或者太长,选片人就没法看懂你的片子,有时候看得人头疼,要给人时间看你的画面,而不是追着读字幕。”
戛纳生态圈的构成条件和游戏规则
演员:数不清的大小Party,一进去全是熟人
黄璐隔了几年回看自己在戛纳拍摄的纪录片,发现当年在那里擦肩而过的很多人,后来都认识了。“看的时候,很像时空倒转,镜头从天空往下看过来,哦,原来她在这儿,他也在这儿!”
戛纳之行结束后,黄璐如她所言,一头扎进了艺术电影的拍摄语境里,也因为作品的优秀,她后来跟随着《中国姑娘》、《红色康拜因》、《推拿》等电影先后去过柏林、威尼斯、釜山、比利时、乌克兰、罗马尼亚等超过20个海外电影节。有了一定知名度,就会认识更多的选片人。现在会有电影节选片人直接来问她有什么新片啊,拿来看一下。还有导演也会说,“找黄璐拍片就有可能参加海外电影节。”
她记得自己在戛纳的一个party上遇到了一位斯里兰卡导演,后来便有了机会去了斯里兰卡拍摄,她说这也算是自己海外艺术片拍摄道路的起点。后来又拍过一位泰国导演的片子,那个人认识新加坡电影节的人,帮她接洽上,她就被邀请去做了一次电影节评委,那一次的评委会主席是王小帅。
“在戛纳,想做得好,玩得开心,人脉和经验必不可少。”黄璐说,其实这个道理在任何一个海外电影节上都通用。她记得第一次去戛纳,一直跟着制片人孙雅丽“混”,“戛纳数不清的大小Party,孙小姐一进去全是熟人。”黄璐在party里的姿态从始至终都自尊而自由,“可以一边和别人看着平等的玩笑一边保持自己的个性。有一个party里有很多法国军装,他们都叫我beautiful lady,还要脱下自己的军装给我穿。没什么嘛,就披上去了。玩儿得很开心。”她也没什么功利心,不着急,“在party上认识导演或者制片人很正常,可以做一些自我介绍,请他们来看自己的电影,但我始终知道不会有什么事是马上谈成的。有一些看起来是没用的东西,说不定也在慢慢酝酿一些惊喜。”
导演:用最好的状态去拍电影,接受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节的尊重和检验
事实上,在令他声名鹊起的《青红》之前,1996年,王小帅就曾经受邀参与戛纳电影节。那一次他没有入围主竞赛,却还是蹭着张艺谋电影团队想去看看首映,“我自己进不去这个单元,那我要去看看到底主竞赛的影片是什么样子的,尽量一个不落。”结果头一遭就吃了“闭门羹”——他没有按照电影节要求穿着正式的西装和搭配领结。这是戛纳历史上从来不曾改变的规矩,除了这些,还对男士的皮鞋有严苛的要求,女士则必须穿着礼裙入场。王小帅在其中看到了这场电影盛宴的游戏规则,体会到了作为电影人被尊重的感动,“没有经过那个过程,内心是无法建立起那种东西的。”
后来《日照重庆》遭遇欧洲影评人的批评和媒体严苛的责难,他亦全盘接收。
“要么你就别入围,那说明人们根本看不上你;要么你的作品就要接受苛刻的审视。”戛纳十五年,这条路走下来,王小帅清楚的意识到作品本身才是铁一般的准绳,接受了最高规格的礼遇,经受了最严格的拷问,媒体间关于票房和大众的问题已经不会轻易影响到他了,“我们用最好的状态去拍电影,接受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节的检验和尊重,就是最好的事情。”
制片人:“中国之夜”?戛纳说,ok,没问题的。
当我们把“戛纳生态圈”这五个字说给耐安听后,她沉思片刻狠狠点头说,有的。她想到了这几年越来越热闹的“中国之夜”。这个参与戛纳并将触角探至电影节最核心腹地的制片人告诉我们,早前的戛纳没有这样的盛况,“戛纳每天晚上有各种各样无数的party,但是不得不承认,近几年动静最大的,是中国之夜。”party上很多面孔,于耐安而言都是陌生的,于电影而言而是无从说起。但是那一天,他们都会出现在那里,“豪华的游艇、照亮戛纳夜空的焰火、震耳欲聋的音乐,都是我们中国人发出的。在这里,你只要有钱,就可以组织和参与这样的活动,甚至可以请到戛纳官方的关键人物来出席。但这不是戛纳影展本身自己的,是旁人可以花钱买到的。当然,这是戛纳整体生态圈中存在的一个机会,你可以在这个影展期间用钱买到一个平台,或大或小,可以做自己的宣传,各方面的都可以。”
伊莎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她说她听到过中国传统的电影人对此有一些微词,为此她还专门和戛纳电影节的人沟通,对方给出的回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说,上世纪50年代,有很多想做女演员、男演员的人,都会自己跑去戛纳,在海边穿得很少,介绍自己,很多媒体去拍他们的照片。那些是法国和美国的小明星,现在是中国的了,戛纳说,ok,没问题的。”但是末了官方也补充说,只要你不影响到红毯、放映和一切正规活动的规则和时间。
“圈外人”离戛纳还有多远?
就在我们发稿前,第68届戛纳电影节的入围名单揭晓,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和侯孝贤的《聂隐娘》两部华语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我问伊莎,为什么?她说就是因为导演。“选择侯孝贤,不是因为是台湾电影,或者是武侠片,或者是舒淇,就因为是侯孝贤。贾樟柯也是同理。”这种“习惯”被黄璐称为是“戛纳的论资排辈”,伊莎给出了更理智的解释,“戛纳注重导演的角度、能力、观念,没错,主竞赛大多选择的都是之前看过的导演的片子,最重要的不是他电影的故事在讲什么,而是需要很强的导演风格。今年还有伍迪艾伦,他也是这样的导演。你能看出来他们不止在做一个一个的作品,而是一种连贯不变的气质和审美风格。”
戛纳这种价值观,耐安也深谙个中道理。所以她会说,“中国电影人在戛纳的生存状态”,这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她不同意。“中国电影人真正应该生存的地方,是你的母语市场,你的本土。所有中国导演,不应该是为了戛纳电影节拍,你应该为了你的内心、你的中国观众去拍。有没有戛纳,中国电影都是存在的,都得活下去的。”
她反观导演自身,在内部寻找无法进入“戛纳生态圈”的原因。“我们的创作环境不够好,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太多,这对所有中国导演都存在。审查,是他们都要面临的困扰,而且不是某一个导演在某一个时期的某一部片子遇到的问题,而是长年累月之后,艺术家的思想就会被禁锢了,自我审查、自我阉割,严重地伤害了创造力,他已经被异化了。”她说,中国导演能否走进戛纳,在戛纳的销售获得更好的成绩,还是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伊莎给年轻人的建议则从更加技术的角度入手。
她给我们讲到了戛纳电影市场上的早餐会。每天有10-15个桌子,专门为了年轻制片人而准备,每一张桌子有一个主持人,还会请来一位贵宾,是电影艺术家以外的特别有名的人,制片人、投资人、发行人……这样,每桌大概10-12个人,大家一起坐下来,一个个小时,可以去跟这位贵宾交流,问他问题,每一个人都可以介绍自己,每一天早上有一个机会见一个行业内有名的人,可以帮你了解、学习。
“他们想请一些中国人来参加,可是每一次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说英语。”
另外一个阻碍中国电影在海外发展市场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还爱电影买卖经纪公司。“这其实也和中国的电影没有太多国际可能性有关,他们的制作都是对国内市场的。
这也正是她和耐安都在担心的事情。
去年,有人问戛纳电影节主席,怎么中国电影那么少?他回答说,我们看了很多,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影片。“中国每年拍800部电影,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节却找不出一个好的作品。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的市场,一部影片动不动就好几个亿的票房,但中国影片在海外的市场却越来越小。”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戛纳生态圈正在面临极具缩小的现状,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来鲜少见到新鲜导演面孔的出现,因为他们都在做商业电影,为的是迎合中国年轻观众的口味,这样的电影,不止是电影节不会选择,海外的发行方也都不会选择。
问耐安,你对那些对戛纳怀有梦想和对这个圈子抱有期待的年轻中国电影人有什么想说的?
她笑了:“我说的话有点狠,你确定可以刊登嘛?”
说说看……
“让戛纳见鬼去吧,好好拍你们想拍的东西。”
坐在一边的黄璐听罢笑了,她想起自己最初在戛纳,背着一个粉色nike双肩包,没事的时候就跟着孙小姐到处跑,听她在那里谈“电影国际大买卖”,自己坐在旁边吃冰淇淋,潜移默化在那里学习她怎么当一个制片。还有在那里迷了路,也不着急,就用DV机拍下当时自己的样子。
“戛纳是外物。但这不防碍我们和戛纳惺惺相惜。”耐安对她说。
来源: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