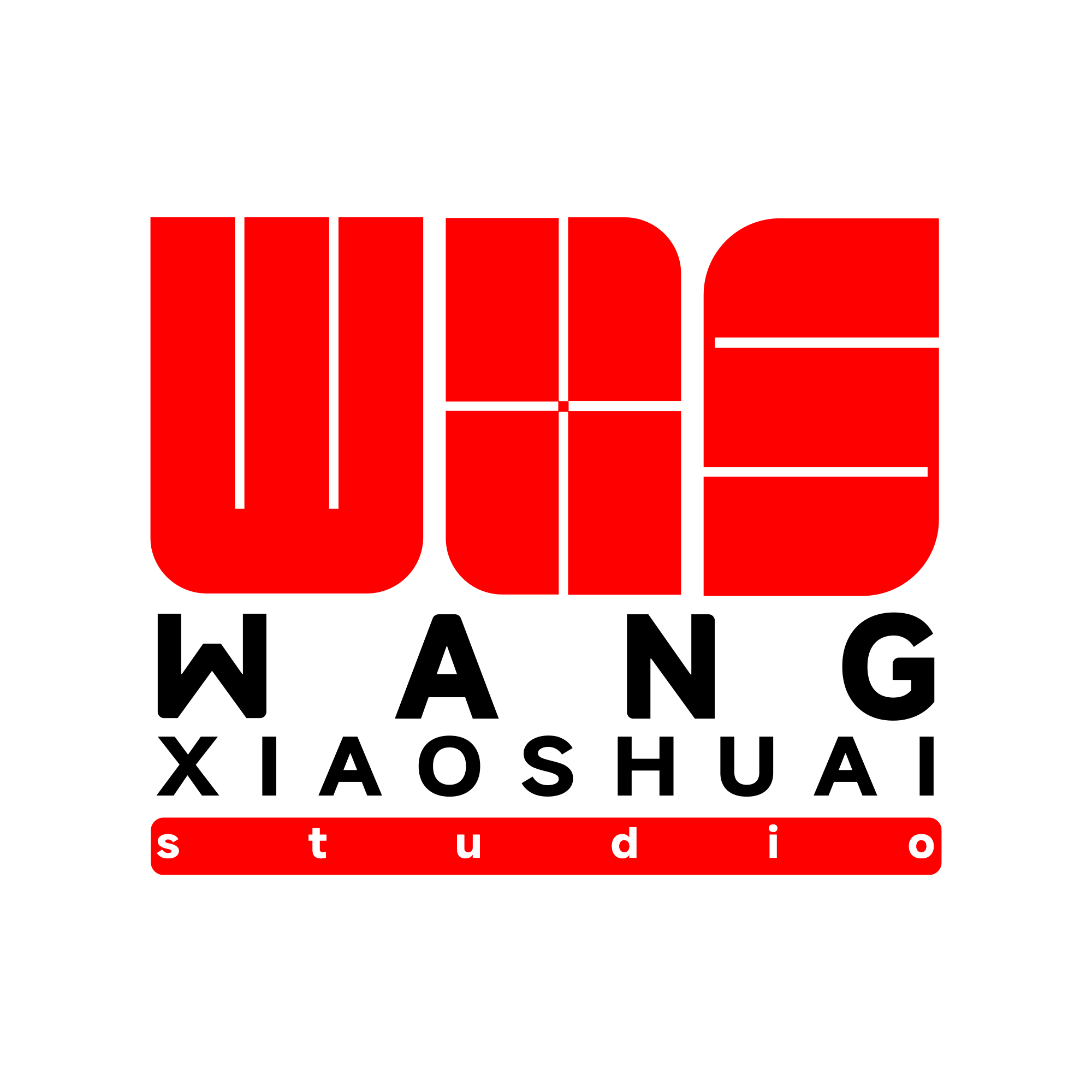一丶谈《闯入者》
这是对当下的感受与反思
杨城:咱们先从《闯入者》聊吧,首先想了解你当时怎么想拍一个这样的故事的?
王小帅:首先《闯入者》是具有当下性的,我在拍电影之前总是先顾虑自己对当下的感受。我们自己家人或者朋友的家人,大家一聊起来隔代的孩子是怎么弄的,自己跟父母是怎么处的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都是相同的,那这个“相同”的东西是从哪来的?《闯入者》里面以老邓(吕中饰演)为代表的这一代人,以及在她影响下的孩子和这种中国式的家庭关系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我觉得可能那一代人的相似性是有依据的,我想探讨这个依据。这样我就把老邓放在现代家庭和现代社会完全失控、盲目瞎奔状态,在这样一个状态里拉回到形成她人格特点的过去。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这样可以提纲挈领的浮现出整个这一代特殊的中国人,老邓是这个样子的状态,我的父母长辈也是这样的,那我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特点了?我们这一代是不是新人类?后来我想不是,我是60年代出生的,一定也会受影响。这样我就可以通过看上一代再反观我们这一代,我们是“中国人”,而且我们是“那样的中国人”,跟民国跟清朝不一样,是一代特别的中国人。而且现在我们的父辈这一代人即将进入他的老年甚至要离去,那么我就想,这个电影可能会帮助我去记录下来这么一种感受。
杨城:那《闯入者》的风格是怎么确定的呢?我现在还没有看电影,但是看到你们的宣传物料,感觉有一些惊悚悬疑的风格。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风格呢?有没有投资公司出于一定的市场考虑给你提的建议?
王小帅:《闯入者》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琐碎的生活片,要去表现吃喝拉撒和家庭关系,除了这些之外我想要纵深一点,把它的前史拉进来,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呢?我在想怎么做的这个过程中才有了电影现在的变化,说一个独居老人被骚扰的一个事件。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是很琐碎的,有了这个点之后,所有的东西就慢慢浮现出来了。一个人生活在麻木状态里,你要想被什么东西提醒,就一定是有一个外力的,这个外力出现以后,后面的风格自然就会跟进来,一个人的生活被打搅,可能内心就会浮现出焦虑的东西,慢慢的这个焦虑就开始猜疑,然后发生变化,这样自然的就需要相对能够制造悬念。在制造悬疑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给它定位成一个悬疑片、类型片,我不想那么简单化的去做。相反,我让这个打扰去增加一种气氛,表面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她内心的疑虑会出来,所以这个电影是这么一种气氛。
杨城:那这个电影,是不是从吕中老师扮演的老人的生活环境开始,带出年轻人的世界?
王小帅:老邓(吕中饰演)她是绝对的中心人物。这个电影的前五分之四是在铺垫,都是为了后五分之一那一下在做铺垫,后面这一小段展现的是老邓的过去,但是“是未来的过去”,它不是简单的闪回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任何一段历史穿越到现在,表面上看过去是没有了,但是实际上过去的东西、时间在空气里是存在的。正因为这么一个过去,而影响了电影前五分之四她所有的行为,她的生活,她的家庭环境,以及她和孩子之间莫名其妙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从观看的角度来讲,要用大量的时间来准备接受现在所展现的一切。
杨城:这让我想到了《日照重庆》,《日照重庆》悬疑感觉就很强。
王小帅:其实《日照重庆》相反,它有故意的把事件进行遮蔽,跟观众想办法做故事。《闯入者》前五分之四是全部展开的,让观众觉得一切都在面上没有躲藏,但是有一个情绪是暗藏在下面,通过这样来推进的,到最后五分之一的时候再来一个反转。
杨城:刚才听你说《闯入者》结构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哈内克的《隐藏摄像机》。都是一个平静的生活被闯入的一个状态,勾连起他的一些过去。
王小帅:对!我们在威尼斯的时候有好多人都这么说。《隐藏摄像机》我看了一遍,我是对前面摄像机视点的部分比较感兴趣,但是因为我只看了一遍,没有太去琢磨,只是觉得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二丶谈导演的创作历程
《梦幻田园》为还韩三平人情而拍,只能算半部
杨城:其实我觉得《日照重庆》有点儿生不逢时了,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它的结果可能会不太一样。
王小帅:我就告诉你,我就没有生逢时过,从来都是生不逢时。说起来叫生不逢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不想去逢这个时。
杨城:我看你有一次采访时说,如果你这样的导演成为主流了,就不正常了。
王小帅:对,不正常了。就像当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第五代都在搞探索影片,大家讨论最多是怎么商业化,怎么把电影变成像好莱坞一样带有机制的东西,而不光是探讨艺术。但突然之间都这样的话,没人想艺术这个事儿了也不行,我也是自己自不量力吧,想要做一些小平衡。
杨城:其实第五代导演,还是集体意识形态的,第六代个人意识一下子就出来了。
王小帅:对,就是那个时间段出来一下,那段时间我们也合过一阵时宜,就是在电影还没有市场化、还跟电影局在叫板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能成为一个话题,现在连这个话题都完全没有了,全是小鲜肉和小仙女们占据了。
杨城:《闯入者》用你的话来说是你的第十部半作品,《梦幻田园》你算半个。
王小帅:前几天,我还看了一遍《梦幻田园》,我觉得还行,那么长时间不看,比我印象中好一些,让我能原谅自己一点了。
杨城:记得《梦幻田园》是一个带龙标的电影。
王小帅:是,其实《扁担姑娘》也是。但是《扁担姑娘》当时没通过,后面到1999年才通过。其实就是为了还韩三平一个人情才,做了《梦幻田园》,他那个时候就告诉我要做喜剧,喜剧至少能通过审查,有市场。其实《梦幻田园》是一个黑色幽默的喜剧,带有荒诞性。当时觉得还是有危险,最后那就彻底一点,结果一彻底就变成现在这样的《梦幻田园》了,但也是好玩儿吧,人哪有说不试试看的。
杨城:那个时候试比现在试好。
王小帅:对!那时候电影很快通过了,当时韩爷(韩三平)说这次不容易,没让你改一个台词一个镜头,我说喜剧肯定的啊,后面这个电影也没有下文,没有上映。
杨城:所以说,可能没有人比独立电影导演更清楚怎么通过审查,但是有的时候是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王小帅:对!因为身经百战嘛
杨城:说回你第一部《冬春的日子》,这个电影创作的一个缘起和大概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王小帅: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次跟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电影的状况跟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候都是计划经济,是有电影厂的。现在的年轻人想进入电影工业里面,它的难度是在于怎么让资本信任你,当年的难度是在于你先要获得导演两个字的权力,那个时候权力是很难拿到的,因为是国家体制嘛!
杨城:那个时候还有厂标呢。
王小帅:对,厂标。年轻人想要变换这个身份,过去是很讲究的,要师傅带徒弟,论辈分,年轻人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也可能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拿到摄影证。我那个时候就属于等不及,我在福建厂呆了快一年,当时那个剧本花了半年时间写申请,最后没通过,我就跑回来了。跑回来就有恐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单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并且租房子是违法的,要租房子的话得说这家主人是我亲戚什么的。没有办法租房子,没有单位,这样在社会上是很恐慌的,同时在那个时间段,第五代导演在整个演变过程中,他们有强大的话语权,但是实际上作为在边缘化的年轻人。我也是需要证明自己,需要表达自己的可能性,欲望也很强大的,当时我觉得要赶紧表达出来,不管是什么情况。
拍《冬春的日子》从一开始就不像拍电影,它跟那个时代拍电影的原则、想法和动静是两回事,没有厂标,甚至没有摄制组,只有一台摄影机。但这个电影没有变成工业化也是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正好也契合了这个电影所要表达的个体意识。那个时候也犹豫过,这么干行吗?是不是在拍电影?有时候跟小东(《冬春的日子》主演刘小东)聊说这样行不行,后来我们就用排除法,当我们犹豫这个行不行的时候,就问自己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不行?后来发现没有人说不行,没有人说我拿一个摄影机很low。或者我们说一下很苦闷的事情,有人反对吗?没人反对,没有法律禁止也没有意识形态或者任何一个外在的技术条件说你这样不对,我们就这样排除掉了所有的不对,那就这么干。所以我觉得我下意识和有意识相结合的在做这个《冬春的日子》。具体就是借钱或者借点儿别的什么,就这样做了。当时想把它拍出一个影就行了,那个时候能够拍出影的东西,除了照相机就靠摄影机,无路可选。我们也想过拿照相机拍完一张一张连起来,但是荒诞的做不到。所以逼迫无奈走这条路。也因为我是学电影的,必然要这么做。
杨城:张元的《妈妈》跟《冬春的日子》,开了独立电影剧情片的先河,在《冬春的日子》之前,张元那个《妈妈》已经拍了,你也有参与。这个事儿对你当时有没有刺激?
王小帅:刺激确实是有的,但不是那么大。因为《妈妈》我自己一直在参与在制作过程中,从开始写剧本、分镜头,我一直都很接近的。但《妈妈》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要等着比如说投资,张元以及原作者他们来定这个事情,也让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想回到过去体制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张元来说是很好的机会,它呈现出了一种可能性。《妈妈》做完之后,我就觉得既然这个事情跟我脱离了关系,我不能控制的话,我就重新控制一下我自己,就开始做这个《冬春的日子》。
杨城:我觉得《冬春的日子》更个人化一点。因为《妈妈》它是一个别人的故事,别的群体的故事。《冬春的日子》拍的是刘小东和俞红,但是《冬春的日子》有你自己很深的投射。
王小帅:就是精神的投射。《妈妈》的剧本已经非常靠近个体,但是毕竟原小说还是老一代的思路去想问题。
杨城:所以《冬春的日子》在这个意义上更鲜明一些。当时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你们有几个人?
王小帅:我们人最多的时候是去东北的时候,两个演员小东和喻红,灯光是一个人,一个场记,还有摄影助理,加我6个人。当时刘小东家里人也帮忙扛扛东西弄弄灯,帮了很大的忙,最大的规模差不多就是这个。
杨城:估计这个比《妈妈》剧组的人少多了。
王小帅:《妈妈》是一个正常的剧组。这个导演组就我一个人,场记都是第一次带。当时我们最有经验的是灯光师,灯光师算拍过电影的,其他的都是没有正式上过手。
杨城:你还记得《冬春的日子》在国内第一次给大家看的情景吗?
王小帅:第一次是在一个丹麦的人家里面。90年代的时候老外家里经常搞party,有次在party上我说拍了部电影但是没地方看,然后有一个丹麦人到说到我家放行不行?当然行啊!那时候只能用胶片放映机放,我们自己想办法找了两个放映机,然后老外周六就找了一帮人搞一个party,当这帮人喝的差不多了,就坐下来开放,当时放映就打到一个墙上,那是第一次放映,挺好玩儿的,后来又在法国使馆做了一次。
杨城:这两场放映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怎么样?
王小帅:对我来说,真的就像处男似的,第一回嘛,完全不知道它会是什么情况。但其实有一点我还是比较清楚的,我首先知道这不能代表我的最高水平,但是态度以及我的角度和方向一定是有意思的。因为技术太差了,出了太多的故障,声音也是后期做的。当时有人反映还很好,我也只是听听,因为对我来说无关紧要。到后来去电影节以后,我也确实感觉到至少别人看这个电影是带有特殊眼光的,没有把它当工业来看。他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当时的环境里冒出了一个特别新鲜、带有强烈个人印记,而且带有悲伤情绪的年轻人的电影
杨城:对,在这个电影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都是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东西。
王小帅:包括《红高粱》《一个和八个》,还都是那样一个情况。这个很弱的,有点像小草一样的东西出来,有点儿像现在我们去观察朝鲜,突然之间北朝鲜出来这么一个电影,我们肯定会觉得这个世道要变,肯定觉得有趣,我们当时在这个大环境下造成这个影响。
杨城:第二部就是《极度寒冷》,《极度寒冷》跟《冬春的日子》一样,拍的也是当代艺术领域的人,你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对艺术家的生活很感兴趣?
王小帅:我觉得还是因为走不远。因为条件不像正常拍电影的东西,就像一个望远镜,那个时候还没有钱买一个哈勃望远镜,手里就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只能看到月亮看到周围。其实《冬春的日子》也是根本不具备拍电影的正规条件。当时就觉得要把《冬春的日子》很多遗憾要补上去,《冬春的日子》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同期声,所以我下决心再拍的话一定要有同期声,那个时候电影很少有用同期声的,都是后期配音。所以后来就用16毫米机器,16毫米机器便宜一点而且噪音小。其他也走不远,还是周边找的,找自己熟悉的艺术圈的一些东西。
杨城:但是从《极度寒冷》开始你开始用专业演员了。
王小帅:《冬春的日子》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小东我们俩处的挺好又熟。等到《极度寒冷》的时候就希望专业一点,如果没有贾宏声,这个电影又要变了,去找艺术家或者找一个什么人去来演,小东是不可能演第二回了,他演《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已经崩溃了,不可能有第二回。贾宏声出现以后,我觉得贾宏声是带有那个气质的,对我来说他不像个演员,虽然很帅,马晓晴也是因为有贾宏声才搭档一个马晓晴。三丶谈审查与市场变化
“它用一种形式在阉割你想法的时候,思想比身体的困惑还要恐怖”
杨城:《极度寒冷》的时候,你是尝试去接触体制的,还是你想做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
王小帅:《极度寒冷》是没可能的,因为《极度寒冷》给我下了禁拍黑名单,下达过这种文件并且都抄送各省市宣传部、电影厂,这有这个东西,所以还没有精力去搞这个,而且《极度寒冷》本身这个题材更不可能过国内的关卡。
杨城:那等于是从《扁担姑娘》开始,你正式的跟体制有一个深入的互动,这个片子被审了三年。第一次跟审查打交道是什么感受?
王小帅:那个感觉还不如做地下电影呢,我觉得物理上的折磨还可以忍受,至少思想是自由的,做不好做得好,是自己的事儿。审查就变成了阉割你,我觉得很恐怖,它用一种形式在阉割你想法的时候,思想比身体的困惑还要恐怖,最基本的闪念都不可以存在,那是很恐怖的。最后我觉得《扁担姑娘》导演已经不是我了,是管审查我的那个哥们,浪费了三四年的时间。当时我们坐一块我请他喝酒,想让他放我一马,他说他也改不动了,通篇拍的这个东西,除非这个片子不要了,要不改不出来。找几场有阳光的戏都找不着,一直下雨阴呼呼的,所以他最后决定放弃。当时我心里就乐了,心想你得知道我们拍电影就是这样一个气质,要想在这个气质里找出你想要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杨城:那个片是哪个厂的?
王小帅:北影厂。其实在95年左右,中国谈论最多的是社会资金来投电影,那时候刚刚开始,但是还害怕社会资金完全投入,因为过去的国家机制还在。国家只是刚刚觉得投电影的钱可以在外面吸资金,但是任何一家公司不可以独立的投资,必须挂靠找一家电影厂,把它演变成社会资金,由电影厂再出品这个电影,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些松动,当时我们也是出于一种这样的状态。当市场化的经验进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找人做这个事儿,于是就想到了年轻人,想到了我们这群人,也就解决我审查和黑名单的问题。当时等了五六个月,其实《扁担姑娘》错过了最好的拍摄时间,原计划的拍摄是在夏天的7月份,直接在最热的天到武汉去拍,后来一直到拖到快11月份了,才允许我去拍,错过了最好的时间,也是一个遗憾。
杨城:这么说当时投资方还是有很明确的商业诉求的?
王小帅:对,但那个时候的商业诉求不像现在这么清楚,那个时候商业诉求就是“能够进入”,能够拍电影和能够投资电影。过去不允许的,这样其实是两个巨大的差别。但是那个时候什么叫商业电影,我觉得投资人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市场。在95、96年还没有票房这一说,那个时候还是卖拷贝,做完之后看谁要,比如说福建厂或哪个电影厂要,就来跟我定,在当时一万块钱一个拷贝,比如说卖了100个拷贝,那就是一百万。那个时候投资电影在五六十万左右,如果卖100个拷贝就算拉平或者是挣点儿钱了。所以《扁担姑娘》拍完面临的是到底有几个拷贝的问题,可是等到99年开始有所谓有市场了,《扁担姑娘》也不放了。
杨城:现在来看,有商业诉求的投资方能投资这样一个气质的电影太不可思议了!
王小帅:那时候真的没有到现在这样的商业意识。所谓的商业化并没有明确,什么枪战、警匪以及冯小刚的喜剧都没有出现,还没有形成概念,只是体制在变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那个时候能够进来投,以及他们选择《扁担姑娘》是因为觉得王小帅望前走了一步,走到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了,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了,他们以这个角度来对艺术。
杨城:到《十七岁的单车》,就能看到你拍电影的技术条件已经非常好了。
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是最顺畅的,最像拍电影的一个电影。这也跟台湾的电影公司带进来一点点专业精神有关系。《扁担姑娘》当时用的都是我们北影厂的老班子,我想用新的方法、新的概念来呈现,但是北影厂的老班子还是按照过去国家电影厂拍戏的工作方式,这样相互之间碰撞的很厉害,我在摄制组经常领着人跟他们对着干。到《十七岁的单车》的时候,至少在我背后不用完全依赖于过去老电影厂班子,我可以在自己的社会里面搭班子,交流的对象是台湾过来的人,这样理念上会沟通的比较顺畅。
杨城:现在你回头看你的电影,你觉得你的风格转变关键的节点是什么?
王小帅:我觉得我还在找,我倒是愿意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从《冬春的日子》小小自我的东西,被老一代说成你们年轻人自恋无病呻吟,这个倒是越来越重要,这个东西是一个种子,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也好,个人的焦虑也好,它是一个社会的细胞,一个种子,你不能无视它。实际上到《极度寒冷》《扁担姑娘》的时候,你看《扁担姑娘》到了工农兵里面,工农兵里面也是小扁担、小姑娘,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处境在社会里面,所以一直以来,这种故事和人物的精神诉求都没有变,所以我也谈不上哪个点是我变化的点,只是题材不一样。唯一的是《日照重庆》被“以为”成一个警匪枪战片的商业片,这都是误解。
杨城:其实像《日照重庆》,我觉得应该跟很多观众是有共鸣的,不是完全艺术家个人化的东西。
王小帅:包括《十七岁的单车》也是,实际上在《十七岁的单车》离大家能看到青春什么的。
杨城:如果现在放的话,反应会更好。
王小帅:就像你说的,生不逢时,不合时宜。你看现在多少青春片,一部一部的上,直到差不多找不着钱了才会开始转向。
杨城:对,别人在拍青春片的时候,你又在拍小孩和老人。
王小帅:我觉得如果跟着这个风潮,自己会很不踏实,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不踏实!另外我觉得现在在追求真正所谓市场和票房成功的时候,我觉得要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退路,你想想,当一部电影一下子出现那么多票房,那下一部就会被票房能不能超过上一部而绑架走形,如果你没有那样的话,反而好,始终还能够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去做,这样反而舒服。四丶谈如何创作
如何处理剧本?怎么与导演和演员进行沟通
杨城:你以《闯入者》为例,你讲一下你的工作方法和创作方法,比如说你写剧本的习惯,你喜欢把剧本写的很详细,还是提纲挈领,后面拍摄的时候,慢慢丰富?
王小帅:这方面倒是有转变的,一开始前几部有一点心高气傲。年轻人嘛,觉得自己什么都想好了,觉得向现代学习,要去现场脑动大开。其实那个时候恰恰没想好,所以剧本会比较糙。在一开始早期带有作坊、手工的形式是好玩儿的,但是后来慢慢的启动,开始有正规化的时候,我觉得就像一个制度一样,你不能把所有东西压到导演身上,因为万一在过程中给阻吓住了以后,那么庞大的一个队伍在那里,然后有钱什么的,这会影响你的心境的。后来我剧本就比较细了,像《十七岁的单车》剧本是最细的,它的结构以及人物之间的变化交叉,这里面有强大的故事推动,就要有剧本。所以这有一点点变化,越到后来我觉得越需要剧本的细致度,这是一个基础,你不能够把这个基础忽略掉。你可以在最后做的时候,想办法再去走开或者变化,但是实在有问题的话,你至少可以回到你曾经的基础上面,所以剧本是做的越来越细。
杨城:《闯入者》这个名字一开始就定了吗?
王小帅:也没有。这个名字也是纠结了半天,我也不知道是谁定出来的。我做电影,我是有企图让电影正常得到放映,得到正常份额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公平,不能说我的电影不适应社会、体制,而没有正常公平的给电影提供渠道。那么除非它自然的消亡,那么剩下的就要靠去争取,所以我一直在争取这个份额,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无形在坚持着创作、坚持理念价值观,这是首先要保住这个核心。剩下的部分,也不得不去做一些所谓的妥协,包括取名字,就是在中国的名字和国外的名字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国外的话,你走向一个相当文质彬彬的名字是行得通的,甚至是会有更好更高的效果,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况下,既然保留创作态度,又想进到市场里面,名字上不得不做一些改变。但是《闯入者》这个名字不完全是为了进入市场,它也有双重的意义,在这个电影中本身有东西闯入他,他也经常闯入到别人的生活,甚至年轻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识都已经被过去洗干净了,也被闯入过,这个闯入本身有这个意思,同时也带有动作性,所以就用了这个。
杨城: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比《日照重庆》可能让普通观众更容易记忆。《日照重庆》一听就知道是王小帅风格的作品。你指导演员表演,是喜欢较长时间的排练还是更喜欢他们现场直接的反应?
王小帅:有一个程序是必须要做的,像话剧排练一样,要有对台词的环节,像《闯入者》这里面都是老戏骨了,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对词。对词对我来说就很有帮助,首先双方检验,检验我写的词是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同时通过他们的对词念白可以看出哪些方面是OK的。但是我可以放掉的是排练,因为舞台剧演员对排练很重视,在舞台上的就是他,导演在下面是失控的,那么他需要千方百计把这个东西弄踏实了。但电影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就是环境的不确定性,镜头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多的变化性,演员就更容易有变化,他们只要把基本的台词记住之后,用他们的经验就可以适应任何一个场合去发挥,然后我也觉得有了基本的台词底子以后,你就可以变化了。在拍胶片的年代,因为胶片有片比,就会很谨慎,会排练很多遍,然后拍,尽量实拍的时候遍数越少越好,省胶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非常耗人的,你可能把很多好东西错过了,所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上来就拿胶片示范,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很好,每个演员的状态都不一样,像在《左右》的时候,刘威葳,她第一遍最好,后来永远超越不了第一遍,当时我们开玩笑叫她“刘一条”,她感性的特别好,如果你第一遍不拍就错过了,有些人不行,有些人第一遍肯定是蒙的,得两遍三遍以后慢慢找到感觉。所以每个演员不一样,都要实拍去做。在现场这种排练比较少,所谓的排练也带着实拍走。现在用数码就更无所谓了,就开着机,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杨城:和摄影师工作的方式呢,是让他先来调,还是你事先有一个确定的构图给到他?
王小帅:一般都是我给定画面,有一些摄影师很主动的愿意去找这个东西,但是真正到电影上不太可能。因为摄影师的角度和导演的角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的电影上都是我直接定构图。五丶谈电影市场化
“一个社会没有批判,假装梦幻中,跟吸毒品一样”
杨城:我想问一下,关于档期的问题,因为这个片子首映都过去特别长时间了。你怎么会到这个档期才拿出来给观众看呢?杨城:我想问一下,关于档期的问题,因为这个片子首映都过去特别长时间了。怎么会到这个档期才拿出来给观众看呢?
王小帅:因为我们得准备工作,包括宣传,现在宣传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说一个电影进了影院,不用宣传全中国就知道了,当然有些片子是这样的,可我们不是。所以就需要时间长,之前《青红》开始,我们都是因为宣传和成本上的一些考虑,我们都是借着戛纳或者借着柏林电影节一得奖,媒体关注的时候趁势去发,通过几次试验,我觉得还是不行,这样是不够的。《闯入者》虽然去了威尼斯,但是我们回来以后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准备国内的宣传和很多的工作,而不能匆匆忙忙赶快发行,一切都衔接不上。这个时间一错开,很自然就错到这个时候了
杨城:我个人挺期待它的市场表现的。
王小帅:看吧,五一档我也不知道,中国慢慢形成档期,形成规律,我觉得也不是百分之百这个档期就会怎么样,但是假期的档期相对比平时要好一点,我觉得大家进去试试看,因为我们现在宣传的备案还是挺多的,会慢慢做一些营销。
杨城:这种大档体量比较大,需要更丰富的产品,这是有好处的地方。你的电影经常有一些批判性在里面,现在大家担心批判性会不会有影响市场,因为观众去电影院去放松,去娱乐的,你怎么看这个关系?
王小帅:我始终秉承电影本身作为一个最大的娱乐工具,要正视它,这是没办法的。我们小时候看电影好玩儿嘛,打仗、好人、坏人,这是一个基本的娱乐点,是没有问题的。电影除了娱乐之外,它的批判性以及艺术的特质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个之外,其实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作者电影或者有一些艺术电影它秉承的对人性或者对社会、对历史的批判一直还在,其实没有消亡,它和整个大的商业构架是并存的,只是小群和大群的区别。中国在这样一种大娱乐时代,人们慢慢被一种声音控制了,电影只是一个娱乐,所有人都在说在现实生活里看到太多丑陋,本身的压力、抑郁已经很大了,看电影是需要放松的。但实际上整个中国现在目前的发展恶劣性就在这里,这是一种新的洗脑方式。通过这样一种让你假装梦幻中,获得跟吸毒品一样享受两个小时的欢愉。实际上回到现实,造成的压力和苦闷的一直还在发生。而这个东西又没有人去触碰,观众也不愿意触碰,拍电影人也不愿意触碰,资本家更也不愿意触碰,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讲是需要大家警惕的。如果观众、导演,资本家和媒体,有多一点这方面的意识,能够投放这方面的影视作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刺激,这种刺激会带来他想要的改变,这样至少比麻痹要好。这是我个人的愿望,太渺小了,因为太少的群体关注这个。至少从我的逻辑分析上它是对的。应该有这样的作品来帮助我们,如果说在麻木之余还有一点警醒的话,可能它对现实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批判性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没有这种批判,完全是在一种莺歌燕舞之中,当然有些人会高兴,所以说对老百姓来说我也不能强求这个。
杨城:2003年的时候,电影局跟你有一次谈话,说现在电影要市场化了,你们要为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做一些贡献,你当时说了一些话,大概意思是说你觉得这是绑着你们的腿,然后把你们推下海,你对那个东西当时是有恐惧的,现在十几年过去了,针对现在的创作环境跟市场环境,你对新的电影人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小帅:我觉得至少我们在几个当口,我们的担忧和提醒,都是没有错的。我们最早应对电市场化,从地下电影走出来,把创作当成一个基本的权力,自由和创作这都是一步一步争取的。但是中国的环境是你的个人争取一定要结合“上面”的改变,2003年确实是“上面”的一种改变,电影也得挣钱不能光靠国家投钱了。有了这个概念,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当时给我们来说,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能会走偏,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是挺好,我们可以拍电影了,可当他把你拍电影的兴致引导到你赶快去走市场的时候,我觉得又偏了,因为这不是说让你发挥你所有的才智以及想象去拍电影,他要做的是市场,肯定就像现在这个结局,当时我们担忧的就是在这一点上,没有回归到我们拍电影当时本真的诉求,不是对电影创作的自由度,想象力的开发,而是为了挣钱,那我觉得这么走下去又跟我们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在后十几年经历市场化后,我们依然是在边缘化,依然是担忧的。而这个担忧,现在已经被更多人看到了它的结果,大家很少在讨论电影创作本身了,都是粗制滥造的。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始终在边缘,但确实我们的想法前瞻性比较强。
杨城:当时你们是边缘,现在更多人是夹缝,审查还没有变,另一边是资本和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
王小帅:我们是明面上的夹缝,像你们以前做的片子更夹缝,还有一些人在下面始终秉承自己的创作和没有进入市场,这是相对可贵的一个土壤。但是在明面上你得去争取,我们就必须要争取了,争取市场上的话语或者电影的走向,对现在这种状况反思还是要有的。
杨城:我觉得你们可以把这个夹缝撑的更大一些,你们现在有这个可能。
王小帅:对,没错。撑起来。
杨城:好,我们这次就先聊到这儿。
来源:影视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