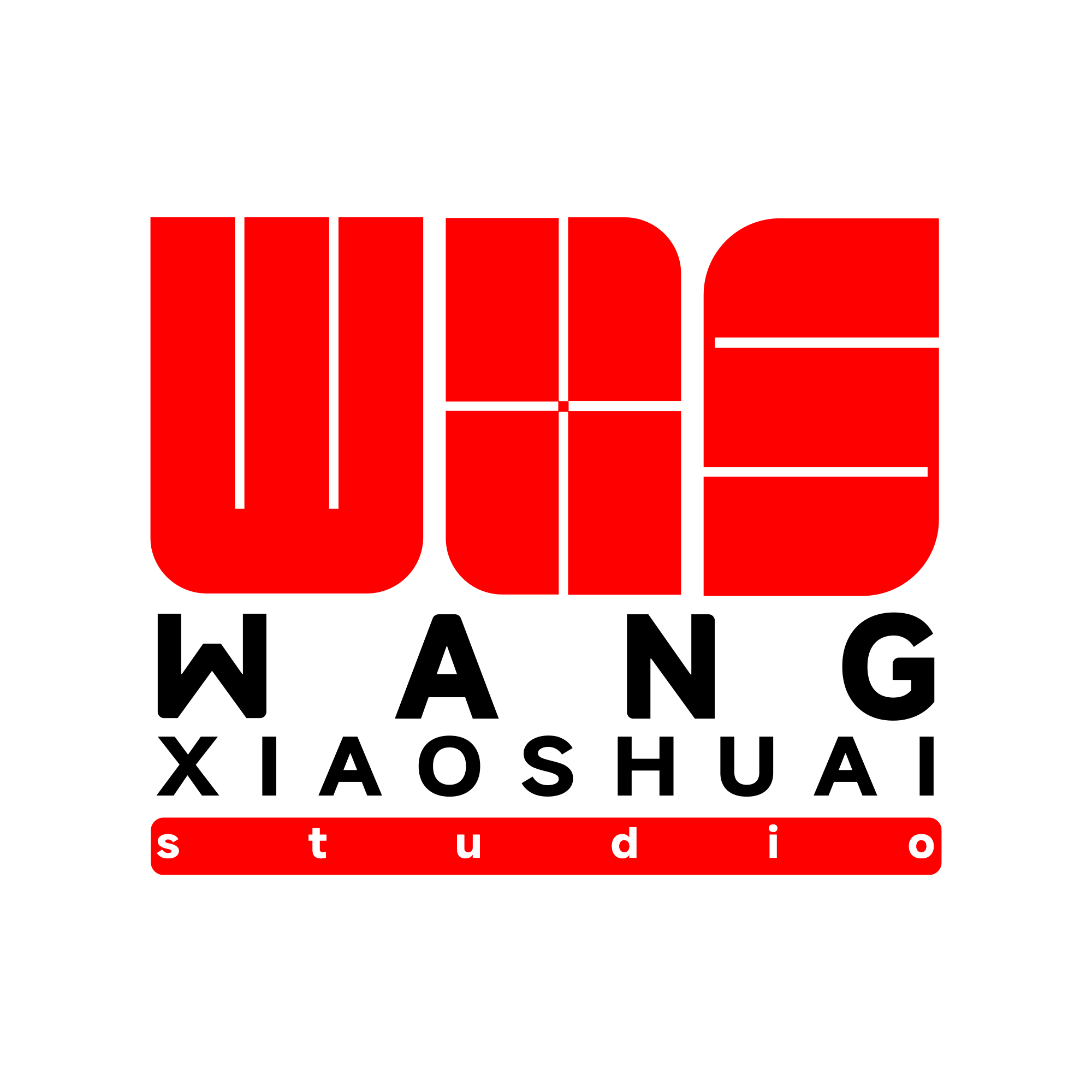王小帅的办公室在一座远离市区的商住两用的大厦里,走进这座如庞大蜂巢般的建筑,能看到表情木然的银行保安,被拆掉了大门的倒闭商铺,临时围起来的建筑工地,电梯口站着的手臂上布满纹身的老外和面目模糊的女孩。
所以推开大门,看到贴满电影海报的房间时,一瞬间有点恍惚的感觉。
王小帅坐在里屋的办公桌前,旁若无人地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并不急于接受采访,而是继续写了一会。窗外的视野很好,但办公室本身完全缺乏现代感,甚至连台电脑都没有。他终于停笔,合上本子,解释说:“现在有点不想用电脑了,开关都很麻烦,有点病态……”
他的新片《闯入者》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的竞赛单元,影片将镜头对准了一位老太太,明显缺乏商业号召力,但是他觉得年纪大的人物能够承载的历史和精神历程会长一些。“人就像蜗牛,爬过之后会留下一条痕迹。”他说。
这条“痕迹”对王小帅来说至关重要,否则小到他的个人身份,大到当下的社会状况,都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他在上海出生,在贵阳山区的三线厂长大,通过报考美院附中来到北京,然后是1989年夏天,当他从电影学院毕业,惶惑地面对未来时,无论是历史还是生活环境,都已经被改写若干次了,这让他本能地对大众和主流怀有警惕和“不安”。
随着他人到中年,这条痕迹也被不断拉长。对历史和个体命运的近乎固执的坚持,既给他的创作划定了准绳,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因为厚重同时也意味着难以把握。
这也是“第六代导演”的普遍境遇,王小帅曾经用“溃不成军”形容过第六代,这一代创作者在社会剧变中成长起来,从盗版碟中为人所知,又面临与大片的商业竞争,由于始终未能掌握话语权而一直被称为“青年导演”。所以不难理解,他们常常提到“缝隙”。
如今王小帅比前几年显得更加淡然,甚至有一种隐藏得很深的幽默感,你能发现他平衡着各种责任和意愿的努力。王小帅在采访中强调了“理性”,他的影片总是用克制掩盖了高潮,没有团圆也错失了伤感,主人公的解脱只是在某个瞬间抵达了一个真空般的沉默而孤独的境地,随后时间又缓缓流淌起来,生活还在嘈杂中继续。
而一切的冷静、挫败和挣扎的勇气或许都来自许多年前那个梦幻般的的夏夜:“大银幕,风一吹满山的人,占位子的在这边,不占位子在银幕背后,两边全是农民,漫山遍野,就看一部电影,风一吹,银幕晃荡着,下雨打着伞还看……”
问:创作《闯入者》时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答:这关乎我们的生活。父母的生活,自己的家庭生活,我们给孩子的生活,这一切在现在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形态?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的小家庭面对人口老龄化,会是一个什么状态?社会遇到这些新课题的时候,它会怎么面对?《闯入者》就是基于这一点来创作的。
问:所以它不像你的之前的作品那样,是关于历史和溯源的?
答:寻找这个主题我的电影里一直都有,有一种寻找可能不在于外延的东西,它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有些人生活了很长时间,经历了周遭了一些变化之后,他可能一直在寻找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一种寻找。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够往里看,看自己的本心,看自己一路走来,很多东西是这样看出来的,跟在外面去寻找自己的根是同等重要的。这部影片的寻找既是外部的也是内部的,而且比以往更强大了。
问:可以说你观看当下的一些问题,并且从过去寻找答案吗?
答:当下发生的一切不是凭空掉下来的,都是有一个过程的。比如说中国全面的拜金主义、全面的泛娱乐化,跟历史、跟一段时间的发展积累到现在,是一致的。
现在我们遇到的那些问题,中国人的价值观彻底消失,只有一个字是集体的崇拜物:钱。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中国过去来的。建国以后经济上的落后,改革开放大家追赶物质上的东西,因为中国之前,物质上的东西太贫乏了,精神上的建立又垮塌了。然后就只剩下了一个东西,就是把自己吃饱穿好,一切前提就是这个。只有钱能给人安全感。所以大家就疯狂了。就是这样。所以说回顾当时,是不是就应该很清楚地意识到,现在社会如果这样了,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理论,更高的人,让全民去注意一些,进行更平衡的发展?环境也是,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逆转了。如果当时有这样的建议,在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同时做好,不见得GDP就是一切。现在我们很清晰,但是在当时,有几个人能够很清晰?所以现在的事,一切都有它的根源。所以说,一个人,包括一个国家,在往前看和往里看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更理性化一点,这是为未来,我们还有未来,不是说地球就结束了,如果地球结束了更好,你拿到那些钱有什么用啊?灰飞烟灭。像现在,我们也要做一些理性的判断和思考,这是一个更大的主题。
问:所以说你一直在用电影来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
答:我一个人的电影没法起到那么大的作用,聊天可以脱离电影去聊自己对社会的感受,但是我觉得电影就是电影,电影能够承载的一切还是要看故事、人物跟观众的关系,能够传递多少就是多少。有什么就是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电影想把这个态度摆进去,这是没人阻止你的,你也可以不摆啊,形成另外的套路,这是大家的自由。
问:你电影的底线是什么呢?
答:底线这个词比较有趣的,每个人都处在社会现实中,处在历史变化中,一些主流的观点、时尚流行会对大家产生影响。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讨论一下,严肃地讨论一下,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底线没有。现在我们经常说“跌破底线”,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是钱和贪婪导致的。这里面也是有一些态度问题:首先,你对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现状,为了金钱完全丧失了底线你怎么看待,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模糊的底线;还有一个就是怎样面对历史,我的底线就是,如果不是客观的复原历史真相,而是因为某些原因去宣传的、不客观的,我觉得这需要很谨慎,因为一个作品会留到以后去看,以后历史一变,就不好弄了。当时欢呼的时候,后来被打倒了。这个底线也是应该守住的。
问:你有一些野心在里面吗?
答:每部片子能够做到一点就不错了。我的电影还没有到史诗性的地步,现实和史诗的关照视角是不一样的,我的视角还是个体化比较强的一点,我认为抽离了个体是很危险的,对集体、对国家都是有害的,对个体尊重起来才能给每个人建立安全感,如果抽离了自己,我们有一天都会不能自保,而且个体能承载的东西也是很多很多的。
人本身,是中国现状特别欠缺讨论的一点,我们说要建立法治社会,民主、自由,所有这些说法或者所谓价值观的讨论,都是基于人,没有人怎么进行讨论呢?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涉及到具体的人的生存的话,那就没有讨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现在中国在内容制作上,尤其是在电影制作上,这一点非常欠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除了北朝鲜和越南之外,这都不是一个问题了。
大部分电影的角色,虽说有性格有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欠缺质疑吧,在中国目前,个人和集体、个人和政治、个人和国家,好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关系都没有处理好,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人是不是具有完整的独立?这一点没有太多的认知,这个根本点欠缺,质疑性欠缺。中国人处于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下,我们应不应该去质疑它?质疑我们每个人现在的状况。生存的状况,这些东西潜移默化的都在你的血液里,中国人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是这些外部的东西让我们成为中国人,中国人的特质就是这些,当然一部电影解释不了太多东西,你有一点这个意识的话,这个作品总会透露出一点点缝隙的。
问:这部影片跟你本人有什么关系呢?
答:这方面我很小心的,我不敢说是自传,因为有环境、有背景,有这么多人的命运和故事牵连在里面。只是每一部电影跟自己精神的契合多少的问题,比如《冬春的日子》拍的就是我,是有两三个演员,但其实就是我的心态和境遇的投射,每部影片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投射,比如《闯入者》,我相信会让每个人瞬间想到自己的兄弟姐妹,老公老婆,父亲母亲,隔壁邻居,就是这样的状态。这种投射只要是关乎人的,大家一定都有共鸣。
问:您的影片会带来一些亲切感,场面调度比较能将观众带入情景,比较准。
答:我力求做到这些吧。电影对于我来说总是遗憾,我只是力求做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一切。这是制作的一个基本态度,没有这样的态度怎么过得去呢?
问:但是现在大部分影片的场面调度谈不上合格。
答:如果你的诉求不一样,比如就是个娱乐的、搞笑的,你做不到这些也没关系。
问:我看到您平时也在发微博。
答:发微博,但是发得不好,所以不发了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发得那么好,吃个苹果能转发好几千条,我挺羡慕那样的人。我也在检讨自己,或许电脑这种现代的东西不适合我玩。
有时候我也故意想要挑逗挑逗,但是我发现关注我的人没有那么多热情,好像都是一些僵尸粉,挺没意思的。不怪他们,怪我,玩不好就逃跑呗,落后于时代就落后呗,不一定样样事情都那么敏捷、那么时尚。
问:您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缓慢一点。
答:恰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珍惜的。缓慢,这个社会太快了,什么都要快,这是中国社会目前来讲我最厌恶的一点,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那些百年的传统,祖祖辈辈留下的东西,不急不躁地享用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节奏,这一切好像在中国都荡然无存了。我们从文革一出来,忽然看到世界,以为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要马上追、马上变、马上超过,我们瞬间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对传统不珍惜,对东西的经营和概念都是几天就要换,所以我们经常去“新开的地方”,新的饭馆、新的卡拉ok、新的酒吧,新的变化。这很时尚,但是从根上说,我们正在流失钙质,传统的东西就像骨头、钙质,骨头疏松了,这个不好我觉得。
问:也并不说就想赶,有时候也是出于一种赶不上的恐惧。
答:大家都在这条河流里面,想停下来都被冲走了。有时候很幸运,可以被一个浪拍到岸上,不动了,反而好。
问:您在说自己吗?
答:我觉得我愿意享受这个过程。相反,假如说我拼命走到了时尚的前面,反而会不安,会恐惧。因为今天你时尚,明天可能你就不时尚了。现在就是嘛,三两天冒出来,三两天就没有了。所以我有时候宁愿接受一些边缘化的东西,不追寻人们所谓的成功的概念。没有这些你才有理由慢下来,没有人推着你走,没有那么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被别人的眼睛盯着的那种重担,就可以慢下来,做一些事情,在时代潮流的边缘,去观看这个社会。
我对那种万众瞩目的成功,成为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人,我是会很不安的。这个没办法,我知道的,有时候你没办法控制,你失控了,就必须为了这个努力了,我觉得这样我很不安。
问:您希望生活和工作能处于自己可以控制的状态之下。
答:这是一种幸运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也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状态了。
问:实际上很难做到。
答:对,你在一个社会、这样一个环境里,你不可能处在一个真空的状态。就算是落后了、边缘了,也没有真空。你还在,只是处的位置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你不能做的事情很多,能做的事情也有。这样一个位置,可能比较适合我的性格。
人人都想象着一种成功,但是可能是性格原因,在我的概念里,成功这个词经常是暧昧的,不清晰。现在,你看机场上,大家都在教授成功学,怎么样就成功了,成功以后就怎么样了,在我这儿好像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什么叫成功,成功了就不安了。
但是你去做任何一个东西,比如做买卖、开公司、拍电影、写小说、做音乐,都要做好,做好就好了。你是干这个的,你要做好。现在钱是宗教,你挣钱了就好,所以我们以前说,你怎么做这个,你做这个臊不臊得慌啊,我们过去的社会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批评,现在不问出处了。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问:您对这方面比较在意。
答:所有人去买爱马仕、买意大利皮鞋的时候,都是图它的手工。它们是手工制作,不是流水线上出来的,在奢侈品消费上,人们都愿意回到传统和手工,最贵的汽车是用手工敲出来的,大家觉得很贵呀,买了开心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慢工出细活,有人的情感在里面。电影对我来说,也像一个手工活一样,每一部影片都是全身心打造的,不是机械化生产,上下集什么的,每一部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心打造的。除了能力问题之外,起码我是尽了心的。有可能这部好一点那部差一点,但都是一样的。在这样的概念里,你愿意买一个流水线的皮包还是买一个手工的皮包?我相信它是好的,我相信它是最昂贵、最奢侈的,跟手工皮鞋一样,是最富有的做法,不管是制作的人还是购买的人,都会因此而骄傲。一个老头子做皮鞋做一辈子,他是非常富有的。
问:您会不会担心有的人观众无法欣赏那种过于精致的东西?
答:我觉得现在观众的接受度是非常广泛的,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我相信有一部分观众,他喜欢那种类型的电影,人是很丰富的,不一样的,不是铁板一块,像我这样做的电影,我相信是很潜力,很有市场的,我对观众很信任。
问:现在中国电影处于一个商业市场的拓荒的时期,市场比较热,挣钱比较容易,这种环境对你来说更容易还是更难?
答:目前来讲,我还没有什么变化。很幸运我还能够做电影,最幸运的是我还能搞创作,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市场处于拓荒的状态,这个不假,因为中国电影刚刚开始,市场化也才短短几年,我们刚起步,能够学习的地方很多,好莱坞、韩国电影这些工业化的东西啊,有很多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拓荒是必然的,不仅是电影工业、市场在开辟,观众也在开辟,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会出现各种各样电影的可能性,就不足为怪了。
问:您的意思是说,市场成熟之后,独立电影会培养出一批自己的观众群,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
答:从市场的逻辑来说,这是必然的。因为这么多人,对吧,这么多不同的人,这么大的市场容量,这是必然的,不可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一定是违反逻辑的,一定哪里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跟市场无关。
问:所以说您是比较乐观的。
答:我对我自己比较乐观,我从来没有失望过、悲观过,我需要做的工作只跟自己有关,调整自己,寻找自己。一句大俗话,要战胜和挑战的只有自己。要超越的只有的自己。我比较享受自己所做的一切。
问:有人说现在的电影市场容不下现实主义的影片?
答:现象是有这个现象,但是从理论上的推理是不合理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关于到政策、关乎到中国社会特殊的形态。这是很大的一个议题。
问:您怎么看《小时代》那样动辄几亿票房的影片,导演却不是专业人员?
答:电影的变化非常非常的……电影导演这个职业不是一定的,我现在去做音乐家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经过这个训练,你会拍照可以当摄影师,但是导演谁都可以当。你不能说你可以当导演,别人不能当导演,不是这样的,只是中国的拓荒阶段,市场好了以后,一切可能性都可以发生,再加上电影的大门是敞开的,掘金者可以进来,一切的发生不足为奇。
问:作为一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科班出身的导演,您怎么看当时的学习时期呢?
答:我说的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的变化,过去的所谓科班,是因为中国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信息的封闭,交流的封闭,使得一个学校成了一个平台,让你能够接触到电影。这是当时的情况。你不去电影学院学习,许多先进的电影、好的资料,你是接触不到的,当时的生产量、计划经济的一切,也使得你的资质变得很重要。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所有人随时可以看到他想看的任何一部电影,不论是历史经典还是好莱坞最商业的大片,每个人都是电影的观众也是批评者,因此市场就大了,可能性也变大了。我若是在现在,也不一定非得去上电影学院,我可以看很多东西,一个聪明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掌握这门技能。电影是各部门协同的一个技能,摄影也演变了,现在的摄影只是呈现美学的方法问题了。技术上其实已经好办了,高清你可以看到,调好了就可以了,以前用胶片,没有胶片曝光的技能你就当不好摄影师。时代在变化。
问:在电影学院的学习经历给您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呢?
答:就是我当了导演。从电影学院出来,潜意识里你认为你是这个大学出来的,你是学这个专业的,所以你要努力;另外,外面的人看你是这个学校出来的,也可能认为你有这个资质。只是一种可能性。倒推到这么早以前,当然要心存感激,我出生在那个年代,我考不上大学我就完蛋了。
问:您的附中同学,刘小东大红大紫,路学长今年年初去世了,这一切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吗?
答:不是我,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切。所有的光环,不见得天天在你这儿,所有的坏事,也不可能天天跟着你,你没那么倒霉。过去一个香港的影评人,很早就跟我说:“你永远不可能是最好的,爱因斯坦现在都不见得被证明是最好的,但是你也要相信,你一定不是最坏的。”不光是附中,任何地方,任何人,都经历了这样的起起伏伏,平时哪怕是一个车间里工作的人,忽然车一个螺丝帽不合规格,被领导批评、写检查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打击,我觉得人要平均、平衡,才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状态。
问:您一直提到的都是命运,但是您怎么看偶然呢?
答:很多的偶然性,也会带有命运使然的成分,比如我读书、上电影学院,就带有那个时代人们选择道路的一种既定思路,学好了就去考清华北大,最后你做出了一个什么成就,肯定是跟你的既定目标是相一致的。这是当时的状况。现在的变化就是,你不是学电影的,但是你突然拍电影了,你不是清华北大你也开公司搞IT了,这是一个相反的命运,既定的道路改变了,但是有一点,万变不离其宗的一点,你得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得是一个有心的人,否则很多的改变在你面前都不存在。
现在微博玩的好的,给自己拍张照片晒出来,就能晒出这么大的名气,为什么呢,看起来可能是无心,但是带出来的价值观我们不讨论,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命运、偶然和每个人的个体都结合在一起了。
来源:文景L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