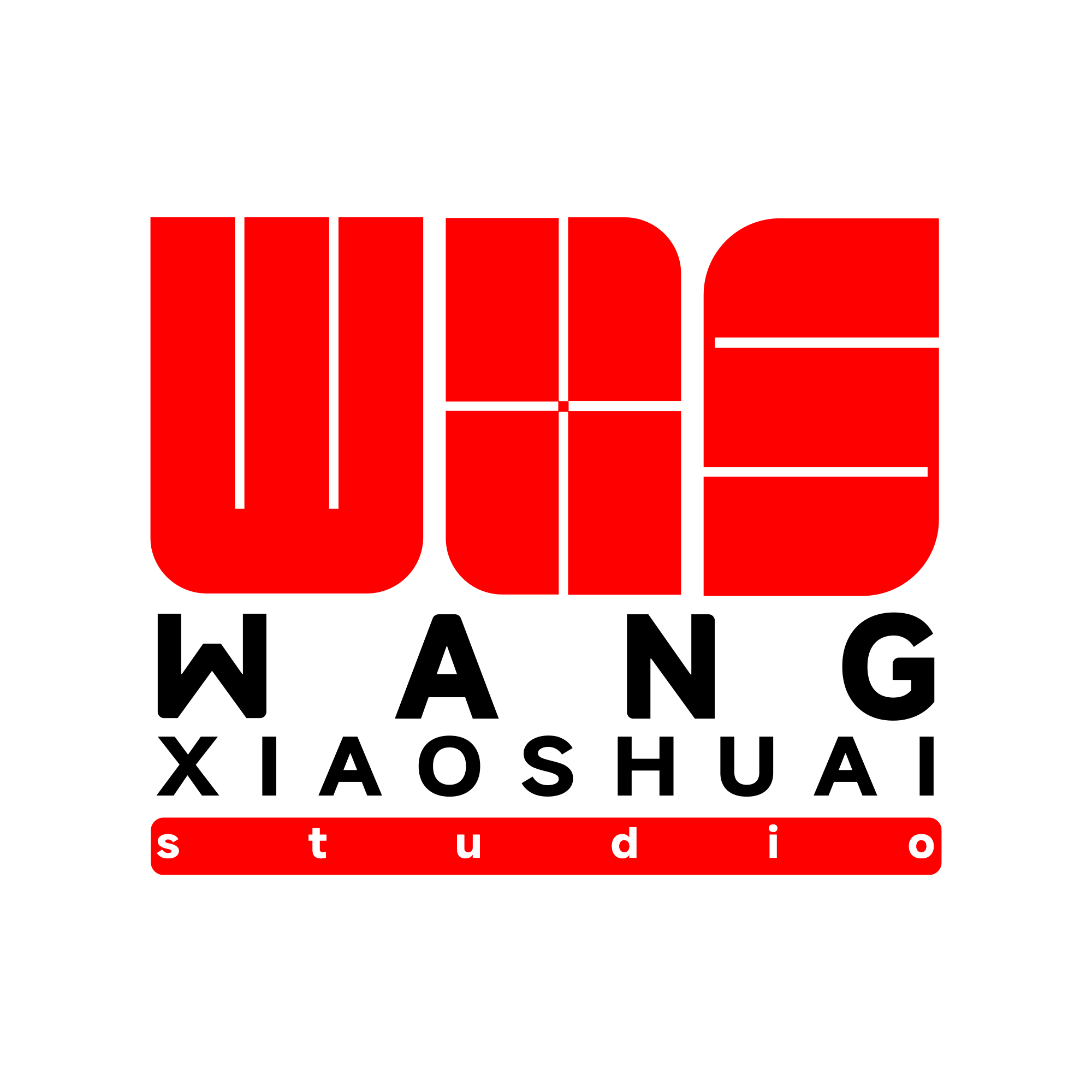受访:王小帅
访问:刘小磊
刘:您1994 年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冬春的日子》,这样算来您拍电影也差不多20 年了。您不算一个特别高产的导演,基本每两年一部。现在《日照重庆》也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回过头来看,您是否还能想起来最开始做《冬春的日子》时的创作状态?
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去了福建电影制片厂,1993 年回到北京。现在想想那时候确实有点少年轻狂,总觉得我们85 班是继78 班之后最完整的本科招生,国家应该很重视我们,又毕业好几年了,就想一定要赶快拍东西,特别着急。当时还是计划经济的环境,也没有现在的院线或者市场,就是到处去联系看能卖多少拷贝,一个拷贝1 万块,有些电影出来一个拷贝卖不出去,有些能卖十个拷贝,如果能够卖出100 个,在当时就不得了了。一部影片基本的成本差不多是80 万元,那时就经常听到一些导演谈去拉钱的经历,谈一些根本跟电影创作无关的事情。当时突然就觉得做电影特别难,总有一个东西在卡着你,要搞人际关系,要处理很复杂的外围事务,跟戏班子一样,根本不是在单纯做电影。有时候满腔热忱地跟人家谈一个项目,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这个事不知为什么就慢慢淡漠了。可能又过了半年,发现人家已经拍上了,当时年纪小,夹在里面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很着急。因为在我原来的想象中,拍电影是艺术创作,是很单纯的,不应该那么复杂。那个时候大家拿钱都很少,1994 年时吴子牛在福建厂拍一个戏,导演费4 万块钱,我们就觉得是天文数字。场记和副导演,整部戏下来连补助才1500 块钱,我们在福建厂一个月工资才200 多元。那时候第五代已经出来了,我总觉得他们的电影好是好,但是不是电影本体的东西。我如果拍电影一定和他们不一样,具体哪里会不一样也不知道,就想赶快拍出一个东西让大家看看的确是不一样的角度和出发点。因为在电影学院看了很多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这些电影对我们直观的影响其实并不大,只是让我们知道电影也可以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让我们明白其实拍电影很简单,不一定非要有战争和历史,甚至不用灯光,扛起机器就可以上街拍。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到中国,电影就非弄得那么复杂。分到福建厂之前,我招呼了一些人拿个机器上街就拍,也不知道要拍什么,单纯是迷恋电影拍摄现场的感觉,拍完就在小酒馆里瞎侃。到了第二天再用B P 机呼人都呼不到了,拍摄也就流产了。所以等到准备拍《冬春的日子》,我就打定主意至少要坚持拍完,每天大家聚在一起,把这个原始的想法变成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拍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接触演员的几率几乎为零,摄影师是刘杰,也是电影学院毕业的。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演员,也不知道怎么用他,就把他当模特一样,作为一个投射,让这个模特的心情和整个状态能够跟自己搭上钩就可以了。至于拍摄题材,就是把镜头对准我们最熟悉的事情,从最熟悉的感受出发,因为我们也没有能力把镜头的视角探出去。当时最熟悉的感受就是毕业后的迷茫、没有安全感。在平时这种迷茫呈现出的就是喃喃自语的状态,当情绪积攒到一个高潮点上就变得很张扬。所以就想在电影中呈现这种困惑和情感,表现一种直接的精神状态。以前的电影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的但是我觉得这应该也叫电影,就好像拿画纸画的就是画,那拿胶片拍的肯定就叫电影,只是这个电影的样子跟别人的不一样,讲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表现精神的恐慌和迷茫。我坚信如果它成为一个电影,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在那个阶段是主张抛弃技术的,那时很多同学
在学校是迷恋技术的,可是我觉得以我们当时的条件根本看不到技术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如果你用很好的技术传递的是老的观念,那电影拍出来都是一样的。我就想我要解决的是我们要拍什么内容,发出的声音和视角是什么,所以我把技术扔了很多年,还原电影本来的质朴,《冬春的日子》最早就是从这么一个原始的概念出来的。
刘:现在回过头来看《冬春的日子》,最重要的意义确实是突破了一种电影创作的模式,当时第四代导演拍的是故事性比较强的电影,第五代导演开始进行镜头语言的反叛和革新,像不平衡构图等等。《冬春的日子》在拍出来时,第五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比较顶峰的状态,包括像《活着》、《霸王别姬》、《篮风筝》都在很重要的国际电影节获了大奖。那么您拍《冬春的日子》时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的出路是什么?
王:那个时候张艺谋、陈凯歌都已经在柏林、戛纳拿过奖了,但是对于这些大的电影节,我们也只是知道而已,觉得跟自己距离特别远,关系不大。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市场”,所以还是希望电影拍完能拿到一个指标。因为1993 年的时候,张元准备拍《妈妈》,我做编剧,分镜头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没有钱。田壮壮导演突然找到我,让我帮他拍另一个戏,我就去了。后来因为深圳的投资人迟迟没有进展,反而是《妈妈》那部戏的投资落实了,我又回来拍这部戏。《妈妈》拍完之后拿到了西影厂的指标,所以就安全了。《冬春的日子》本来也想走这个路线,拍完之后我们拿到电影局去审查,看完之后电影局说还行,可以给我找一个指标,就跟福建厂联系。但是福建厂不同意,争取了半天也没有成功,所以最后不仅没指标,还被通报批评。那时候我想了很久,就只剩下一条路还没有走,就是香港评论家舒琪。我在电影学院上课时,认识一个老师,是英国著名的评论家,他跟舒琪关系很好,我毕业参加香港影展时,他介绍我们认识。如果我想跟国外电影节有点什么联系的话,舒琪是我唯一的途径。他跟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是最熟的,所以我就把《冬春的日子》拿给他看。当时是在一个丹麦大使的家里,租了一台很笨的放映机,在人家客厅里放的这部片子。他们看完之后的反应跟我的预期是一致的,就是觉得这些黑白影像带出的信息是非常新鲜的,让他们耳目一新,所以就说可以试一试走一下电影节。最开始是说去香港国际电影节,虽然受了打击,但是还是觉得能参加电影节已经很了不起了,然后继续准备去温哥华电影节。但是因为护照问题,温哥华没去成。到第二年的四月去了鹿特丹电影节,那是第一次真正带着片子出国了,到了鹿特丹发现反响还不错,因为鹿特丹和柏林电影节一直有着某些联系,所以鹿特丹参加完就没回国,直接去了柏林,当时,对我来说是很懵的,因为当年柏林戛纳威尼斯对我们来说想都不敢想。一去到了柏林,第一次直面这么大的电影节,我才知道这个门原来也是对我敞开的。
刘:在您的创作中,感觉《扁担姑娘》是一个分水岭,开始去注重电影的可看性了,题材也更具有社会化意义上的敏感度和关注点了,不再是一种个人情绪上的迷茫或者喃喃自语了。从《冬春的日子》经历了《极度寒冷》,再过渡到《扁担姑娘》,是创作观念发生了变化,还是创作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王:拍《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时,如果讲创作状态,那就是我们总觉得自己不是拍电影的,虽然拿着机器,抱着胶片,但是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我要确定一种用电影说话的风格,我就是要这么说话,跟其他导演的说话方式都不一样。而且我也说不了远的事情,只能说我身边的、我最了解、距离我最近的事情。而且当时创作环境真的很艰难,有时候胶片拍了但是没保管好丢了;有时候拍出来了发现胶片印反了、接不上。我就把能接上的接上,继续拍。带着一种赌气的情绪吧,就是别人越不让我拍,我越要拍,我就非要坚持下去。当时跟我差不多毕业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态度。为什么会有“第六代”的这个说法,我个人对“第六代”这个称呼其实是不排斥的,因为当时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一群人在努力奋斗,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等到拍《扁担姑娘》,拍摄条件确实发生了变化,这个是必然的。当你拍出一个样品出来,并且获得了一些声音的时候,自然会有人针对你的作品进行跟进。我当时就想,不管条件发生再大的变化,我基本的创作初衷是不能变的。当时就有电影厂和投资人找到我说,他们觉得我能拍,但是不能这样拍,不能说我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我知道他们的诉求在哪里,但是我又很担心跟他们一合作,我坚持的原始诉求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影又变回了以前中国电影的样子,这个是我很不愿意的。但是不愿意也要走出这一步。当时有一个北京金蝶影视公司,挂靠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是最早的民营资本开始和电影厂合作,通过影视公司的名义挂靠电影厂。金蝶就找到我,说可以合作,但是我不能再拍自己的事情了。所以我就提出一个框架,因为我在武汉生活过,当时码头、扁担和民工是武汉非常典型的三个社会点,我就说是否可以拍这么一个故事,我亲眼见过,但是又不是我自己的事情。他们就觉得这个框架可以接受,至少不再说租房啊、吃不上饭啊、迷茫啊这些问题了。我想如果要拍这么一部电影,我可以把自己的态度、观点通过一个共同判断社会问题的角度表达出来,也是很好的。所以就先做剧本,因为投资人要看剧本的,以前两部电影都是靠人家资助,比如舒琪、侯孝贤等等都是拿一卷钱给我,不算是投资,就是很信任我,让我去拍,所以我拍起来也就没有另一方的牵制。拍摄流程也很简陋,有时候没有剧本,我脑子中大概想一下,第二天就拍了,现在只有王家卫才能做到这样。到了《扁担姑娘》有投资人了,制作团队也一下子从原来七八个人增加到了七八十个人。所以遇到的题也开始是正规电影拍摄遇到的问题了,投资和审查各方面的问题也都进来了。但是我想不可能永远是我拍《冬春的日子》的状态,所以还是很用心地去磨合和配合,一直到《十七岁单车》整个拍摄流程就逐渐完善了。
刘:从《扁担姑娘》到《十七岁单车》再到后来的《二弟》、《青红》、《左右》等等,已经有很强的主题连贯性在里面了,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王小帅的作品。但是中间为什么加了一个《梦幻田园》?这好像是你创作中比较割裂性的一部作品?
王:《梦幻田园》就相当于张艺谋拍的《代号美洲豹》、陈凯歌拍的《温柔杀手》。每次想到《梦幻田园》,我都这样安慰自己。我们这一代人,贾樟柯是最幸福、最完整的,他1997 年开始拍长片就有自己的公司,而且是跟香港人合作,这个合作人也是很积极融入到大陆生存环境中的,所以他的作品就比较稳定,有连贯性。但我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极度寒冷》1994 年就拍完了,但是拍完真是一分钱都没有了,还在香港丢了好多胶片,就只能搁那里了。1995 年底拍摄完《扁担姑娘》送去审查,发现审查没通过。这一下把所有人都打蒙了,包括韩三平。本来都已经打算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了,因为审查没过,也去不了了。我当时就跑去了荷兰,组委会就问我“没通过怎么办?你还有什么片子?”我突然想起《极度寒冷》拍完还一直扔在那里没做呢。当时鹿特丹电影节组委会就给了我一点钱,让我赶紧做后期。其实我一路走过来,遗憾真是很多。当时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人把所有的东西从香港寄过来,一查发现素材丢了很多,而且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剪片子,已经放下两三年了,也忘得差不多了,要重新看素材、做音乐、翻译字幕,每天弄到凌晨4 点多,音乐还得找外国人沟通,声音也得找外国人,把那个老外逼得快疯了。赶到电影节放映当天,才做了一盘热乎乎的拷贝送过去,但是很粗糙,因为真是没有时间再去检查第二遍、第三遍了。一直到1999 年,有一天北影厂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赶紧回来重新剪《扁担姑娘》,各方面关系都疏通好了。我那时候在纽约,而且没有钱,我说我真是回不来,而且我说这个片子其实再剪也是这个样子,万变不离其宗。最后他们就说你不回来,我们就给你下剪刀了。所以《扁担姑娘》最后的剪辑版不是我做的。北影厂那个时候刚刚变成企业公司制,也有青年导演计划,我就是那个青年导演计划范畴的,《扁担姑娘》来回折腾了三年,其实我对他们是很感激的,觉得很难为他们。金蝶影视公司那时候已经不知去向了。因为觉得欠了他们很大的人情,所以北影厂提出让我再拍一部审查比较好通过的电影。我说“我一出手必伤人,那你们看应该怎么弄这个剧本,我来拍就好了”。所以《梦幻田园》本身的剧本是很黑色幽默的,但是按照这个剧本拍肯定还是通不过,于是就找来了郭晓橹,还找了文学策划,完全把剧本交给他们。我告诉自己电影都是这么合作,有编剧和文学策划,我应该试试看所谓的正常合作的。那个夏天是北京最热的一个夏天,也出了太多的事情。拍完之后我就知道完蛋了,最好别看,至少人情还掉了。结果果然是这样的,厂里一看很高兴,然后送电影局,很快就传回来消息说拍得不错,通过了,我心里说“完蛋了”。给我印象很深的那天开完会出来,在北影厂上厕所,韩三平说“小子,这回你给我长脸了,送去的几个片子我都顶着挨骂,就你这个片子把我表扬了,以后接着拍。”但是最终因为各种原因,没发行出去,海报也没有做,碟也没有出,我本人还是很高兴的,这部电影再次告诉我一个导演是不能失去他的主控力的。
刘:您大部分作品的精神气质还是很一致的,如果说贾樟柯的作品是电影美学观念的一
致的话,您的作品其实是社会焦点模式的一致性。您在取材上比较能够抓住整个时代的敏感点,《扁担姑娘》和《十七岁单车》都是因为民工潮,农村的小孩大量到城市打工;《二弟》是很多人想出国导致偷渡客的增多;《青红》是知青时代的子女已经长大了;《左右》转向关注中产阶级,这些都是跟时代的敏感点契合在一起的,这是您创作到目前为止的一个核心焦点吗?
王:我的电影确实是原创作品。中国摇滚讲究原创的精神,从我的理解上,原创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梦幻田园》原创权给了别人,别人再反过来让我拍的东西就不是我的了,因为原发点不在我这里,就会距离我很远。这也是为什么我拍电影不可能有长远性的计划,不是说这个片子拍完后,后面有几个电影的剧本在等着我。因为伴随我心理年龄和经验的变化,兴趣点也在发生变化,创作的路子也会因此改变。往往我写了三个剧本,做出来一个后,后两个剧本过了一年半、两年后就变味了,不是我想要的了,所以创作的这个点子始终只能在现
阶段和当下,符合我的心智、心态、经验和我关注的社会点。这里面的核心更像是一种精神流浪,就是精神的变异始终统治着电影的精神。比如说像《日照重庆》,只能是我在做父亲以后完成的作品,因为人的心态在年龄跨越到40 岁以后,有了小孩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刘:这就慢慢集中到您的创作态度的问题。您可以说您的作品不是有计划性的创作,但是
对于观众来讲,都知道王小帅的作品持之以恒保留的是什么,观众的心理期待是在一个框架
当中的。有一个问题您最近一直在强调,就是“得奖和票房都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
您呼吁“要给电影留一些尊严”。那么您认为衡量一部电影真正的标准是什么?所谓的“尊严”具体是指什么?
王:首先,商业认定、票房回收,在现有的大环境中一定不是衡量一部作品好坏的标准。因
为在现有的大环境中,是有一个观众群体喜欢所谓严肃电影的,但是因为环境问题,我们没有办法从这部分观众群体中得到相应的投资回报。所以从第五代之后,中国电影市场是再一次断裂的,或者说是又一次“走偏”。因为现在的市场环境完全受美国和港台的影响,当资本进入的时候,是否赚钱成为很重要的砝码,并且慢慢地形成一种循环。因此这种循环只是单纯从资本角度来看的,票房好坏也就不能成为真正衡量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第五代的时期,甚至更早的,中国三十年代的电影,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保留下来的文化价值,这样的电影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有尊严的,有灵魂的,这应该是做一部电影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就是关于得奖问题。这是个人心态的变化,一路做电影,我的身体和精力是累的,但是我的内心和精神是愉快、富有的。人永远要战胜的就是自己,对于我来讲,目前出现的问题就是“得奖”。是否得奖现在成为了大家对我进行框定的一个标准,也慢慢成为是否被肯定和如何被评判的标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危险的、不好的。如果我保持现在做电影的方式,保持我精神的独立性,那么现在只有这一点点出路能让我的电影流通。但是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会碰到“是否得奖”这个问题。其实《青红》和《左右》之后,我一直都在讲,得奖是可遇不可求的,我现在只想把每一部电影都做好、做踏实,让自己的条件、环境各
方面都变得更成熟,至于是否得奖,真的不重要。
刘:但是在电影节获奖是否跟海外版权卖得好坏直接挂钩?
王:对我现在的电影来讲,海外代理公司已经在持续做了,他们有自己的操作流程,跟是否
得奖无关,如果得奖了无非是增加一个砝码而已。比如《日照重庆》的海外发行已经展开了即使不去任何电影节,他们的工作也会持续做下去。至于对中国电影市场的运营来说,咱们的市场基本态势已经形成了,是否得奖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贾樟柯这么多电影,也就是《三峡好人》卖得好一点,其他也都差不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得奖的心理压力反而更大,本来票房就是一个压力,得奖又成为一个压力,就失去了做电影最原初的单纯。对我而言,现在能持之以恒地按照自己的创作思路走是最可遇不可求的,因为你需要和投资人沟通、和周边的合作人沟通,这么多年,我还能紧紧抓住自己觉得最可贵的东西,回到电影本身做电影,对我而言是意义最大的。
刘:那么把控电影节的风向与您创作的出发点是完全无关的吗?
王:这么多年了,电影节的风向把控不了、也猜想不到。一个好的电影节是反过来的,它会去关注艺术家,从当年的很多作品中发现一些共同点,再反过来梳理电影节的主题。所以好的电影节是观察艺术家、尊重艺术家的。比如这一届电影节中有一些片子是拍同性恋题材的,有一些是拍乱伦或者虐待的,他会觉得这是目前一些艺术家的创作心态,好像是在探讨关于人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变成这届戛纳电影节的一个主题思考。所以作为导演来说,你就不可能去预测一个电影节的风向,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走,有的时候契合,有的时候不契合,这些都没有关系。这其实跟所谓的票房电影是一样的,尽量避免不要去看外面。但是现在中国电影几乎是没有原创的,都在看外面,因此就容易跟风和模仿,也因此越来越少的人关注创作的根本,连对艺术家起码的尊重都没有了。
刘:我们再回到票房的问题,比如2009 年,从“国庆献礼月”到“贺岁档”,上映的电影很多,整个中国电影票房大概30 多亿,其中《阿凡达》是十几亿,剩下所有的国产电影大概是几十部平分不到十几亿的票房。现在有国产电影票房号召力的集中在几个导演身上,比如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香港导演北上的越来越多,商业片的氛围越来越浓,中国电影市场中充斥的国产大片几乎全部是打打杀杀的古装片,所以我们说这种市场环境肯定是不健康的。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如今进入到中国电影市场的好莱坞大片都是诸如《阿凡达》之流了,大部分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年纪都快接近60 岁,现在应该是您这一代人撑起整个中国电影大旗的时候了,面对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您认为应该怎么来平衡?
王:这里存在一个分工的问题。当中国电影市场产业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因为国家政策开始逐步宽松了,市场开始开放了,就需要一批优秀的导演把这种转型贯彻下去,把这个电影产业慢慢做起来,变成中流砥柱,变成主流的支撑。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的整个产业储备还不够,之所以是觉得由几个导演来做票房支撑,就是因为别的储备跟不上来。但是往后看,未来产业的储备、商业片的储备会越来越多,从事这个产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因为商业的模式始终是一个快餐文化模式,当硬件都齐全了,工业储备量就会很快,等储备到一个阶段就会产生一个机制。当这个机制逐渐成熟,被建立起来,另外一个渠道可能也就会逐渐被建立起来了,也就是不以快餐商业文化为模式的渠道,这个渠道也需要建立自己的一个环境和市场模式,也应该有科学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也有自己的票房机制。也许我样讲有些自私,但是我是将自己归属到第二个渠道中的,这也就是我说的分工问题。只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渠道还没有成熟和完善,也导致第二个渠道迟迟不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建立起来。比如硬件问题、电影院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看电影的观众群就不集中,他们就越来越
被网络、3G 给覆盖、被湮没。但是我相信,这些问题都会随着机制的逐步完善而慢慢解决,只是时间问题。
刘:您现在整个创作的平衡点其实已经找到了,像您的电影中其实也会用到明星,甚至会自己培养明星,但是同时又在坚守您想要的艺术品质,您作为导演的主控力也没有丧失。
王:对,这是通过积累形成的经验,但是我作为导演的主导力是绝对不能变的。比如《日照重庆》跟范冰冰和王学圻老师合作,他们跟我的交流也是把我真正放在一个导演的位置上,他们是明星,但是首先是一个演员,只要导演的要求是合理的,演员也会非常的配合,因为演员其实是根据角色来的,没有固定的模式。这样将来的路子也就会走得更宽一点。
刘:《日照重庆》的投资是您所有电影中最大的吗?大概什么时候能跟观众见面?
王:对,应该是严肃电影中的大片了。现在这部电影制作已经完成了,发行还要看档期的问题。我比较希望在淡季。《阿凡达》的出现让很多电影院线的管理人员都在想,一年12 个月应该怎么拉开基本的档期,把影片的集中点稀释。以后每年的片子会越来越多,500 部甚至600 部,那么均衡档期的问题就越来越重要。像美国电影也有重要的档期,按照咱们的观念,可能认为他们最大的档期是圣诞节,但是对他们来讲,相反圣诞节的片子是最危险的,因为美国人的假期观念很强,一到假期可能就举家旅游去了,也就跟电影完全没有关系了。所以档期问题可能是未来中国电影院线的管理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刘:谢谢小帅导演,也希望早日在影院中看到您的《日照重庆》。
王:谢谢。
来源:《电影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