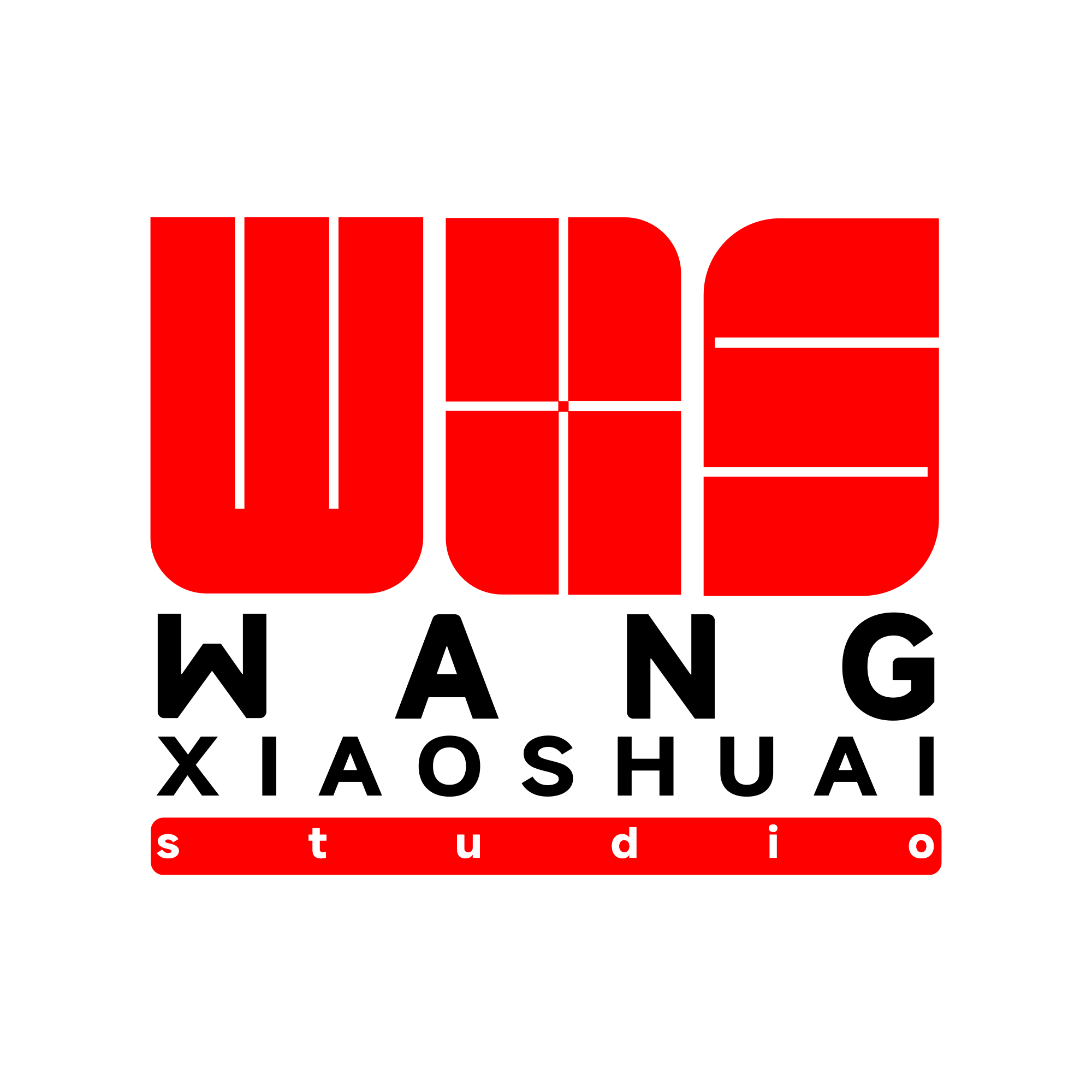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我憋不住了!”——青红
青红是王小帅电影里最闪耀的角色之一,这是她在电影结尾最惊人的一句台词。这场戏,那个喜欢青红的工人以强奸罪被枪毙,三声枪响回荡在天地之间,父亲不放心女儿青红独自上下学,天天接送她。一日,在回家路上,青红说:“我憋不住了!”青红这样说其实是有双重意义的指向,身体与心理的“憋不住了”都被打通,你会发现,青红这样一个人其实是很震撼的,她跟王小帅诸多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在用青春最简单的言语和动作凸显自己的压抑并寻求解脱。
提到这些是因为在采访小帅过程,发现小帅逐渐激动起来的语言和动作,在我提到国内当前的电影和文化环境,提到当前电影圈的一些激动和一些压抑时,小帅似乎也在说:“我憋不住了!”就好像那一刻,他是青红上身,要有一番话要急于表达,结果又显得冷静克制道此而言他物。那种暧昧不明却其实深藏内里的表达,总有些像一位超然于当前局面躲开于现世纷争的旁观者。
年初《白日焰火》国外获奖,票房走高,王小帅感到这是一种欣慰,不好用“文艺”或者“商业”去定位这部电影,但片子难得,市场也越来越包容。然而他听说有位业界老总表示现在都想拍“文艺片”的时候,又觉惊讶,“这又是一轮新问题的开始。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些热情,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和制度,这才是为观众负责。”
80年代人人推崇电影艺术化,王小帅却想让自己的电影走市场化路线,后来都在追求大片化,他没有去拍大片,当前“文艺片”三字成为时髦,他又提出了质疑。因为他说自己最讨厌一边倒的“人云亦云”。当然,他不是非得要做一个反叛者,可是有时候,他就是不随大流,忍不住向这个社会的伤疤狠狠地杀一刀,也正是因为可以杀出这一刀,他才得以始终坚持,在这个世界里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再回到青红的身上,我想,可能小帅不仅仅只是想说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直在用青红这样的人来讲他自己的记忆。
“我憋不住了”的暗语或许是“我终究还是憋住了”。
当下: 华语片的一种可能
“船到桥头自会直啊,国家现在都在变,总归会有办法的。”
——《青红》
《文周》:同是作为柏林电影节走出来的导演,您对《白日焰火》怎么解读?
王小帅:我也一直很关心它上映以后的效果,就这头一个星期来看非常好,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们大的环境也到这个时候了,不是说获奖的片子必然没有票房,这样一个魔咒需要大家来推动、改变,《白日焰火》这部片子的市场成绩也给了大家一个鼓舞,同时也祝贺他拿到这么好的成绩,导演、投资人和创作班子能做到这样,真是非常难得,特别是在中国电影的现状下。
《文周》:《白日焰火》这样的电影对中国类型片的开拓有什么意义?
王小帅:首先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单单简单归纳为某一种类型片,当然我了解这部电影的出发点是以一部类型片去看的,警匪,谋杀,它具备许多观众期待的元素,因为电影很奇怪,色情暴力凶杀,警匪悬疑,这些都是观众爱看的类型。但它的叙事模式,不见得是类型片的叙事模式,按道理说警匪凶杀,他应该有类型片基本的叙事模式,但是它不完全,它又具备了一点点所谓的艺术感。它得这样一个奖,是两边都跨着,所以它带出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就像你说的,是类型片的改观,开拓,我不好下这样的结论,究竟它是哪个属性更重,比方说我更愿意看到,假如它在柏林拿了奖,是艺术类型的探索走得更远,而同时在市场得到认可,更让人安慰。
《文周》:网上看到新片《闯入者》的片段中也包含悬疑凶杀的元素,关于这些元素,您是怎么想的?
王小帅:这个片子里面,它所需要的比如说凶杀或者说隐藏的危机都是和故事的线索需要相结合的,不是说以一个商业的标签要贴上去,它是含在故事剧情里的,含在结构里的,所以我也无法给这个片子定一个性,无法说他是一个悬疑片。相当于《白日焰火》也是,它有很多元素,但是它的叙事是反很多这个元素该有的东西的,那我这个也是一样,很多的叙述表达是有想法,是有可能观众需要跟进去,需要参与进去看,多一些自己的理解去建构这部电影,所以这个电影的完成需要观众参与,《白日焰火》也是一样,它的侦破形态不是随着起起伏伏侦破完,观众需要猜,需要理解,需要根据很多留白去看的。
《文周》:您在电影市场里处在一个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到现在市场环境好起来,像对《白日焰火》这样的片子更包容的时候,自己还甘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吗?
王小帅:我觉得我的电影,像我说的,是一部一部在做,但是我说的很多话让人不中听啦,这个是我的问题,可能我自己也把自己边缘化了吧,但是我恰恰是希望这种电影能被大家接受,所以我自己个人是不是被边缘化、能不能被别人接受,这是我考虑范围之外的事情。像《白日焰火》这样类型的电影要能够被市场关注,得有办法——不光是纯粹市场化的方法,来帮助这些电影。
环境:给不同的电影留出更多空间
4月9日,2013年度中国导演协会奖落幕,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奖项空缺,双双空缺的决定并不容易做,王小帅认为,这是导演们共同的声音和立场,也是对中国电影的责任和期待。导演协会奖不应被过于市场化的因素左右,王小帅也由此谈到,整个环境都需要给不同类型的电影更多机会和包容。
《文周》:您最近在做导演协会奖的评委,今年参评电影的情况怎么样?
王小帅:这次能报名的影片数量不多,都是一些年轻导演的电影,像赵薇的,整个的环境使得这次刚刚拍电影的导演就很突出,这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很多原来新导演的可能性变为年度导演的可能性,这也可能是今年的特点,明年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个人是特别希望有几部并没有市场放映的,观众可能不知道的,能够受到重视,我们也都尽量把他们拿进来放到这20部里面来,后来提名的5部,有的还在,有的就不在了,这是挺可惜的,这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在协会的表彰倾向性上,不要被过于市场化的因素来左右。
《文周》:那像美国,是不是比较市场化倾向的呢?
王小帅:我们中国电影学美国的这几十年,恰恰就是美国电影本身的文化形态上走了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说因为它市场的无限扩大化,然后高科技进来之后,给电影形成视听语言的震撼,所以更多地走向了这样一种层面。甚至美国电影有几年还是一些超级大片得奥斯卡。但是美国有一个好处,因为它体量太大了,它的政策是自由的,所以有很多好的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在那儿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可能有一天奥斯卡评奖没片子,傻了,再评给什么第三集、第四集,就没有原创,没有意义了,那这个时候,有些这样的影片就还会脱颖而出。比如说那年的柯恩兄弟《老无所依》,柯恩兄弟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奥斯卡从来不带他玩儿,结果奥斯卡自己发现自己续集拍糟了,说出去全世界要笑话,柯恩兄弟《老无所依》赶紧的,它是随时有这个储备的。
其实中国至少不是完全没有艺术片、独立片的发展空间,只是要重视,要保护和呵护这一切。现在,在急速发展的市场里面,跟美国一样,都忽略了这个方面,不像80、90年代初期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种振奋,文化形态、电影形态这种新格局的突破,现在都不需要了,现在就是挣钱吧,谁把钱挣得着,谁就是座上宾这样的,相对美国和中国,大家都要警惕吧。
《文周》:您怎么看待中国观众对电影的审美趣味?
王小帅:电影的观众全世界都是慢慢地倾向于年轻化,现在我们电影院建设也倾向于高档,快销化,所以也很适合年轻人,现在是80,90,00后慢慢主导观众人群,而这代人的成长,又是和现代社会的电子产品啊、快餐文化相伴的,所以这样的一种趋势也是无奈的。不能说观众不对,从电影商业化角度去迎合去判断什么样的观影人群的审美趋势,是市场化,没法避免。只是说在欧美的话有一个观影传统,年轻人看年轻人的,中年老年也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选择,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没能有好的方法让不同诉求的人都有他可去的地方。
《文周》:是分级制度吗?
王小帅:至少是从市场的构建上,把电影类型,文化属性,商品属性,不同看待,更政策性概念的东西都考虑进来,电影不光是纯商品的 ,需要考虑它的文化特性,当然从根源上说,分级一定是让电影的创作更加丰富的,在一个可见标准下发挥,会有更多有意思的电影,但是同时这个源头如果开开,下游,市场环境也得有容纳不同电影的空间,这才是从上到下都健康。

时代: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我不记得当时,是否听到了远处刑场的枪声,但是随后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却始终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11》
成长的背景不可能被选择和重来,但王小帅发现至少还有电影,可以让他一次次回到似是故乡又已面目全改的贵州,释放记忆中根植的表达诉求,也一次次把自己摆在上层与底层之外,摆在时空之外,看时代和历史如何在变迁中给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打上烙印。
《文周》:是因为剖析少所以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还是成长和时代的烙印使然?
王小帅:我是一个一旦人云亦云我就要质疑的一个人,可能从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在文革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闹运动的时候还能独立思考的一个人,那么这些对我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当人们被一种疯狂驱动,都是一种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相反,这是一种威胁。如果现在电影环境还是像80年代是一种探索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凡是出一部片子是娱乐的,就会被批评的,所有文章都要找艺术的、探索的,你可以为此查证。当时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不对了,我觉得所有都在搞探索艺术的,那么我可能去做市场,因为确实我们拍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市场化的,我们没有介入这个体制,拍出来是直接要发行,直接要去做市场。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一个大众流行趋势的环境下,希望自己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文周》:关于电影,您那一代生的人有怎样的集体记忆呢?这些电影记忆对您有什么影响?
王小帅:就是娱乐,那种电影记忆就是玩,我们没有别的嘛,所以说是追逐,是崇拜吧,我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把电影里编造的故事我们在生活中去演绎。像《侦察兵》《渡江侦察记》,在小时候对这样电影是极端感兴趣的,我们统称打仗的电影,正邪特别清晰,在我们那个智力上特别容易接受。回过头看,像这样打仗的、正邪非常清晰的电影,过去就过去了,等到你慢慢从孩童时期初级的、纯粹观众角度看打仗,看热闹这么一种心态里走出来后,就进入一种相对职业的状态了。为了去拍一个电影去为观众服务,这是最基本的,那么我们现在慢慢也在脱离这样一个标准。
《文周》:您对生活的思考反映到电影中是很知识分子化的,对这种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王小帅:我最近也看到这个说法,因为我自己无法评判自己,我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是什么位置。我位置也很复杂,因为家庭环境背景是工人,而像我父亲搞戏剧,我是从小地方出来,但是我不是真正从农村或小县城走出来的。我又上了学,又从科班出来,那我所呈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话,不是很清晰,但是有一点,我可能是介于那种完全的底层,和所谓的完全的时尚上流之间。
《文周》:那么这种成长历程一直对您影响非常之深吗?
王小帅: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现在人格的形成,都是和过去相关联的,甚至有的人说三岁看到老,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只不过是看有多少人去感知它,有多少人是不感知它。我认识有的人把小时候全忘了,那么他可能下意识选择屏蔽了,对我,我觉得它依然还在,时不时蹦出来。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庭、成长环境、受教育背景跟亲戚朋友,所有这些关系都在影响你的人格成长,同时也会对你的表达带来潜意识的一个源泉。
《文周》:大环境之外,一些小细节您也非常清晰地还原,比如《青红》里一家人吃西南特色鱼腥草,这是有意识的吗?
王小帅:其实那么多年,一定有些细节是已经遗忘的,但总会有几个是在那儿,可能是后来的生活不停提到,所以它慢慢被筛选出来。因为记忆有时候会很强,也会很糊涂,该忘的忘,你这个片段的截取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是很深的学问,什么东西让你印象很深刻,什么东西别人认为对你很深刻,但是你却忘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来说,还是记得很多细节,痛苦也就在这些点上,因为中国迅速变化,当细节只是停留在记忆里,无法去复原它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细节的清晰只是自己能享受,但是在电影中去呈现,我觉得特别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呈现也是下意识的,它就在那儿,不是特别刻意的,能做就做出来,不能做也没有办法。
理智:“像一把刀子去剖析这个社会的太少”
“我跟你说呀,这城里头的人坏得很,越是给你钱的时候越是挑你,左挑右挑。”
——《十七岁的单车》
《文周》:您拍了很多青春相关的电影,而《闯入者》又是怎样一种情绪呢?
王小帅: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当下的。在当下的中国,有很多人在提出一些反思,就是我们中国走到现在,这个发展跟过去是有很多勾连的,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不管从个人也好从社会形态也好,对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个是我们以前不思考的,我们以前要么是回到文革时期说文革,要么是回到过去时期说过去,现在好像就是要忘记过去向前看,那么我们中间的发展过程是断裂的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形成,性格形成,社会位置的形成,难道是凭空就来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考是非常当下的。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思考,那么中国的发展其实还是盲目型的发展。
《文周》:您早期的情绪就好像是有些锋芒和愤怒的,现在您开始拍这种关注当下的片子,是出于什么而变化?
王小帅:当然我觉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创作阶段也会不一样。在早期的时候,自己也年轻,随着自己成长、学习,随着与社会接触,会有很多很多要表达的。因此那个时候的表达可能结合着一种冲动,因为没有经验,可能有的只是看到了锋芒,有的还不成熟,但是锋芒却露了出来,这个我觉得和每个人创作的过程都有关,随着年龄,随着经验的积累有关。至于我现在,那也可能是内心想的东西还在,可能只是表达会不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你隐藏得更深,有的时候你揭露得更狠,有的时候对你内心更震撼,可能我用的方法更直接,但是却更加不易让人察觉到它的锋芒,这些都是可能的变化。
《文周》:还会拍青春片吗?还是说青春片只是它的一种形式,思想的东西还是不会变的?
王小帅:对,我觉得可能在片种类型上的简单划分已经不能够完完全全地安插在像我们这样导演的身上。像这个东西往往是在好莱坞的结构里容易发生,因为好莱坞市场的结构是非常细分化的,一个剧本上来,它就有很多人来把它划分成什么类型的片子,这样他们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去策划发展。但不是像好莱坞这种成熟的制片体系下,不见得这种划分就非常精确,像《闯入者》,也跟生命成长有关系,它有可能不光是一个青春的成长,它可能涵盖更长时间的,一生的、一个中国家庭的成长史,一个家庭经历了社会变迁的历史,但它不外乎都是跟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本质有关系。
《文周》:您之前的片子里,有一些希望来的时候又破灭了,是很残酷的,为什么呢?
王小帅:我是这样,看电影也好,平时也好,我挺警惕心灵鸡汤的。现在大部分都是心灵鸡汤嘛,教育你怎么生活,怎么看待世界,怎么平复自己的心情。电影呢,也确实要给正能量,给你阐述生活的道理,正能量的电影我觉得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很多人需要它,很多人在自己苦恼的时候要看一两句心灵鸡汤来打打气,但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我觉得还是要教会别人真正地去反观自己,去直视自己的内心,甚至是去抛弃自己。自己有一个伤疤,狠狠地把它扎下去,让你真正警醒,而不是靠心灵鸡汤去掩饰,这个东西不仅关乎电影,而且关乎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心灵鸡汤,但这个社会很多问题需要一刀杀下去,哪里有伤疤就要杀向哪里,哪里有隐患就要杀向哪里,这个是疼的,包括青春也是,但是我们要直视它 ,过了这个关才能真正地成熟和强大。
《文周》:像《青红》的最后那声枪响是个非常绝望的情节,您在现在的心态之下还会这样设置情节吗?
王小帅:我觉得《青红》到那个地方不得不那样做了,甚至是更强烈,只是被一些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削弱了。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了,就应该咬牙切齿地狠狠地给一下,但也不见得,比如《我11》里面涉及的也是枪声,但是方式改变了,其实最后这个孩子他听没听见也不知道,他有个屏蔽,可能主观上就离开了,那么这个就是不同处理带给片子不同意境吧。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时期还是根据每一部电影最佳的选择去做处理。但是你所说的一些让人绝望的、残酷性的东西,可能我也知道在一个市场化的条件下,在一个流行的文化下,大家都不愿意过多地去接触、去看到。有时候我看电影也是,到最后很绝望了,我真希望它是一个幸福的结尾,我也知道,但是也可能,我是这种直面人生的,我们国家都是希望你好我好的主旋律,像一把刀子去剖析这个社会的太少太少。
《文周》:有的片子到一个点稍微用力大家都哭了,但是您在这方面是比较克制的。
王小帅:我恰恰就是反对这个的。大家可以撒狗血,让观众哭,但是可能我个人主观上,首先我觉得我是个男孩子,从小被教育不要轻易哭,没出息,然后我的成长中,特别害怕看到我亲近的人哭。如果遇到很大事情,当然悲伤是有的,哭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能用理智去认知这些事情,那种悲伤,那种互相之间的理解,也是一种表达。同时,在电影的创作与表达上,我至少希望它做到收敛一点,克制、理性一点,但是这只是我主观上的想法,他可能并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在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觉得哭才是正确表达,采访一个人,说到伤心处流泪了,镜头就要推上去,如果把他采访哭了就是采访的成功。这在西方可能正好是不需要的,他不愿意触碰到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特性,我也承认,但至少我是不希望表达这点,我也是中国人,但我的做法也有我的道理。
《文周》:但新片里面有凶杀的情节,这样还能做到情绪上收着吗?
王小帅:我觉得我们可以不要去过于追究一个词,比如说凶杀,它能带出来的都是残忍,血腥啊,让你刺激啊,其实不见得。就是说,我的电影,任何元素都要恰如其分地在叙事结构里,在人物里,来推动,它不是拎出来的一个噱头。

坚持:“你先做好自己,把自己弄踏实了”
“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总是看着别人,假设自己是生在别处,以此来构想不同于自己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一切都太晚了,你就是你。”
——《我11》
《文周》:跟许多中国的第五、第六代导演一样,您是学美术出生的,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中国电影?
王小帅:其实有很多中国导演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美术的功底,有一些专业出身的背景。只不过大家老这么说,是因为我上的是中央美院附中,美术的基础,实际上它教你的不是一个技法,不在于简单的构图、色彩,我觉得是在教会我们一个看世界、看生活的角度,可能我以前也说过,学习美术的人出来看世界,他可能学会了审丑而不是审美,他呈现的可能是美,但是美的概念可以是经过他的表达而呈现的美,而平时这种美在普通人看来它不是美。比如说夕阳西下、朝阳,可能每个人都觉得它美,这个不用说,但是有些情况就需要用更独特的眼光去发现,所以我们经常说美不是不在,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发现。
《文周》:具体反映到已有的电影里,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呢?
王小帅:我恰恰觉得在我的电影里,普通人认为的美被我削弱掉了,我是砍掉了形式上人们认为美的东西,我恰恰是用一种收敛的方式,呈现一种“非美”的电影。这样就需要更多人透过美的表象去看无美之美,就像大象无形一样。我是力争做到这个,但是不见得做得好,也不见得做得被别人理解。
《文周》:有的导演一生只拍一部电影,您的电影也是有一点偏作者电影的,您自己怎么看呢?
王小帅:其实总结下来,还真不是那么单一性的。我个人当然很羡慕一生只拍一种电影的导演,我觉得那个一直在表达,一直在说,不急不躁的,非常舒服,很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需求,这很好。但这不是一种公论,因为也有一些导演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像库布里克的每一部电影都不一样,完全意想不到,非常敬佩他把每一部电影的不同都拍到极致。还有就是有些导演是什么电影都能拍,像导演李安,好莱坞的单子能接,自己的表达他也能拍,很丰富。作为我来说,有的时候不是你主观地去选择说,“我必须这部和那部不一样”,“我各种类型的都能拍”,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我现在所处的环境轮不到你那么自由地游走于各种尝试之中,我觉得现在的现实环境,你先做好自己,把自己弄踏实了,已经很不错,很让人满意了。
《文周》:那么如果条件成熟,其实一个好的导演是能拍各种类型的?
王小帅:我觉得大家都比较迷信导演,当然导演是应该被迷信的,可是这个迷信是要分类,比方说这种类型的这个导演适合,这样的话要去努力发挥他最大的能量;有些类型不适合,这样的话你让他来,他虽然是个著名导演,愣过来不见得有好处。我要是转型做类型的话,首先有一点,就是要我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第二,还得看合作方投资方对我有没有信心。
现在比方说我们很期待侯孝贤要拍《聂隐娘》了,是个武打片,那我们就看看,如果拍得很好,那就是他什么都能拍,就跟李安一样,但是侯孝贤的风格原来是那样的,只是现在台湾市场中国(内地)市场整个文化都不需要那样的,他也很艰难,这些艰难包括蔡明亮都死扛,这些其实都挺可惜的。还比如说像小刚这种电影,不是说其他电影你能拍,这个就能拍的,北京那种土的文化、睿智的黑色幽默,加上过去有点小痞,不是你张口就能来的,都需要很强大的储备和能力。
有能力的导演千差万别,每个人都去守住,或者说做自己能做的,然后社会也能够都关照到,甚至寂寞一点都没有关系。法国大导演卡拉克斯每天坐地铁去办公室,租的房子很小,在中国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连个车都没有,其实这是不对的。
《文周》:《我11》的开头说“生命的烙印不会因为遐想而改变,唯一能做的是尊重它,并且接受它”,这句话在您身上有什么体现吗?
王小帅:这句话其实电影开头只说了一半吧,这是对更多人说的,我们是被动的,每个人的出生都是被动的,你是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社会、背景,甚至在什么样的日子,都是被动的。所以没有必要去幻想,我还是主张所有人好好地回看自己,这只是一半吧,我觉得。另外一半就是电影本身了,我的生活是这样的,那现在我要用电影去补充我的另外一半,就是去表达。我出生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环境,我自己无法改变,但是我手里是不是有着基本的东西让我去表达一些改变的愿望呢?
《文周》:这句话或这部电影,是您这么多年以来一些总结式的东西吗?
王小帅:嗯,反正我越来越觉得,对我来说,能够一步一步走,坚持一部一部做,这就是满足了,我一直以来也是这样的。往下,随着自己年龄的变化,还能够坚持一部一部做,已经很满足了。
( 本文由《文艺生活周刊》联合凤凰文化《年代访》节目合作)
来源:文艺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