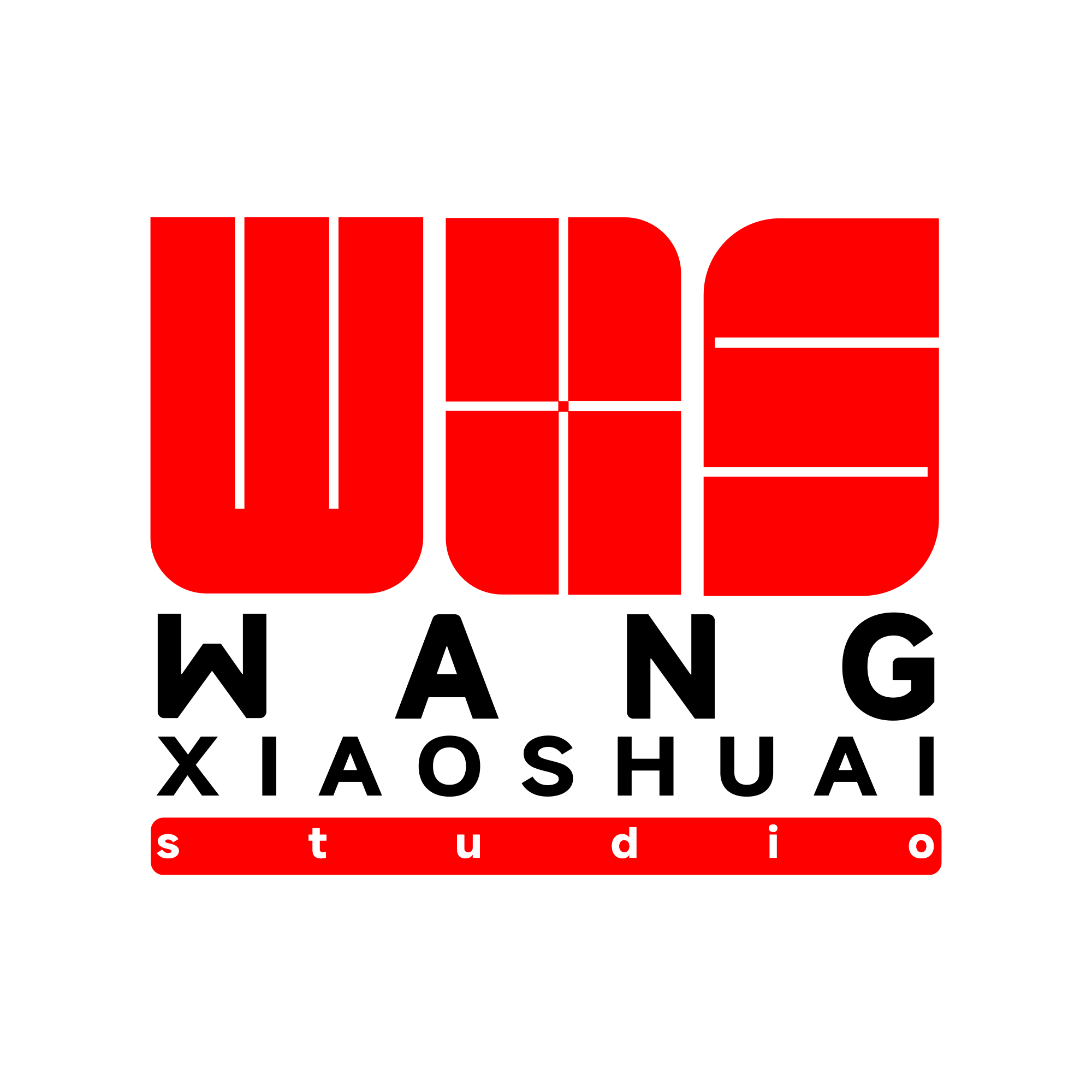在宣布死刑的刺耳广播声中,11岁的男孩王憨正朝着刑场奔跑。但他突然停了下来,表情迷茫。
这是导演王小帅的半自传新作《我11》的最后一个镜头。王小帅迷恋这种山里男孩特有的、无拘无束的跑动。他试图在跑动和停止中表达少年成长的一瞬:王憨在追逐暴力、恐惧与刺激的刑车时突然止步,正是在跟那个年代的暴力行为说再见。
在《我11》的其中一款海报上,王小帅穿起白衬衫、戴着红领巾,与同样装束的小男孩一同上镜。这部影片几乎讲述了王小帅自己的童年故事,但并不仅仅是一部儿童电影:随父母迁居至三线城市的王憨似懂非懂地目睹了文革结束前的仇杀、恩怨和性,导演希望还原这些元素给孩子心里留下的烙印。
它仍然是一部极具王小帅风格的文艺片,就连上述奔跑的一幕,都让人想起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特吕弗的处女作《四百击》著名的最后一个镜头——朝海边奔跑的男孩也戛然而止,留给观众一张迷惘的脸。
玻璃球 捅炉子 缝纫机
这也许是王小帅最为看重的一部电影。1990年代初刚毕业时,他就写出了这个关于“三线”生活的剧本,名为《十一朵鲜花》,意思是十一岁的“祖国的花朵”。为了支援三线建设、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王小帅出生后5个月便随父母从上海迁居贵阳,在三线工厂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1997年,王小帅在自己长大的贵阳光学仪器厂选好了一片老楼作为拍摄地,甚至已经建好剧组。
相较之下,最初构想中的《我11》拥有更大的故事框架:时间跨度从197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囊括三线厂后来发生的变化。然而,由于“各方意见不合”,剧组宣告解散,没了下文。7年后,王小帅把这个搁置起来的剧本拆分成两个,将后半段先拍成了电影《青红》。前半段一直搁置。
看着1970年代的建筑一点点被拆毁,2011年,焦急的王小帅终于有机会重拾那个故事。他在重庆万盛区的一个废弃兵工厂里修复原始场景,甚至花钱在半山腰上重置了一条街道,那里有标语墙和巨大的毛泽东像。
跟《青红》类似,《我11》里仍然包括三线工厂里想回上海的父亲、被人凌辱的女儿——她的扮相与青红极为相似,也囊括了广播体操、上刑场等元素。对那个时期西部三线城市特有的琐碎细节,王小帅不吝篇幅地加以堆砌。小孩们胸口挂着旧式铝制钥匙、父女住所的门上用粉笔写着“大坏蛋”、小孩们放学后在路上玩玻璃弹球……导演甚至亲自教小孩们做广播体操、捅炉子、淘米煮饭,教饰演妈妈的闫妮使用缝纫机、搓煤球。
同时,王小帅把对三线生活的表现视角转换成了11岁男孩的眼睛,“不能太越过小孩所能知道的某些东西,要给人一种朦朦胧胧、似有非无的感觉。”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即使拿捏分寸并不容易,他还是希望通过细节把故事的背后放大,能让观众感觉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虽然我认为孩子的成长跟政治无关,但整个社会环境还是会让他多多少少受到一些熏染。”王小帅说。他更希望表达个体命运与社会变化的密切关系,观众能通过电影回想起自己的11岁。“无论是家长、周围气氛、电视,社会事件都会在你心里留有印记,”他说,“社会变革能帮助你在某方面获得感知,甚至影响到你心理和生理的变化。”
“我没踢你啊!”
1970年代,王小帅跟三个小伙伴坐在楼前玩耍,忽然看到一个逃犯跑过来,警察在后面开枪追击。好奇的小孩们不远不近地跟着,逃犯被抓后,几个胆大的小孩还凑上去踢他。王小帅没有上前。逃犯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这一瞥让他害怕起来:逃犯会不会回来找我?他甚至想上前跟逃犯解释,“我没踢你啊!”
这次印象深刻的目击成为《我11》中最重要的情节,其中还包括了王小帅小时候另一件难忘的事:他刚穿几天的新衣服掉进河里弄脏了,怕回家被妈妈发现,只好自己在河边等它晒干。
王小帅把《我11》称作“半自传电影”。除了那两个细节,男主人公王憨跟他小时候一样担任学校广播体操的领操,而舍不得布票给王憨做新衣服的妈妈、教他画画的爸爸、妹妹与三个小伙伴的设置也几乎完全拷贝了王小帅的童年生活情况。
他一直对拍摄自己的真实经验很感兴趣,从《青红》开始,他就有了拍摄“三线”题材“自传三部曲”的想法——在完成《我11》的拍摄后,王小帅愈发意识到第一代“三线职工”已经慢慢变老,因此拍摄了口述式纪录片《三线人家》——不口述也没办法,因为毫无关于三线生活的纪实性影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留下一些后创作的影像。给几代三线人留下一点东西十分必要。”王小帅说。
事实上,他对反复拍摄同一题材的影片颇有些担心——在如今这样的社会氛围里,老做这种带有个人色彩的东西会不会不讨好、不知趣?他不想成为祥林嫂。假如顺利,王小帅的下一部“三线”题材影片将涉及到当下生活,包括更多的人物命运,更广阔的触及面和视点。
“你的11岁关我什么屁事?”
与很多文艺片一样,《我11》实际上并不一帆风顺。
“你的11岁关我什么屁事?”4月,周立波在一次饭局上就片名与王小帅发生了争执。周立波建议,影片应改名为《8岁梦遗》或者《我发育了》。
2月,《我11》就曾传出发行公司建议改名的消息——他们希望改为《孤胆童年》或《11岁惊魂计》,而王小帅则坚持不对商业妥协。
“他们(发行方)也是为我们好,为了市场做一些怂动性宣传,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我11》还是不错的,至少可以勾起每个人对自己11岁的回忆。”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中国处在一个新的集体无意识时期,票房至上,老百姓又认包装、认忽悠。”
在很多人眼里,从地下导演浮上地面的王小帅约等于“票房毒药”,一大佐证便是他的上一部影片《日照重庆》。虽然动用了范冰冰和王学圻这对商业组合,却只获得400万票房。
两年前,王小帅在戛纳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票房再不成功就退出,不在国内发行自己的影片。
“不在国内发行就省点心呗,”他说,“(拍文艺片)其实是为了给中国观众端上一盘不同口味的东西,他们要是都不愿吃,都馊了凉了,那就倒掉。我觉得这也没关系。”
实际上,与很多文艺片导演不同,王小帅甚至不排斥在影片中植入广告。但比较尴尬的是,对大制作趋之若鹜的广告商家却对文艺片不感兴趣。
《我11》的怀旧元素让王小帅想到了一些红极一时的国产老品牌。他曾试图联系过可能的厂商——大白兔奶糖、凤凰牌自行车及红灯牌收音机,并对他们说:“也许你们已经在生产新产品,但应该把你们的历史告诉别人”。“但对方反应相对比较冷落,”王小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几个月来,宣传方大打“11岁少年与杀人犯的故事”及“唤醒童年记忆、复苏年少时光”的怀旧牌,以求吸引观众。但与强化情节高潮的商业片不同,王小帅又明显把《我11》处理成了一个反情节高潮的典型非商业电影:他并没有正面表现杀人、强奸和放火等核心矛盾冲突点,目击逃犯的情节甚至在影片开始半小时后才缓缓出现。在王小帅看来,自己要说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生活经验:当面对公共事件时,大部分人往往不是亲历者。
不过,《我11》已算是王小帅近来几部影片中最“易于观看”的一部。他之前的几部片子曾被评价“太使劲,与生活有距离的情节太多,离观众远”。而不同于《青红》冷眼回看历史所造成的压抑气氛,《我11》明显欢快许多,带入感更强。
王小帅清楚自己在很多人眼里“比较不知趣、不合时宜”,但仍然希望“可能时间长了,老百姓就不会认为一个漂亮的月饼盒子里一定是好月饼,还是要吃一口,才能知道这个月饼的好坏。”
不过,出于商业考虑,国内观众“吃”这口“月饼”的时间又推迟了一周:为了躲避五一档期好莱坞电影和国产电影的扎堆上映,《我11》的档期已由原来的5月11日改为18日。
而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走进影院去“吃月饼”?“久经沙场”王小帅看起来抗压能力和心态都不错——作为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法合拍影片,影片5月9日就将在欧洲上映。而由于出色的国际发行,影片“完全不可能赔”。王小帅称,中国的票房部分也仅仅在于“追求拓宽观众面”而已。
2012年05月14日 11:44:41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万佳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