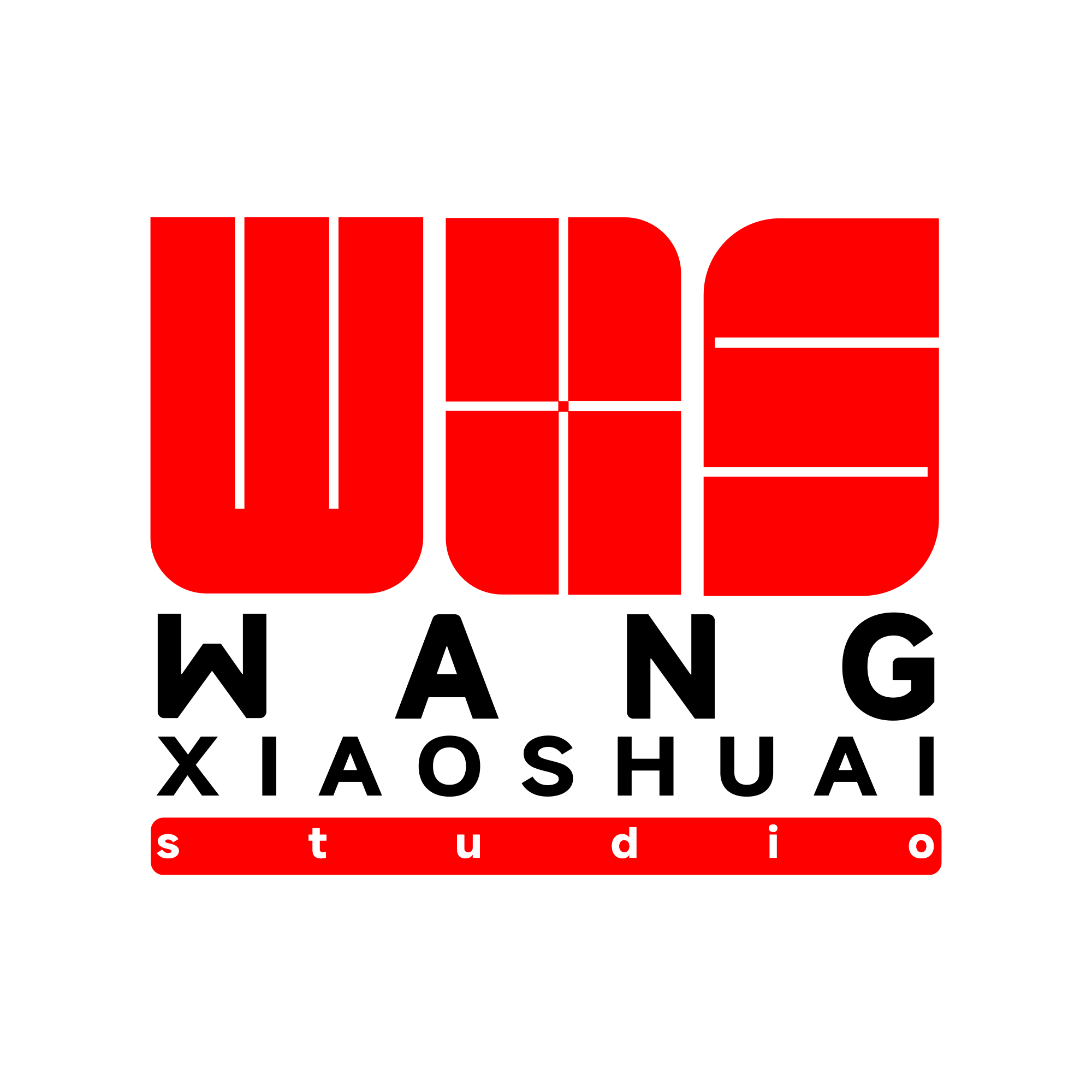王小帅的电影作品中始终回荡着城市的召唤,《十七岁的单车》在海外发行时名为《北京单车》(Beijing Bicycle),《青红》参展2005年度戛纳电影节的英文名是《上海梦》(Shanghai Dreams)。中国两个最为重要的巨型都市交替出现在影片中。前一部影片中的“北京”,既是影片主人公暂时立足的所在,也是他渴望皈依其中的人生目的地。而《青红》中的“上海”更具有能指的想像意味,影片中并没有与上海直接对应的镜头,但是这个词语却活在每个人物的内心,在整个故事情节的演进中也念兹在兹。
有所不同的是,“北京单车”的故事主线是外来农民艰难楔入都市,主题是农民工进城;“上海梦”的故事主线则是离开上海十几年的老工人艰难返沪,主题是市民回城。无论“进城”还是“回城”,都是由乡村朝向城市的运行,影片展现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时段、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的生活映像。王小帅在《青红》中用朴素的镜头语言还原式地再现了一个时代的个体生活切面。名为青红的十九岁少女是上海到贵阳支援三线建设的移民职工的第二代,其父老吴的唯一愿望就是为了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回到上海。在这场艰难返乡的故事中,历史之维和个体命运环环紧扣,构成表面平淡、内里凶险的叙事冲突。推动影片叙事进展的力量是历史意志和个体意志之间的交互关系,赋予其艺术价值的则是对特殊历史中个体困境的真实展示以及来自真诚记忆的精神抚慰。
一 历史意志和个体意志的互生
影片《青红》是一部直面历史的写实主义作品。片中反映的时代离现在并不久远,不仅在历史上还有清晰的痕迹可以查询,而且部分观众就是这段历史的知情人、亲历者。该片首映戛纳,当影片打出汉字题献,“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母和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三线职工”,许多中国观众由衷地鼓起了掌。当然,影片中屡屡出现的“三线建设”一词让外国观众不明所以,甚至在该片回到国内放映后,也有不少年轻观众不知其所指。但是,这个历史词语在影片中是关系到青红一家人命运的关键词,也是笼罩整部作品的历史意志和个体记忆。
青红的父母来自上海,报名到贵阳支援“三线建设”。“三线”政策指的是1965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1。单从历史记载看,“三线”不过是当时众多国策中的一条,而王小导演帅以回忆历史的方式将“三线”纳入镜头叙事之后,“三线建设”的含义就变得生动而具体。影片体现出历史意志之于个体命运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透视历史的切入角度,给一段尘封的历史配上了影像的注脚。
1、话语建构意志,意志拆解现实
《青红》的故事时间约为1980年代前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继续为历史偿还债务的时期。当年“三线建设”抽调的人员多来自北京、上海和哈尔滨、沈阳几个大城市工厂,其中以上海人的返乡愿望最为执着。影片中的三个家庭都沉湎于同一个上海梦——对照了英文名中的“Dreams”。复数的“梦”既是第一代三线建设者不肯放弃的内心希望,也是他们强加在第二代子女身上必须完成的人生梦想,同时还是两代人共同逃离现实伤害的避难方向。
对于第一代人来说,他们是从上海来到贵州的三线建设支援者,当初离开上海是因为历史意志对个体发出了召唤。第一个话语层面是“先进、光荣”等价值诺言,“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2。历史意志通过塑造时代英雄的话语召唤,同化了这些上海职工的价值取向,将他们的个体意志统摄在主流话语的价值观下。因此,剧中的上海职工在回顾各自报名来到贵阳的初衷时,都为当年“一句话,全家革命,就都过来了”的意气之举流露出自责和懊悔。第二个话语层面指向经济利益:“说好了,来几年涨三级工资”。历史话语承诺的精神价值和经济利益合并成为名利双赢的人生路向,使这些上海职工们服膺于历史话语的合理性,接受历史意志并将其内化为个体的自我选择,印证了历史话语对于个体意志的建构过程。
然而在第二个阶段,亦即1965年到1980年左右的十几年时间正是历史意志渐渐消退,个人意志逐渐自觉和强盛的过程。负载历史意志的话语宣传最终未能落实承诺。职工们抱怨:“三级工资到现在也没涨啊”。他们失去了故园,却没有得到利益补偿。双方面的打击使他们在上海家人面前彻底丧失了尊严和认同。不仅经济上已经承担不起,“来回一次要花掉一个月工资”,而且亲情上遭到冷遇甚至轻蔑,“谁还认你这乡下来的亲戚”。他们在上海的“家”并没有像“国”一样认可、赞赏他们的举动,正如第二代的不满:“外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不希望我们回上海去”。代表历史意志的话语没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构起一个有效的价值认同系统。这些建设国家防御体系第三条战线的支援者们,一旦脱离了自己存身的语境,就沦为双重的失败者。一边是家园的拒绝生出无根的孤单感,另一边是外界经济发展映照出穷困的现状,外边“搞计件工资,每个月有三百多块好拿”。在两面夹击的窘境中,历史意志对于个体意志的支配力渐渐松动、减弱。
在第三个阶段,新的个体意志出现,并开始用具体的行动改变现实,尤其改变子一代的命运、现实和意志。历史与个体的矛盾在这个阶段里变形为父辈意志和子辈意志的冲突。父辈以放弃自我的方式来说服孩子服从他们由历史教训中得来的新个体意志,但是子一辈却拒绝理解父辈的历史,拒绝继承父辈们的精神负担,执拗地抗拒着父辈对自身意志的强加和改写,暴力和悲剧就此开始。
2,话语暴力和上海想像
与一般剧情片相比,《青红》中的台词并不多,大量镜头都派给了雾岚弥漫的山地空景,留在人物言谈中的只有一个真正的主题——上海。片中每个人物在和另一个人物进行对话时都必定谈起上海。即便是影片开场时十分拒斥上海的青红,最终也把投奔上海当作唯一的救赎之路。青红之于上海的态度转变,正是父辈的强力意志对子一辈的现实和命运进行的成功改写。正如历史意志采用了强大的话语攻势同化了老吴这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一样,老吴也在无意识中拾取了自身的历史遭际,把自身经受过的意志剥夺再一次通过话语暴力转嫁到子一辈身上,以爱的名义重演一场规定他人命运、操纵他人意志的精神施暴。
这场冲突的发生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前提,对于老吴来说,支撑他违背历史意志的勇气既有挥之不去的上海情结,更有对孩子的殷切期望。
“孩子才是关键,我们都无所谓了。”
“为了培养我,把我派到三线来,我为了培养自己的孩子,我一定要把他们送回上海去。”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的孩子就要回到上海去。”
“上海就是上海……”
老吴的话语信誓旦旦,像一个冲劲儿十足的战士向着强大于自己无数倍的阵地冲过去。可是当他回头看时,却发现为之血拼的女儿不仅没有并肩作战,甚至还临阵脱逃。在老吴看来,青红对于上海的漠然源自本地青年小根,于是就迅速调整话语中上海的梦想性质,把上海当作一个锐利的武器,无情地摧毁了小根和青红的朦胧爱情。他对小根话中有话:“我们家早晚会离开这儿,啊,回上海。”此时的上海就成为鄙弃小根农村身份的堂皇理由,成为阻隔小根追求青红的鸿沟。
然而青红很难认同父亲的上海梦。自然生成的家园感让她疑惑,“我们不在这儿生活还能去哪儿啊,这是我们的家啊”;此后,十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她和本地青年小根萌生了恋情。青年人美好的初恋落在老吴眼里却无异于最危险的信号。他意识到,如果再不尽快离开贵阳返回上海的话,有可能子子孙孙都要定在这里了。老吴的上海梦迅速上升为强烈的新个体意志,他要用自己的意志强力去对抗并中止历史意志施加在他一家人之上的命运。如同历史意志借用“革命光荣”的价值话语和“涨三级工资”的利益话语诱使老吴一辈放弃个体意志,老吴通过喋喋不休的话语暴力,剥夺了青红自然的家园归属和情感欲望,在她头脑里强行楔入了“上海梦”。
从青红对上海的态度转变过程(参见下表)可看出老吴的话语强力意志是如何逐渐生效并最终取代了青红的自然意志的。开场之初,青红不想去上海,也不理解父母和小珍为什么都把上海看作唯一值得努力的方向。但是周围的人都在重复唯一的主题——“回上海”。上海对于青红的父母来说是返乡之梦,是他们改变历史意志,重审个体意志的唯一途径。对于小珍这样的第二代而言则是美好新生活之梦,是改善灰败现实,实现自由想像的可能途径。但是对于青红来说,“上海梦”却是父亲老吴用话语暴力铸成的爱和意志的双刃剑,阻断了她向成人世界的顺利过渡。虽然上海梦最终成功地植入青红的头脑,却是以一种变态的谵语形式出现。影片中用他人的转述来说明青红的转变:“她不是闹着回上海吗?”此时的青红因为精神幽闭而失语。一个反讽的对比出现了:当青红拒绝上海时,是一个有活力的青春少女,当她最终也梦想回到上海时,却是一个失语的空洞躯壳,仅仅成为承载父亲的话语意志。犹如在上一代的悲剧中,她的父亲也一度成为承载历史意志的空洞躯壳。
从“(我)哪儿都不去”到“(她)闹着要回上海”,青红最终认同了父亲用话语建构起来的上海想像,屈服于父亲的话语暴力。上海梦的胜利其实是老吴的意志胜利,代价则是让女儿受到无法治愈的身心伤害。这个伤害既是父亲老吴自身创伤记忆向下一代的转嫁,也是老吴无法中止自身历史之痛的象征,预示了青红的未来将终身携带伤痛的印记。遭到暴力破坏的处女身心永远无法修复,暗喻了这个印记将在青红和父亲的未来生活里共同延续。来自这个印记的痛楚记忆就是刺破上海梦的真相提示——青红和父亲两人的创伤记忆都不会因为回到上海而根本治愈,因为历史已经不能改变。
二 历史记忆中的细节真实和个体抚慰
王小帅在《青红》中退行到了个体记忆之中,通过精心设置的真实细节营造出二十年前的历史环境。影片凭借“真实”这一难得的艺术品格唤起观众们共通的记忆,在历历在目的影像再识中得到情感抚慰。《青红》中的历史记忆是批评,是理解,也是感动。不加美化的原景复现温和地批评了历史之于个体的压力,而作为亲历者,导演长大成人后的重新讲述更能体会打破父辈们的历史负担,让人感动于艺术对于人生的反思、悔悟和无奈。
1,历史语境中的个人困苦
面对历史的姿态是检验影片真实品格的标准,如何表现历史语境中具体的人则反映出影片的价值关怀,《青红》首先经得起第一条标准的衡量。影片精心复原出二十年前山地小城最可能的历史原貌。环境方面,街道景观上同时交迭出现了火车-马车-扁担挑子。三种交通方式表现出这个地区在经济方面的困窘淤积。一方面,外来的先进生产力随着铁路的铺设以飞快的速度一路驶过,另一方面,由于山地的落后和闭塞,交通的主力还是缓慢的畜和人。
小城文化的闭塞一如经济上的落后。青红的父亲每晚守着一台干扰声极为嘈杂的收音机,“窝在这山沟沟里,要是连这都不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另外,片中还多次出现歌曲,开场时手风琴演奏民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舞会上录音机播放磁带(邓丽君《美酒加咖啡》和迪斯科舞曲),吕军带小珍看日本摇滚电影《阿西们的街》,吕军婚礼上海职工们先唱革命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再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从这个歌曲的序列中不难看出历史生活的微妙变化。诚如同样喜爱在剧情中配置乐曲的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所言,“大众文化出现在县城里,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3隐喻了多种生活形态的各类乐曲混乱地叠加在闭塞小城中的精神生活上,真实地再现出彼时生活的原生态。
片中只有一首歌重复了两次,即《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第一次出现在开场,有曲调但无歌词。教小弟拉手风琴的上海职工说,“来,听听老师是怎样用感情的”。话中的“感情”不单是处理乐曲的技巧,也在演奏中融入了真实的乡愁。第二次在上海职工第二代和当地村女的婚礼上,上海职工们围坐而唱。一个职工先独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万古长青……永远屹立在山巅,在山巅。”然而反讽之处在于,高亢的曲调颂扬革命者青春不老,到了敬酒说话时却成了“这是咱们这群职工的第二代了,马上要生第三代了”。雄壮的歌词和激昂的曲调改变不了他们正在失去青春并且可能世代滞留异乡的无奈事实。也许正是出于内心的犹疑和对扎根“山巅”(山中小城)的疑惧,独唱者没能顶起最后一个小节的高音回环,“在山巅”的“巅”字湮没在自嘲的咳嗽中。接下来合唱《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上海职工一起扯开嗓子:“如果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歌声未歇,镜头两次跳切,先是站在高处发呆的吕军,接着是踟蹰坡道路灯下的小珍。镜头最后又切回酒席,合唱的职工们显然已从激情跌入颓唐,歌声越来越低,尾音再次滑脱,最后的“乡”字严重走调,简直是哭腔干嚎。
唱不出“家乡”的“乡”字,与其说是因为上海职工们不胜酒力,倒不如说是歌词灼痛了他们内心的伤痕。他们已经没资格为故土骄傲,更无法发自内心地赞美蜗居的山中小城。这些上海职工虽然滞留在外十几年,却固执地保持着上海的生活习惯。小珍妈妈烧鱼头汤,青红家收音机上蒙着洁白的提花钩织,职工们聚在一起讲上海话。一如王小帅的回忆,“当年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全给占了,小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4因此,他们唱到“这是家乡”的时候又怎么情愿认定他乡作故乡呢?只好在客中做客的离愁中放纵思乡的哀伤。毕竟乐为心声,唯乐不可以伪,故而上海职工们怎样也顶不上去革命决心的高音,怎么也唱不出“这是我的家乡”的骄傲宣告。他们在历史境遇中的困苦之情和难言之隐都在断续的乐声中一泻无余。
2,规训身体和意志管束
《青红》中出现的单位只有三个:三线工厂、技工学校和移民家庭,工厂是上海职工们工作的地方,技校则是他们的子女上学的地方,都可以看作家庭的延伸。在交替出现的三类场景中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身体和意志的规训和管束无所不在。
全片一开始首先是一段字正腔圆的画外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我们一起来做第六套广播体操。”镜头从黑幕中推出,画面上方出现一个高音喇叭。镜头穿过狭窄的走廊,俯拍狭小校园。排成队列的技校学生软绵绵做操,和刚健有力充满朝气和权威意志的号召性领操乐声构成极大的反差。远处高台上晃动督导教师的剪影。接着,高音喇叭里换上真实的带口音的普通话,禁止女生烫发,禁止男生穿喇叭裤等。声音中充斥不可化解的怒气和不容置疑的正义感、威严感。第三个段落的声音再降一格,一个中年男老师慢条斯理地怂恿穿喇叭裤的男生高抬腿,随后抽出剪刀飞速剪向宽裤腿。所有这些技校场景中的段落,都指向记忆中身体受到的规训。
强行剪发和直接剪宽裤腿是虚拟的身体暴力,在威慑的意味上迫使学生放弃按照个人审美标准修饰身体、展示身体的权力。如果按照福柯的身体观念,从实际效果来看,广播操未能增加学生们的体能,剪裤腿也没能杜绝学生们继续模仿新潮装扮,所强调和贯彻的无非是一种强力意志或者说是纪律,目的是“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驯顺的身体”,就功利目的而言,要增强这些身体的可用力量,所以安排了广播体操,同时还要减弱这些身体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更容易服从,所以才会强行剪发、剪裤腿。5作为三线政策的附属和延伸,技校对学生们的身体规训和意识约束几乎是历史意志缩微版重现。
青红从技校回到家,仍然受到身体和意志两方面的规训和管束。可是,老吴之所以像对待囚徒那样对待女儿,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囚徒。他抱怨十几年来“窝在这山沟沟里”,怎么也逃离不出“国营新兴光学仪器厂”。下班时刻,黑色的铁栅门打开大锁,缓缓拉开,清一色灰蓝装束的人群机械地涌出,伴随这一切的是被雨淋湿的军号声,提醒人们注意,这是军工厂。
工厂中的囚禁意象象征了父辈受制于历史意志的事实,他们的愿望则是一定要把儿女释放出这个禁锢自己的地方。但是为了达成放飞的愿望,采用的办法却是新一轮囚禁。老吴用跟踪、禁闭等方式现限制青红的身体自由,可悲的是,这一轮囚禁的目的是让青红脱离老吴指认的囚禁境地,以清白之身回到完美上海。由此就出现了严重的意志错位。青红要到山上会小根,山是青红的自由境地。老吴站在山头监视青红,情感乐园变成权力制高点。
影片在表现老吴对青红的意志管束时,采用了逼视的机位和倒“T”字的画面构图。青红处低,老吴处高;青红在远景,中间是老吴,最近处是机位,造成青红无法突破父亲看守线的视觉效果,完全符合监视者对囚禁者的构图需要,“被囚禁者受制于一种权力局势,他受到的监视太多了,因为他实际上不需要被这样观察”。6另外,每次老吴训斥青红,都是青红坐在半封闭的斗室深处,门外老吴踱步。两个房间垂直构成倒“T”字。尽头处青红没有动弹的余地,横线上老吴在盛怒中来回走动。而且,青红的房门如同牢房门一般由外向里关,这一设置使她无权关上房门拒绝老吴训斥,老吴却可以随时摔上房门禁闭青红。老吴对青红的身体规训和意志管束不构成身体上的暴力,却是无言的精神重压和无所不在的禁锢。甚至青红偶尔逃出家门,老吴年轻时的照片还从背后炯炯地盯着青红的背影。
3,个体情感抚慰
家庭-技校-工厂,三个场景中的规训如出一辙,尽管施与受的主客体有所变化,但是整部影片对于既往年代的回忆还是倾向于冷色的个体困境。多雨的贵阳天气和灰蒙蒙的山地实景进一步加重了影像记忆的伤感情调。影片的情感关怀和抚慰功能在此实现。对于经历过困境的人们来说,真实地复原他们曾经忍受的历史场景,不刻意美化,更不故意隐瞒,本身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尊重,也是对历史亲历者的敬礼。但是影片对于艺术能在多大程度上抚慰个体情感,还是有所保留的。影片临近结尾,青红认同了上海梦,却失去了纯真的爱和童贞之身。此时山地雨丝如幕,反锁在屋里的青红滴血如泣。刚刚在军号声中下班的青红父母踉跄跑来。画外音乐渐起,却是1970年代最后一年里最为流行的《甜蜜的生活》插曲。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乐景写哀,更增其哀。在大雨中憧憬阳光,在小根被捕后说携手,在历史意志的囚禁中高歌革命理想,在离家千里以外渴念远方。真实的影像记忆和影片的关怀所系构成了一个精致而奇异的吊诡,成就了影片《青红》的现实主义审美品格,也在个体记忆的影像书写中表达了子一辈对父辈的理解和宽容,同时尽其所能地抚慰了一段历史的伤心。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21页,1989年版。
2 陈东林 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
3 程青松等 著《我的摄像机不撒谎》,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343页,2002年版。
4 《我的摄像机不撒谎》,298页。
5 福柯 著《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56页,2003年版。
6 Foucault, Michel, Panopticism, A Reader of Cultural Theories,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p164, 2003.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