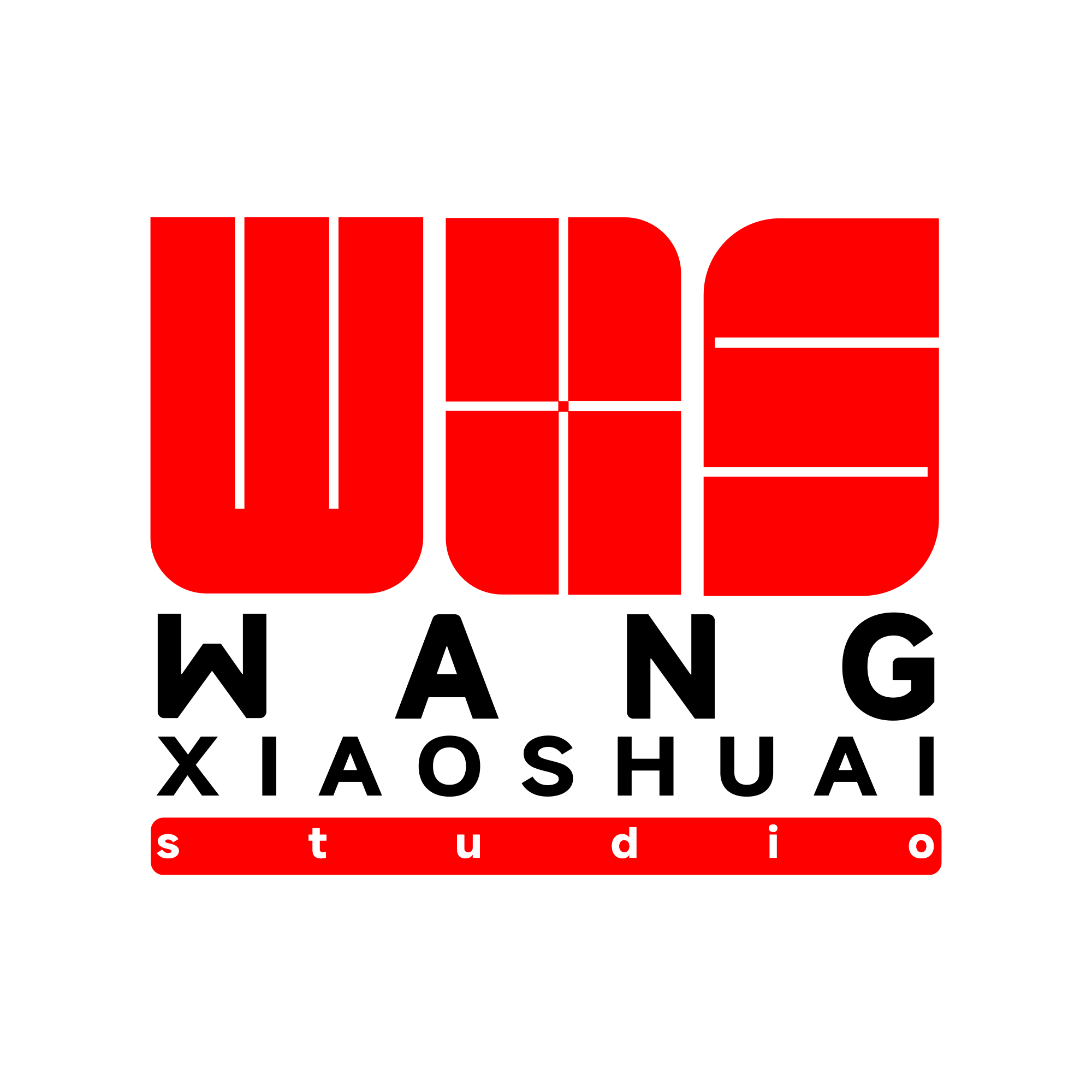提要:青年导演王小帅的新作《青红》试图用影像探讨转型时期两代人在漂流人生中与命运相抗争的主题《。青红》将 父辈与子女们的青春叠加在一起,因而使影片的叙事指向曲折丰富起来。所谓的上海梦,其实只是父辈们自己的梦, 不但于子女们的青春梦想无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似乎还撕裂了子女们本应具有的平常的青春梦想。 关键词:王小帅 青春 漂流 父辈 青红
《青红》的电影海报是这样宣传的: “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残酷青春系列”之《青红》
你十九岁时有没有爱过
你十九岁时有没有想过
你十九岁时有没有⋯⋯过 从《青红》的海报所强调的年龄——“十九岁”——
来看,这应该是一部青春片,王小帅这个名字也让人联想 到它的青春主题。然而《青红》的最后一个镜头却定格在 载着青红一家奔向上海的吉普车在贵州蜿蜒起伏的大山里 渐行渐远,然后画面上出现一行字:“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 母和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三线职工。”这样,19 岁的年龄被 笼罩在了父母的阴影之下;而所谓的“青春”,也就有了更 为丰富的内涵指向,它们叠加了父辈过往生活的经历(父 母们的青春),并因此而使影片的叙事指向曲折丰富起来。
和王小帅的其他电影一样《, 青红》其实也试图在时光 的流转中表达他对于转型期历史的看法,以及在转型过程 中每一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从这意义上《,青红》 也可以说是一曲青春的挽歌,既是父一辈的也是子一辈 的。父母们把青春留在了远离家乡的穷山僻壤,其人生满 是疲惫;青红们的青春则被压抑,甚至与死亡相缠绕。
一
1965年至1971年间,国防工业大规模向中国内陆省 份所谓“三线”转移。青红小时便随支援“三线”的父母 来到贵阳。虽然一待便是十多年,父亲老吴还是念念不忘 回上海去,认定那里才是他的归属,当意识到自己人生已 荒废,让子女离开这儿,离开偏远不发达地区,回到上海 那个繁华大城市便成为他们日日揪心的梦想。这实际上是 父辈们把个人梦想强加于子女身上。
与《十七岁的单车》相比,《青红》沉闷了许多,全片 灰蒙蒙的,剧情大多发生在晚上或者幽暗的房间,这样的 气氛很符合那个时代。片中有无数强调画框的构图:窗户 玻璃、铁栏杆、门框⋯⋯总之,是重重禁锢。主人公青红 往往置身于层层相套的门窗或被切割得极为狭小而局促的空间中,前景经常有窗户、墙等遮挡,仿佛不可突破的精 神牢笼,青红在其中单薄、绝望而无助。
在青红与父亲的第一次对话中,二者还出现在景别、 构图对称的画面中,暗示着父女之间尚处于势均力敌的抗 衡阶段。接下来,在影片的视觉语言中,青红就始终处于 父亲的严密监控下。青红穿上了小根送的红色高跟鞋满心 欢喜,转身却发现父亲远远地站在高处。通过青红的视线, 我们看到父亲铁青着脸。反打镜头中摄影机透过父亲的肩 膀俯拍僵立在原地的青红。父女俩未来的位置关系基本确 定,父亲处在优势的位置上。但是不管是湿滑的台阶,还 是路旁的注目,或身后父亲沉默的怒视,都没有使青红换 掉那鲜艳的红色,红色高跟鞋敲击青石板路发出的“嗒、 嗒”声,显示父女之间紧张的对峙。
这种精神上的对峙在下面这个用长镜头讲述的关键段 落中也得到充分的表述:
中景。青红坐在自己床上,门外处于前景的父亲走向 画面左侧,直至身体的大部分处于画外,只在左侧留有约 1/5 的背影。
(声音)父亲:“我问你,鞋哪来的?” 短暂的沉寂。父亲:“是不是那个小赤佬给的?” 青红:“不是。”
父亲:“还说不是,还嘴硬。” 父亲从左侧走向画面右侧,只在右侧留下约1/5的背影。 父亲:“我看你这几天就是不对劲。一有机会就往外
跑。我那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那些信都白烧了?哎, 脱了脱了,看你就恶心。”
青红弯下身慢慢地脱下红皮鞋。
在这一长镜头中,虽然画面中心是青红,但父亲的形 象却是视觉的中心。父亲在前景中站立、走动,青红在景 深处面无表情,始终沉默,前后景构成动 / 静、变化 / 僵 止、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父亲在镜头中尽管只是背影, 却占据更大的面积,而后景的青红却始终只有画面的下半 部分。父亲居高临下的位置凸现了主动,象征着一个神圣 的权力空间。言语/ 声音也表现了同样的语言效果,不仅在台词上表现出父女间的冲撞,而且是父亲的声音控制着 画面空间,不管在画外还是画内,而女儿的影像却始终是 悄然无语的。
王小帅试图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父亲的强权或粗暴,而 是他们基于自身生活经历的内心的焦虑,和在这种焦虑影 响下的对于子女们的前途(青春)的规划。然而,正值青 春的子一代却不会理解父母的心愿,他们对故乡一无所 知,爱的恰恰是脚下这块生养他们的土地和这上面的人, 他们迎接和焦虑的是自己的生命季节——恋爱季节。父母 与子女的隔阂在吕军的婚礼上做了最好的象征性的表现。 父亲们伴着手风琴的旋律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蓝蓝的天上 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一把吉他,几杯浊酒,人 过中年,故乡却只在魂牵梦萦中,归期渺茫,怎能不一醉 方休。唱完后集体沉默,冷场。这中间有几秒钟的时间,导 演给了一个站在墙头上的新郎的镜头。吕军站在高高的墙 头上俯视着父辈们,没有丝毫理解,却是哀怨和冷酷,它 暗示了吕军接下来和小珍私奔的僭越和不轨行为。
在影片结尾,青红一家仓促驱车离开贵州,半路遇上 公判大会,当车被围观的人群挡住时,车窗外闪过吕军略 显沧桑的脸,他和小珍一样也回来了。他在外面转了一圈, 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地。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吕军还不经 意做了一个“擤鼻涕”的动作,无表情地看了一眼车。这 时,他已经变得和这地方的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于无动于 衷。就这样,在“出逃”和“回归”的对流中,导演将青 红的前景渲染得灰暗无比——在回到上海以后,她的生活 会呈现出父辈们想象中的光明吗?抑或,最后,她也会如 吕军一样,退回到这个生养她的山区小镇,成为这个地方 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此片被王小帅题献给曾在三线工作 的父母,使人误以为那是一种矛盾的和解,其实要说和解 也是一种多年后的缅怀,真实的是影片所表达的父女矛盾 之下的另一重矛盾。
二
《青红》表面看起来是讲述贵州小镇的故事,但它与同 年代的《孔雀》截然不同,骨子里应该是一部城市电影,它 的英文片名Shanghai Dreams更为准确地表达了影片的 内在精神。对于《青红》来说,上海以及上海所代表的城 市文化乃是笼罩全片的一个“场”,而矛盾,也就在这个想 象的文化—地理场域中展开。
从表面上看,《青红》是在两代人的矛盾中展开故事 的。然而当王小帅把它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来讲述, 这个矛盾就显现出了它历史、文化上的悲剧意味。父亲为 回上海阻止女儿青红与当地人恋爱,青红的反抗在父亲的 强权面前不堪一击。朋友小珍追求爱情私奔的结果反而让 青红认清了现实,在与男友小根摊牌分手的当口,愤怒的 小根强暴了青红。精神趋于崩溃的青红与父母一起偷逃回 上海,而小根却在严打中被判重刑。枪声响起,青红的梦
(爱情)破灭了,而父母们对于青春的缅怀,以及他们对于 子女的青春规划,则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在这个层面 上,父母们的青春与青红们的青春,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得 到了融合。
然而略一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融合”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的假象,父辈与子辈的心理裂痕依然存 在,而子一辈的青春前景也依然暧昧不明。在这组矛盾中, 父母们口口声声地声称回上海是为了子女,可青红和她的 弟弟却对于能回上海并没有太强的愿望。即使青红用自己 迟早也要走的理由来拒绝小根,可从她与小珍的谈话里可 以看出,她内心深处对于与本地人结婚而留在此地并没有 特别的抗拒。念念不忘要回上海的其实只是父母这一辈 人,尤其是青红的父亲。
父亲的上海梦是可以理解的,他生在那里,长在那里, 那里是他心中的家园,梦里的明月光。他是如此强烈而执 著地渴望回到上海,为此他一直不肯放弃听收音机的习惯, 也一直不肯让自己,乃至自己的子女在异乡的土地上落地 生根。然而青红呢?作为主人公,19岁的她在片中却是沉 默的存在。小根夜夜在山坡上等她,她沉默不语;父亲每 天跟着她,她沉默不语;小珍带她去参加地下舞会,她还 是沉默不语。作为主人公,她却时时处处显得被动,让人 看不清她的所思所想。父亲夸大了她的叛逆,不知道她其 实是准备顺从的;小根不理解她的游移,夸大了她的承诺 的含义,不知道少女的她其实尚未做好承担命运的准备。 他们从不同的方向逼她,终致她要用扼断青春的方式来做 逃避。生命被挽回的她却失去了对青春的所有记忆和热情。
影片结尾,青红的一家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坐上了 一辆偷偷开往上海的汽车,也就是在那个清晨,小根被押 上了囚车。车行蜿蜒的山间公路上,一切先是静谧而诡异, 突然传来三声划破天空的枪声。小根是否被枪决,我们不 得而知。电影叙事刻意让“房洪根,犯有强奸罪”后面的 宣判声音被噪音打断。此刻,青红及家人的内心世界留给 观众自己揣摩,对青红一家未来在上海的生活也留下了想 象的空间。影片以一个看似开放,实则极为残酷且拒绝回 答的姿态结束叙事:这家人乘坐的吉普车渐渐消失在盘山 公路上,背负着一个女孩儿的贞洁和一个少年郎的生命。 这样的归程何其沉重,心灵的创伤何时能得到抚慰。青红 和她的父亲都把青春留在了那个西南边陲重镇。在此,留 守和飘移成为悲剧的两面,变得难以逃遁。在这样的思想 层面上,所谓的梦(Shanghai Dreams),其实只是父辈 们自己的梦,不但于子女们的青春梦想无涉,而且在一定 程度上,似乎还撕裂了子女们本应具有的平常的青春梦想。
三
在王小帅的叙事空间中,他的人物永远想反叛,却永 远只能是一种秩序中的辗转。王小帅表示:“这部影片表现 的就是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个体在与社会矛盾愈发激化时 的挣扎和反抗,而我所呼唤的正是对个体的尊重。”(1)
影片开头的广播体操就暗示了无处不在的集体话语。 节奏强烈步调一致的广播操配乐比画面出现得更早:“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准备好, 我们一起做广播体操⋯⋯”随着第六套广播操前奏的旋 律,镜头缓缓地推上,南方潮湿的气息瞬间扑面而来,阴 暗潮湿的走廊,斑驳的墙壁,靠墙的雨伞全都是黑色。前 景是一个悬挂着高音喇叭的窗口,窗外不时飘动的红旗一角成了大片灰色中唯一的艳丽,此外就是掉光叶子的树和 操场上排队做操的学生。在这里,如何在一个坚固而封闭 的历史困境和秩序之中寻找个人命运的道路,成为楼道、 广播操和窗口的意义所指。
《青红》的故事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的裂变对 应着主人公生命的裂变。国家的变化和个人的成长混杂在 一起。为体现对时代质感的逼真复现《,青红》多采用现场 录音,即使音乐也不用画外的无源背景音乐,而是全部采 用场景内的有源音乐元素。第六套广播体操音乐的两次运 用,以及邓丽君歌曲旋律的多次反复,象征了集体主义与 个体欲望的冲突和碰撞。第六套广播体操象征了在封闭和 僵化的体制下,青少年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手段是整齐划一 的,而脱离集体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是从邓丽君的靡靡之 音开始的。
在影片中,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电影插曲《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曾两次在贵州小镇上空很遥远地回响着。歌中 唱到: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我们的 心儿飞向远方 /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 啊 / 亲爱的人啊 携手前进 / 携手前进 /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 充满阳光⋯⋯
那时的抒情也不是属于个人的,即使是歌唱个人的爱 情也一定要跟工人、农民、国家之类联系起来才有合法性 和合理性,否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
而在小珍房里她悄悄地用单卡收录机放给青红听的则 是邓丽君的《谁来爱我》,地下舞会里弥漫的也是邓丽君的 《美酒加咖啡》,甚至本地人小根口琴中传出的还是邓丽君的
《南海姑娘》。收录机和录音磁带“携带着台湾歌星邓丽君喘 息般的‘气声’,席卷红色中国”,它们打破了电台声音的神 秘性和垄断性,国家意识形态精心构建起来的革命的声音神 殿开始出现了裂隙。(2)这预示着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最早听到这种音乐的,是像吕军这样的街头“小混混”。大鬓角飞机头发型、贴着标签的蛤蟆镜、大喇叭裤、 尖领衬衫,这些是有叛逆倾向的所谓“小混混”的全副“行 头”,它们在吕军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小镇上像吕军 这样的人其实很受年轻人的崇拜。高中女学生很喜欢那样 的人,跟着他们上舞厅或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去看露天电影 是很荣耀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敢开风气之先 的,是一种体制之外、制度之外的生活方式。而青红的父 亲说到底不也是要过一种体制之外的生活吗?
然而在青红父亲的身上,折射出的恰恰是他本人的命 运被政治话语改写的痕迹。在迅速变化的时代面前,他们 那三线建设者的身份早已荣光尽逝,甚至意义模糊。当这 些浮萍一样的移民家庭被时代的潮水抛掷到荒芜的岸上 时,他们疼痛地发现,自己的身份已经完全被历史所改写。 毫无疑问,青红的父亲不愿意女儿来重复自己的命运,或 者是承担自己命运的后果。但他管制青红的方式是将自己 的命运缩小复印到青红身上。两者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 操纵青红父亲的是政治指挥棒,操纵青红的是家长权威制。
小珍与吕军离家出走、父亲与同事谋划辞职回上海, 这两条线索推动了青红的选择。她对小根的恋情本来就不 明确,所以当个体难以左右家庭和时代的诱惑时,她选择 了与小根告别,终导致小根的强暴。愤怒的老吴曾试图与 小根拼命,想以个人方式了结,但他最后还是找来了公安, 依靠国家机器将小根绳之以法。但权力是面双刃剑,当权 力之刃伤到对手的同时也伤及了自身。青红一家在悄悄的 归家路上,虽没听到小根最终的宣判结果,但情感和历史 的重负是不可逃脱、无法躲避的。正如父女两代人的青春 和国家命运解不开的历史纠结。
(俞洁,讲师,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系,310018)
来源:当代电影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