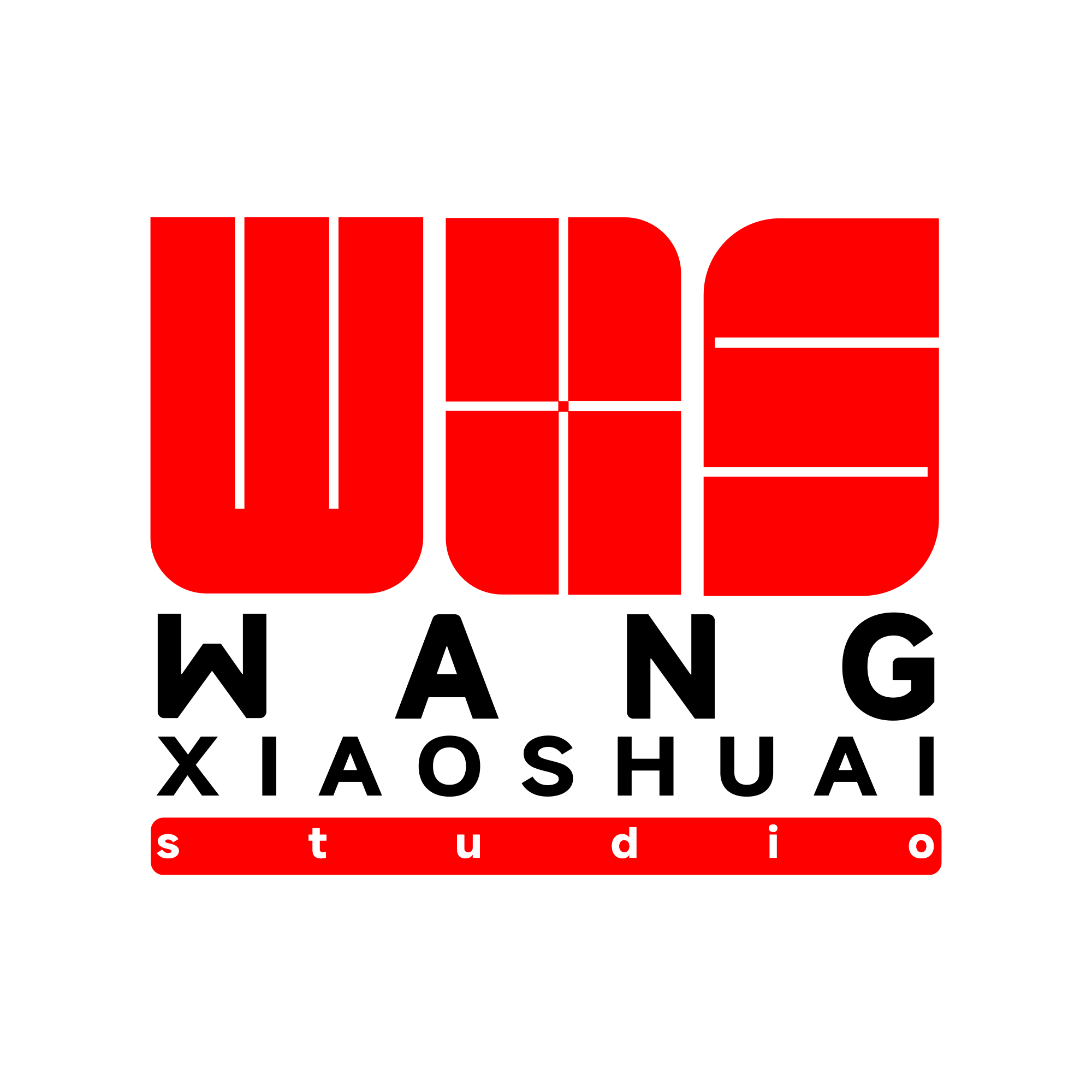作者:程青松
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尽管不是十分恰当,不过也并不离谱。三大电影节里,戛纳相当于奥运会,威尼斯相当于世锦赛,柏林相当于世界杯,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都是经过国内的层次选拔才能成行的。入围戛纳,就证明这部片子是这一年内世界电影的佼佼者,《青红》能成为HYPERLINK 戛纳电影节的正式竞赛片绝对是今年中国电影的一件盛事。在我们收藏的世界经典影片中,来自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是最多的,其它电影节上诞生的世界经典名片可谓凤毛麟角。象我喜欢的影片《霸王别姬》、《钢琴课》、《大象》、《地下》、《低俗小说》、《永恒的一天》都曾经在戛纳加冕。
王小帅凭借其独特、敏感的电影个性,从他自筹资金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到《青红》,十二年的时间里,已经导演了七部影片王小帅开始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电影风格。《冬春的日子》被BBC评为电影诞生以来的100部佳片之一,同时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扁担·姑娘》入围199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十七岁的单车》获得51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2005年5月21日。在第58届戛纳电影节上,《青红》一举获得了评委会大奖,非常凑巧的是今天也是王小帅的生日,戛纳电影节给予了这位生于1966年——中国最动荡的年代,的导演一份最美好的礼物,同时我们可以把《青红》的获奖视为新一代的中国导演为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奉献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旅行在王小帅的生命里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够体味到其中的颠簸、快乐,疲倦和幸福。1966年的夏天,王小帅出生两个多月后便随父母从上海去往贵阳。其时正值文革爆发,横贯大陆东西的旅程,一路上,担惊受怕的是王小帅年轻的父母。而他,已然不记得沿途的红色风暴和革命小将的“一路歌声一路笑”了。
在贵阳,王小帅生活了13年。贵阳是一座小山城,几乎都是外地人,尤其以四川人居多。不过,居住的时间长久了,外地人也就成了贵阳人。孩提时代,王小帅开始学习绘画,在一张白纸上涂抹阳光雨露不及画一艘轮船,或者一驾飞机有意思,渴望在某个季节、某个日子被带走,这样的愿望,大概已经宿命地从出生两个月后的那次旅行就开始了。对电影的记忆,王小帅说得出来的只有《董存瑞》和《闪闪的红星》。和大孩子一起趁着检票的混乱溜进电影院几乎是王小帅这代人共同的记忆,也算是他最初的电影经验。 当然那个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这13年的经历会在有一天以电影的形式出现,《青红》在那13年的人生经历中已经埋下种子。
1979年,王小帅全家迁往武汉。武汉是个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流动人口非常多,几乎每个外来者都要面临着现实的诱惑,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这样的困惑显得异常突出。王小帅质朴、执拗的性格跟精明、善于变通的湖北人有很大的差异。不过,江城的廓大和气派也让“贵阳人”王小帅大开眼界。王小帅在这里只生活了两年,可这两年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他的青春期是在这里开始的,他独自出门去远行也是从武汉开始的。一个人由少年进入成人世界,绝对不会是“花季雨季”,特吕弗的《四百下》、小栗康平的《泥之河》、侯孝贤的《恋恋风尘》、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包括陈果的《香港制造》都在反复印证相似的命题。
1997年,王小帅在武汉拍摄了他非常《扁担·姑娘》(《越南姑娘》)。他把镜头对准了一个从农村来到武汉的少年,低徊的汽笛,鳞次栉比的街边地摊,繁忙的轮渡,包括潮湿的江雾,这些异常真实的影像进入了王小帅的视野。所有表象的东西被观照时,都可以闪现出它本身从没有觉醒的光泽,它已经由现实的物质成为精神世界的构成。电影的魔幻之处正在于此,它可以呈现,或者说接近人的精神世界。
王小帅在他的生命旅行中发现了这个秘密。 1981年,王小帅来到北京,成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一名学生,四年当中,要成为一名画家的愿望与日俱减。80年代初,正是中国电影全面复苏的时期。通过绘画来反应自己对周遭世界季节和温度的变化,显然不再能满足王小帅。附中毕业的时候,王小帅没有继续学画,而是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是1985年,当时的中国影坛。第五代导演正在全力出击,《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猎场扎撒》相继问世,这些影片震撼了被革命浪漫主义加革命现实主义熏陶的国人,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的兴趣。王小帅在电影学院,开始如饥似渴的观摩世界上最优秀的影片,安东尼奥尼、费里尼、阿伦·雷乃、小津安二郎都是他喜欢的导演。后来,他又对侯孝贤、北野武、阿巴斯的电影推崇有加。
电影为王小帅展开了一条银色旅程,而这一切来自于他生命最初的旅行。
电影评论家郝建在其《无法命名的一代》中这样评价王小帅这茬导演:“他们的思想成长、基本的艺术思想和政治理念成型是在80年代。在他们身上,比较明显的是80年代的思想营养。第六代成长于80年代,浮出海面却是在90年代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巨大的撞击、转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产生极大的分裂、转变的年代。”
1989年夏天,王小帅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1年才去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在福州,他呆了两年。两年当中,小帅被动地等待着制片厂给他拍摄电影的机会,写了五个剧本,没有一个投拍,孤独的时候,小帅曾经在墙上写下“镇静”两个字。
1993年,王小帅回到北京,自筹资金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没有厂标的独立电影《冬春的日子》,不少误读王小帅的影片的人会认为这样的影片过于忧伤和绝望,《冬春的日子》里的画家刘晓东最后精神失常,而《极度寒冷》中的行为艺术家齐雷干脆放弃了生命。其实他们非常热爱生活,《冬春的日子》里简单反复的日子,仍然不时透露出隐隐的诗意,喻红在影片中突然凝视着镜头长时间的静默,将生命里本来就具有的那份虚无(生命的另一面可能是饱满)体现得令人震动,抒情而不滥情,王小帅用极其节制的方式来表现了他们的某种具有共性的压抑感和孤独,我们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冬春的日子》这样单纯、简约,精神化的影片。该片被BBC评为自电影诞生以来的一百部佳片,也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影片。这是中国导演的荣誉,也是中国电影的荣誉。西方影评界这样评价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如果你对中国电影的了解还来自于张艺谋或陈凯歌的话,那么年轻的独立电影人王小帅的作品《冬春的日子》将带给你一份新的惊喜。《冬春的日子》充满了一股狂热而又哀伤的情绪,王小帅以优美的影像和音乐打造了一曲稍纵即逝的爱的挽歌。
《极度寒冷》的齐雷,绝不随波逐流,身体力行的介入他所从事的行为艺术,他是一个内里渴望人类情感又外在疏远人类情感的梵高式的人物。齐雷没有死于自己的行为艺术,而是死于自杀,表现的是他对“伪生活”的弃绝和对真实生活的感悟。
在看似冷峻的《冬春的日子》和《极度寒冷》里,王小帅用影像传达了他对生命的感受和热爱。这一时期王小帅的影片有着浓厚的哲学意味,从影像上来看,空间封闭,构图凝重,属于形而上的范畴。
王小帅是中国60年代出生的青年导演中一直还在坚持按自己的追求拍摄电影的人。他也是很不喜欢透过媒体谈论关于电影创作之外的东西的人。而让他来谈找钱一类的问题本来是最有发言权的。在中国的文化批评里最缺乏的可能就是独立品格。比如谈谈中国电影,谈“代”的多,谈时髦的文化转型的多,可是谈作品本身或者说谈创作的很少。
中国的电影批评最喜欢刮风,沿袭的思维模式则是“非此即彼”。本来,电影表现什么人,他是什么职业,处于什么阶层都不是问题。,可是当纪实,底层,民间等语词再次被功利的理论家利用时,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就成了某种不合时宜的东西。
王小帅的电影非常知识分子化,绝对不是平民的视点。但是并不代表他将自己和平民分开,也不代表他要将自己和生活切断。他仍然透过电影来关注人物的精神状况,只是关注人物的方式到了《扁担·姑娘》发生了位移和变化。我把他的这一创作阶段王小帅的物质时期。
前两部影片无法同观众见面,不能和自己之外的更多的人去沟通,王小帅感到异常的孤独。变通的方式很多,一些导演可以完全放弃自己的创作立场和原则,去做所谓的三性统一(所谓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影片,很快就能获得在中国电影界讨生活的通行证。可是王小帅无法去做这样的选择。《扁担·姑娘》给王小帅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他继续从事精神探讨的支点。王小帅回到了武汉。
很多导演都喜欢在自己的家乡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章明在家乡巫山拍摄了《巫山云雨》,贾樟柯在家乡山西汾阳拍摄了《小武》。而王小帅直到拍第三部电影《扁担·姑娘》才回到曾经居住过的武汉。
码头上的年轻民工,涂抹着血红嘴唇的异乡少女,“生活”召唤着他们。人或许是最可怜的动物,不管他在想什么,在思考什么,他的一切行为都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上。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对物质的所有替代物,“随身听”,钞票,性,江湖地位,充满了狂想。前两部影片的客观视点转化为剧中人的主观视点,王小帅的电影空间也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由封闭的画室向较为开放的城市扩张。我们在《扁担·姑娘》中听到的江笛声,老大高平、“扁担”东子和越南姑娘阮红带有湖北腔的普通话(需要指出的是普通话对湖北话的改造,不代表文明的进入,而是暴力无所不在的象征)以及整个武汉码头和江面的取景,都是一个极其“生活”、“物质”的场景,可是越南姑娘在这个城市仍然一贫如洗,最后还成为了被打击的对象。在江湖上地位最为低下的歌女和扁担(挑夫),慰籍他们的是一首歌,歌声贯穿整部影片:“你还能够留下些什么?是散落的白纸片。你爱的天堂里面,请来听我唱首歌。”围绕着金钱和女人的话题,指向的还是人的精神。《扁担·姑娘》在戛纳受到欢迎正是由于影片呈现了我们在现代化的命题下所经历的沉重代价。
王小帅1999年拍摄的《梦幻田园》。文刚是工程师,他和新婚妻子小霞在郊区买了一幢别墅。和小霞结婚以前,文刚和保险公司的安安有过一段恋情,小霞对此耿耿于怀。这天早上,小霞出门了。文刚开始不停的打喷嚏。大雨中,安安来到文刚家。文刚见小霞浑身湿透,让她进屋洗漱。没过多久,小霞的家人从东北农村来到别墅,文刚将安安藏进了储藏室。安安来不及走,小霞也回来了……
文刚近乎自虐的自我审查,妄想症,折磨了他整整两天。有了金钱也有了房子的开始阔绰中国人,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心理疾病呢?整部影片围绕着储藏室展开,人物众多,情节性也加强了许多。在叙事方式上的改变,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有人认为,比较起前三部影片来,王小帅的创作状态有所回落;还有人认为影片里的储藏室非常具有象征性,还不习惯“站出来生存”的国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储藏室,人们不是到那里忏悔,而是去逃避自己想象的审查。文刚的生活因为他曾经坦然面对的东西的到来而陷入种种混乱,如何梳理这样的混乱,使我们的精神达到最大限度的舒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真正迫切而现实的问题。王小帅的叙事给《梦幻田园》抹上一笔浓厚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经历了整整十二年的艺术探索,无论是直接提出精神命题还是通过刻划物质生活对人的异化,王小帅的镜头始终对准的是人并且努力地保持自己在艺术上的完整。最让人感动的是,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王小帅仍然在他的影片中坚持他的理想主义,坚守他的精神家园。《冬春的日子》里,喻红离开了囚禁她的画室去了美国;《极度寒冷》里,经历了无数次葬礼的齐雷沉睡在阳光明媚的自然里;而《扁担·姑娘》结尾定格在扁担对他心爱的越南姑娘露出的积攒许久的笑容上;《梦幻田园》里的文刚和小霞从恶梦中醒来后又安然睡去。而在《十七岁的单车》,这部描写残酷青春的电影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导演对当下中国青年人的生活的关注。
王小帅的电影,构图优美精准,造型意识强烈,他始终在运用自己的电影视野观照充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些被异化,感受到异化或者拒绝异化的人。而这样的努力都是在维护一件事情,使我们的生命免遭伤害。
王小帅对人性仍然有所期待,这也是王小帅拍摄电影的原动力。他的影片中的每个人似乎无时无刻不处在清醒而痛苦的自觉中,他们极度地感觉到生命的存在。这样的自觉在《青红》中得到了最为犀利、尖锐的体现。
三年前,我,黄鸥和小帅一起聊天的时候,小帅谈到他出生在上海,可是才两个月的时候,就跟随参加“三线”建设的父母一起到了贵阳,在贵阳一直成长到13岁。贵阳是小帅拥有记忆的第一个故乡,而他的出生地上海,真的就如同一个遥远而不可及的梦。我们的谈话后来被收录进《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之中。虽然小帅母亲所在的工厂那里是贵阳的郊区,可是从上海过去的人们依然坚信自己是上海人,当年两千多人挪过去把那片山给占了,小学校里说的全是上海话。小帅从小就说上海话,现在还能说。可是,若干年之后,小帅为了拍摄《青红》,回到贵阳,他以为他们也还说上海话,他跟他们说上海话,都没人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全是贵阳话了。小帅给整个弄蒙了。
小帅最初打算要拍的电影写的是五家人,都是同一个工厂里的,都是响应号召从上海到贵阳的,那时候还没开放,什么自由职业,停薪留职,什么说法都没有,调动和迁移必须都要户口档案。可这五家就跑了,有一家是小帅的一个老师,她是从小学到中学小帅最喜欢的一个老师。结果就是他们家,他老公那时候是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四家人策划好,半夜3点多钟,提前约好了车子(解放牌大卡车),开走了。第二天厂里发现人没了,家搬空了,他们已经奔上海去了。五家人家就在上海浦东农田边上住下了,什么都没有,户口上不去,小孩没法上学。慢慢的很多年,才开始扎下根。
《青红》的前身叫《我19》。跟后来所拍摄的《青红》有很大的区别,讲述的不仅仅是青红的故事,还有青红的女儿的故事,两代人的故事。不过,最后小帅还是没有在《青红》当中讲述那个拼了老命要回上海去的父亲和青红在上海的故事,他还是决定将这个叙述戛然而止,让上海继续停留在梦想之中。不过,我们依然在电影中看到青红的父亲和同事们开着秘密会议,策划回上海的内容。对于从小就生长在贵阳的青红这一代人来说,父亲的梦想并不是自己的梦想。可是对青红的父亲来说,他们像一些囚徒,时代的囚徒,被流放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做疯狂的挣扎。令他们疯狂的是这个错误似乎是他们自己犯下的,他们是自己从上海到贵州的。实际上,他们是听到了所谓时代号角的召唤他们依然是不能自主的蝼蚁。这种要与毁灭他们的“命运”抗争的行为以毁灭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为代价。
今年戛纳电影的主题是父爱和暴力,《青红》正好是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的。父亲以爱的名义,来阻挠破坏女儿的爱情,最后甚至是以爱的名义去摧毁这种爱情。
在国外大片和国产大片完全垄断电影市场的今天,王小帅仍然期待着一个良好的,多元化的创作环境,当我们的电影院只剩下商业大片,这其实是对整体发展的放弃,对文化信心的丧失。我记得去年小帅去贵州拍摄《青红》前跟我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要坚持下来,拍艺术电影。戛纳电影节的获奖可以说是恰逢其时。中国电影有着宝贵的艺术传统,2005年,在中国电影的百年华诞,《青红》和《孔雀》的获奖,无疑代表着中国电影的艺术传统的薪火相传。